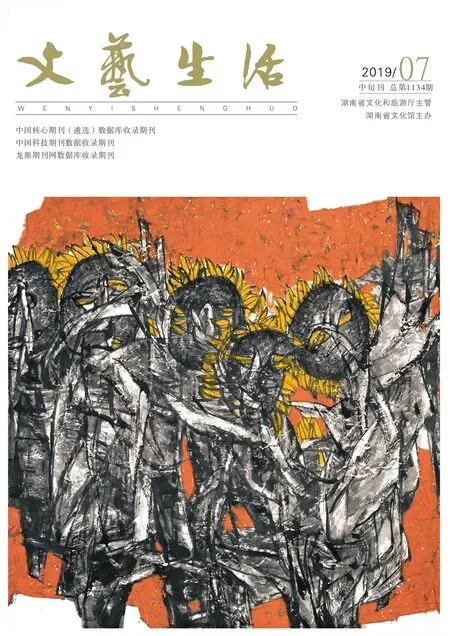論白先勇《Danny Boy》中的頹廢色彩
陳 敏
(青島大學,山東 青島 266071)
一、“頹廢”的概念
“頹廢”一詞源于拉丁語。1886年,魏爾蘭的雜志《頹廢者》的創辦,標志著法國頹廢主義文學的出現。伴隨著“頹廢派”的發展壯大,頹廢主義文學在文壇方興未艾20世紀20年代,西方頹廢主義文學傳入中國,對中國文學也產生重要影響。直到20世紀90年代之后,中國新時期文學才對頹廢主義逐漸接受,并開始注重對頹廢文學的研究。
頹廢“通常聯系著沒落、黃昏、秋天、衰老和耗盡這類概念,在更深的階段還聯系著有機腐爛和腐敗的概念”①在白先勇的小說中,這種頹廢之感既體現在人物對西方物質文明的崇拜之感,也有對現實世界產生的失落之感。
二、“頹廢”在文本中的呈現
白先勇筆下的人物大多充斥著孤獨、迷茫、憂郁等頹廢情緒,而他自身童年的孤獨生命體驗,也讓他的小說籠罩著一種濃厚的頹廢色彩,這種頹廢色彩在其同性戀小說《Danny Boy》中表現的尤為突出。
(一)個體生命的孤獨體驗
《Danny Boy》以日記體的形式記述了主人公云哥的命運遭際。在開篇,云哥在寫給韶華的信中回憶了他在臺北教書的生活。在校長、同事的眼里,他是一位受學生敬愛的模范老師。然而,他內心的痛苦卻無處訴說,即使是身邊最親近的人也只能選擇隱瞞,他身上的孤獨體驗一直貫穿在整個文本之中。
云哥的童年是遭受創傷的,父親去世,母親生下云哥便改嫁到日本,云哥過繼到韶華家中,過著寄人籬下的日子。對他而言,尋求感情歸宿的過程卻是異常艱辛的。云哥養成了沉默、孤獨的性格。雖然一直以來,云哥成績優異,但總是形單影只,無人傾聽他的心事,唯一與他親近的人便是韶華,當上老師之后的云哥更少回家,與韶華之間的聯系也越來越少。童年的經歷是造成主人公孤獨情緒的來源。在臺北教書期間,他一直掩蓋自己對男學生的迷戀情感,壓抑自己,孤獨地生活。當情感勝過理智,云哥被迫選擇逃離,開始他在美國的離散生活。
(二)“被棄”的逃離之感
由于傳統社會對同性戀群體的拒絕,同性戀者只能生活在社會的黑暗面,他們得不到社會、家庭的支持;而同性戀者本身由于長期被主流文化排斥,也對他們的心理上造成一定的缺陷。
小說中的云哥因為具有同性戀的傾向,一直痛苦地隱藏著自己的情感,即使是身邊最親近的人也選擇隱瞞。來到紐約后,云哥獲得了精神上的解放與自由,但也并未從分裂的世界中解脫出來,他仍然像夜行俠一樣,在黑暗之中尋求片刻的身體欲望的滿足。除了社會以外,云哥也未得家庭的關懷。他找不到自己的傾訴者,內心的孤獨、憂郁只能長期壓在內心深處。
(三)靈與肉的欲望沖突
李今指出:“文學上的頹廢風格顯在的內容特征是色情和肉感”②紐約作為欲望的都市,在給人極大的物質與精神滿足的同時,也以其極大地魔力引導人走向墮落的深淵。
在紐約,云哥在紐約找到了自己的容身之處,享受著紐約帶給他精神上的自由,但也讓他迷失了自我,陷入另一場災難。去了紐約的云哥,白天在圖書館工作,晚上便穿梭于曼哈頓的大街小巷,或者去酒吧中買醉,只有在黑夜之中,他們才能通過身體欲望的滿足來緩解內心的孤寂。但是這并不能徹底消解內心深處的孤獨,只能起到暫時的消解作用。欲望滿足之后,是更大的精神痛苦。“香提之家”度過的日子,云哥第一次感到家庭的溫暖,精神上的解放似乎拯救了一切。經歷社會的拋棄?身份認同的重新構建到最終感受到人間大愛之后,云哥最終實現由肉體到靈魂的跨越、由救人到自救的升華。
三、“頹廢色彩”背后的價值意蘊
白先勇在其小說中呈現出來的頹廢色彩與其自身的經歷有著密切的關系。白先勇以他親身的藝術實踐向我們展示了感傷、幽冷、頹靡、凄婉的頹廢美。《Danny Boy》中他讓那些孤獨頹靡同性戀群體得以發聲,再現這一類被社會邊緣化的群體的生活與內心情感,讓同性戀的離散者生活在有愛的空間里。作者試圖以跨越種族界限的人性交流尤其是愛情來撫慰這些人的心靈,在小說中,作者把同性戀與艾滋病聯系在一起,通過把云哥在“香提之家”照顧丹尼,解決了自己靈肉沖突之間的矛盾,獲得精神的解放作為結局,蘊含著作家內心中的人文關懷。
四、結語
在《Danny Boy》中,作者通過對人物個體生命的孤獨感的體驗、被拋棄之后的逃離之感、靈與肉的欲望沖突的描寫使得作品充斥著濃郁的頹廢色彩,在這濃郁頹廢色彩的背后蘊含著作家強烈的人道主義與人文關懷。
注釋:
①(美)馬泰.卡林內斯庫.現代性的五副面孔[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166.
②李今.海派小說與現代都市文化[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