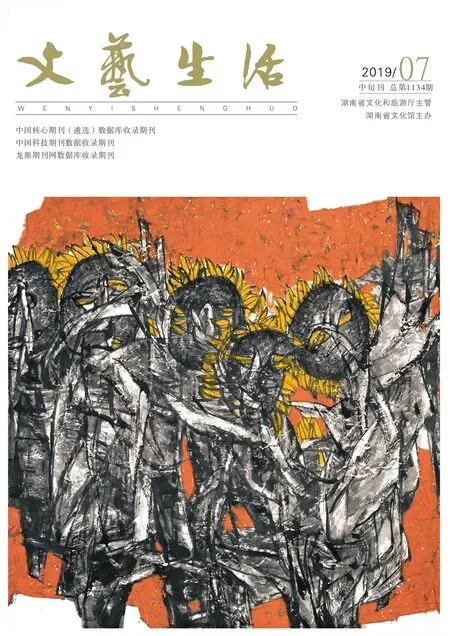禪宗對減筆人物畫法的影響
鐘 慧
(華中師范大學,湖北 武漢 430000)
東漢永平七年,漢明帝劉莊夜宿南宮,夢見一個身高六丈,頭頂放光的金人自西方而來,在殿庭飛繞。次日,漢明帝將此夢告訴給大臣們,博士傅毅啟奏說“西方有神,稱為佛,就像您夢到的那樣”。漢明帝聽罷大喜,派大臣蔡音、秦景等十余人出使西域,拜求佛經(jīng)、佛法。佛教自此由印度傳入我國來,并在本土化的過程中形成了我國獨有的禪宗。
在唐代時,禪宗被分化為南北兩宗。北禪宗的代表人物為禪宗五祖弘忍門下大通神秀,以弘法于北方,故稱北宗,主“漸悟說”,其代表偈語是“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表達出要循序漸進,不斷自省,方能修煉成正果。南禪宗的代表人物為六祖惠能,弘法于南方,故稱南宗,主“頓悟說”,其代表偈語為“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弘揚“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頓悟法門。此后,慧能南宗,勝于神秀北宗,成為中國禪宗的正宗,在發(fā)展過程中,逐漸成為影響最廣,流傳最遠的中國佛教宗派。
禪宗發(fā)展到了南宋,高僧、居士輩出,達到了禪宗的昌盛時代,在此階段,不但禪宗的語錄增多,并且大型登錄也陸續(xù)出現(xiàn)。禪宗倡導的見性成佛、直指人心的思想理論依據(jù),是解脫論上的“佛性論”。“佛性論”的意思是認為“眾人皆有佛性,眾人皆能成佛”。并且南宗的“頓悟說”認為:只須見性,即可成佛。“頓悟”是一種很重要的禪宗觀念,它是禪宗的靈魂和焦點范圍,由它衍生出禪宗的理論和實踐。禪宗主張的“不立文字”說,就是認為一切經(jīng)書、注釋都是因人而存在的,如果沒有了人,那么它們的存在便沒有了意義。把它應用到畫面上,就是對傳統(tǒng)方式的反叛,如果畫得很精細,就只會障人耳目,讓人執(zhí)著于此,也就達不到“明心見性”的效果,所以,繪畫若想成為幫助人們反觀自心,就必須簡化,去除一些不必要的修飾,這樣做反而可以增加畫面的內(nèi)容,同時又體現(xiàn)出禪宗無處不在、不可言說的特點。可見,若畫家真的以禪入畫,以畫參禪,必定會別開生面。
梁楷,其外號為“梁瘋子”,雖非和尚,但卻長于畫禪畫,與智愚、妙峰兩位僧人相交甚好,其受了南宗“頓悟”思想的影響,對畫面進行簡化,創(chuàng)造了“減筆”繪畫方法。
什么是“減筆”呢?減筆跟“細筆”相對,是中國畫的一種技法。“細筆”又叫“工筆”,屬于“密體”,追求周密精細;“減筆”屬于“疏體”,追求簡單干凈,能舍去的就舍去,這種技法叫“遺貌取神”,一筆也不能少,一筆也不能多,比細筆要求更高,更難。用筆從簡但是內(nèi)涵雄厚是減筆的特點,描繪對象用以一當十的方法,造型能力和筆墨本領非常精辟老練。“減筆畫”尋求筆墨的精煉,可以表現(xiàn)出對方的情態(tài),看著仿佛是隨意草草幾筆,但卻可以把對方的主要特點捕獲住,效果非常傳神。梁楷的減筆畫在用筆上精煉豪放,在構圖上簡約并且有力,以少勝多而內(nèi)涵深刻,十分耐人尋味。他通過有形的筆墨將無形的禪意表達出來,深深地感染著觀眾。
觀摩梁楷的傳世之作,能夠覺察出他在繪畫創(chuàng)作的過程中灌注了禪宗思想。比如《六祖斫竹圖》,展現(xiàn)了六祖惠能在砍竹子的過程當中“無物于物,故能齊與物;無智于智,故能運與智”,表現(xiàn)了南宗不參禪,不讀經(jīng)書,不重視外在的修煉,任其自然的態(tài)度。這張畫的人物形象不但簡約而且精煉,在用筆用墨上以少勝多,十分形象地描繪出了人物的生活場景和動態(tài)。
類似此種畫作,另有《李白行吟圖》以及《潑墨仙人圖》等。在《李白行吟圖》一畫中,惟有李白的頭部描繪地比較詳細,衣裳跟其余的地方,都是幾筆帶過,就將詩人的瀟灑、豪邁的模樣描繪地淋漓盡致。《潑墨仙人圖》給人的感受是用筆暢快,水墨淋漓。夸張地處理了仙人的頭部和眼耳口鼻,畫風豪邁瀟灑。觀摩這種畫,吾等可覺察梁楷是在擺脫佛教的清規(guī)戒律,回歸“禪宗”以自由、隨意為尚,以“意”見長,以少勝多。畫作中的筆墨與造型恰是禪宗思想的表現(xiàn)。觀賞梁楷的作品是一種筆墨的體驗,同時也是一種心境和禪意的體驗。其在禪宗影響下創(chuàng)造出的減筆畫法把寫意人物畫推上一個新的高度,使時人耳目一新,對當時及后世都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