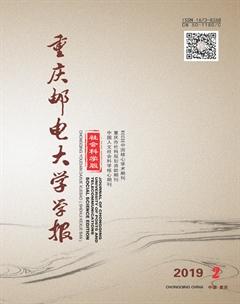情感類電視節目中“消費苦難”的道德考辨
張登皓
摘 要:情感類電視節目熱衷于消費個體苦難以博得觀眾同情,贏取高收視率。以異化“消費苦難”的職業性行為來喚起社會大眾內在的情感認同繼而獲得收益,已成為情感類電視節目制作者的一種營銷手段,其本質反映的是對人性的消遣、對情感的消費和對道德的褻瀆。從哲學語義來看,“消費苦難”是以引起道德感動、情感認同為內需性的一種社會生活方式,是人實現積極社會化的一種行為方式,是人自由發覺自身“善的系統”的一個過程,具有情感性、社會性和個體性的特征。異化“消費苦難”使情感類電視節目存在道德認知失真、道德情感失真、道德判斷失真、道德行為失真等問題,必須通過堅守道德底線,排除道德真空;牢筑職業道德,重視行業倫理;恪守道德情操,提高道德判斷;完善制度規定,明確行為責任等路徑實現“消費苦難”哲學語義的回歸。
關鍵詞:情感類電視節目;消費苦難;哲學語義;道德失真;道德回歸
中圖分類號:B8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8268(2019)02-0135-07
情感類電視節目作為備受制作人、廣大社會成員關注的節目種類之一,對發現和弘揚社會的真善美,實現和滿足社會成員內在的情感積淀和需要發揮了重大作用。但在社會發展面臨多重轉型時,它卻未能及時有效地、合規律性地找到一條健康發展之路;相反,作為其核心內容和主要銷售手段的“消費苦難”這一電視行為,卻一再陷入道德失真、失信于民的困境。在表層形態中,它表現為引發社會成員的普遍不信任和對其的道德詰難,在深層形態中則表現為社會的普遍情感冷漠。因此,如何界定“消費苦難”的邊界、重塑人民群眾的情感認同和提升社會的幸福感,是發展和滿足社會精神文化建設與個體情感的需要。
一、“消費苦難”概念的哲學界定
在對“消費苦難”這一概念進行哲學界定之前,有必要明確情感類電視節目的內涵以及其與“消費苦難”間的關系。概言之,情感類電視節目是產生“消費苦難”這一行為的基底,它“以人物的感情故事為資源,以動情為目的,煽情為手段”[1],實現電視與觀眾的連接,體現以情化人、以情育人的社會關懷。其原生制作意圖是用情感打動觀眾,以真善美的感召力修補觀眾的心靈陣痛。且因其直接作用于人的情感,故這種力量更為深沉、厚重,也更具影響力和持久性,因此,發揮好情感類電視節目的原生作用是其良性發展的重中之重。但其本質是市場化的產物,盈利是其內蘊屬性,一旦這種屬性蓋過了其原生功能的發揮與保障,表明其“初心”已不復存在,而“消費苦難”恰恰是其根本表現與核心內容。
(一)消費與苦難
談及“消費苦難”這一復合詞組時,需從“消費”與“苦難”這兩個單項詞語談起。先看“消費”。一方面,“消費”作為經濟學中的核心概念,指的是“對物質產品和服務的消費和使用,用以滿足人們的需要和欲望”[2]?;另一方面,它“作為一種時代的肯定形式真正出現于19世紀,并延續至今”[3]?。簡單來看,“消費”作為新興的經濟名詞進入到公眾特別是經濟學家的視野,在于生產的相對過剩,即生產與需求不存在緊張性,在一定意義上可視為不受需求制約的交換的擴大式社會行為和獨立式個體行為。所謂擴大式社會行為,強調的是由簡單的區域性社會交換行為轉變為復雜的完全性社會交換行為。獨立式個體行為表現的是由需求制約的半獨立式交換行為轉到不受需求制約的個體獨立交換行為上。總體來看,“消費”的實質就是交換。再談“苦難”。籠統地講,“苦難”指的是個體在社會化過程中經歷的艱難外部環境在情感上的一種認定方式。首先,“苦難”是個體實現社會化的組成部分和必要階段。佛教將人一生所經歷的“苦”分為八大類:“生、老、病、死、怨憎會、求不得、愛別離、五蘊盛”[4]。從時間維度來看,“生、老、病、死”是人從獲得獨立生命形態(脫離母體)到完結(完全死亡)需經歷的階段,這是基于一種人生軌跡的常態化查考,需要排除的是獨立生命形態在正常狀態下的非常態情況,即人為意外和自然災害。從社會化的維度來考量,“八大苦”是個體實現社會化的重要內容,內蘊了個體情感和社會情感。其次,“苦難”是一種艱難的外部環境,這表明其既是抽象的又是具體的。抽象性在于對一種或多種相似外部環境的系統認定,具體性指抽象成為苦難這一概念的外部環境是具體可感的。最后,“苦難”是一種體現個體或社會群體對情感的一種認定方式和價值定位。一是當將“苦難”定義為認定方式時,表現的是個體對其自身社會化所經歷的外部環境特征在形式和內容上的一種認識;二是將“苦難”定性為一種價值定位時,表現的是個體自身或社會群體在情感上的一種性質認定,與快樂、順利、幸福等類型相區分,通常的情感態度表達為“同情”“可憐”等。
(二)消費苦難
那么,“消費苦難”就是“消費”與“苦難”的簡單相加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基于上文對“消費”和“苦難”的哲學分析,不難明白,“消費”是一種人的外化的社會活動,是能夠通過有形物表現出來或一定標準度量的客觀行為。而“苦難”則是人對客觀環境在情感上的一種認知方式,具有主觀性,導致相同的“苦難”存在著不同的被認可、被接受、被同情的程度。也就是說,“消費”與“苦難”是兩種不同的質料。“消費苦難”就是“消費”和“苦難”這兩種異質物在一定作用下產生的既與兩者相聯系又相區別的新產物,表現為“出于母體”“異于母體”,是以引起道德感動、情感認同為內需性的一種社會生活方式,是人實現積極社會化的一種行為方式,是人自由發覺自身“善的系統”的一個過程。
首先,“消費苦難”離不開情感性。情感性是“消費苦難”的本質特性,是其得以存在、發展和變化的根基。當“消費苦難”作為一種社會生活方式,以道德感動、情感認同為內需性存在時,這種情感認同與道德感動就是情感性的外化形式,所以可以簡單地將滿足情感性的需要視為“消費苦難”的立命之本。需要注意的是:這里強調的情感性是人所獨有的,因為“消費苦難”的雙向主體是人;將道德視為情感性的一種具體形態,是因為社會體現出的道德就是情感的普遍理性約定俗成的表現。這種認識應區別于休謨簡單的“片面情感主義道德原則”[5],即休謨否認理性在道德判斷中的重要作用,認為道德判斷“不是一個思辨的命題或斷言,而是一種靈敏的感受或情感”[6]?。道德感動是“一種情緒狀態,是親身性、個別性、公眾性”[7]的有機綜合,情感認同是“借助自身的想象力,以當事人的立場,考察當事人置身的事情時自然而然產生的一種情緒”[8]?。以兩者作為一種目的性的內在需要的社會生活方式,是“消費苦難”的表層結構展示。第一,“消費苦難”從古至今都是社會的基本生活方式。由原始社會到現代社會,對于不幸者、弱小者的“幫助、救援”的社會化行為,是社會成員的一般生活方式。第二,“消費苦難”是社會人的一種普遍心態或基本情感需要。“消費苦難”在情感的維度上可看作一種語言和行動上的同情之意、同情之行。孟子曾論述人之為人的根本是具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其中排在首位的是惻隱之心。惻隱之心強調的就是對社會成員(除自身之外)具有“同情、憐憫”之情,做出滿足社會成員(包括自身在內)情感需要的基本反應。
其次,“消費苦難”離不開社會性。“消費苦難”之所以能夠成為一種社會生活方式,就在于其具有的社會性。“消費苦難”無論作為一種狀態還是行動存在時,不可回避是“人”創造發明的這一客觀事實。因此,“消費苦難”作為“人”的一種“創造品”就不難理解其具有的社會性。人是社會中的人,一生都在不斷地進行社會化。人的社會化過程采取的都是積極的社會性行為,“消費苦難”是其中之一,且成效顯著,這是因為“我們對悲傷的同情,就某一意義來說,比我們對喜悅的同情更為全面與包容”[9]?。“消費苦難”體現的是人的社會性需求,表現為滿足個體自身的情感需要和追求符合社會成員情感一致的表達。其一,“消費苦難”是滿足個體自身情感需要而進行的積極的社會化行為。實現自身情感的滿足與積極的社會化行為不存在沖突,相反,兩者統一于人獲得“社會人”這一身份認可的過程之中。其二,“消費苦難”是個體追求的符合社會成員情感一致的表達,本質上可看作是對一般社會道德要求的遵循。不可否認的是,的確存在違反社會成員應有的一致性情感的特殊情況,但就社會整體發展的潮流與要求來看,這種狀況是不入流的,應當進行改造。
最后,“消費苦難”離不開個體性。“消費苦難”的個體性特征來源于對其的哲學界定,人自身就是一種由“善意、善念、善心、善行、善舉”等要素組成的“善的系統”,人追求全面發展的過程就是不斷自由發覺自身“善的系統”的歷程。其間,不可忽視的是個體自身的認識因素對于自由發覺“善的系統”的重要影響,這是其一。在談及“善的系統”的發覺時,“自由”應成為一種自然選擇。在實踐中,難以否認的是由于個體在認知水平、行為能力等方面存在的差異,“自由”與“強制”經常作為組合出現,這是其二。在清楚個體性與“善的系統”之間的關系后,有助于理解“消費苦難”作為一種自由發覺自身“善的系統”的過程。這里表現有三:一是當“消費苦難”作為一種自由自覺的外在行為表露出來時,其本質反映的是個體內在的抽象的“善的系統”的外在具體化,通常以語言、行為等介質傳遞出來。二是“消費苦難”的存在前提是引起社會成員身臨其境、感同身受的情緒體驗。這種體驗在形式上通常存在著時間上的不一致性,可能是一瞬間的觸及,也可能是較長時間的醞釀。三是關于“自由發覺”的性質認定。“自由發覺”就屬性而言是一種方法,本質而言是對人自由意志的肯定。認為“消費苦難”是個體“善的系統”的“自由發覺”是人性本善的一種認識,因這一生活方式、行為方式而產生的自由發現自身系統中的善,不因外力而左右。但不可置否的是,這也存在著特殊性。
(三)現代語義下“消費苦難”的哲學認知異化
“消費苦難”具有經濟性與情感性。當將“消費苦難”置于哲學之下審視時,通過系統性抽象,完成了“消費苦難”在性質界定上的相對統一。但隨著物質社會的不斷發展,“消費”在一定程度上已成為現代社會成員的存在方式,“消費”的內容、形式和作用等發生了量的增加和質的變化。而“消費苦難”作為區別于“消費”的客觀存在,逐漸成為“消費”的內容之一,導致“消費苦難”在哲學性界定上出現了異化。第一,“消費苦難”最初作為一種自我自由發覺內在“善的系統”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質料的構成是情感認同和道德感動。在現代語義下,“消費苦難”成為“消費”的下屬物,不具有獨立性,即“苦難”是“消費”的對象,作為一種交換物而存在,是情感的加工品,導致其不具備哲學意義上的整體性內涵。第二,“消費苦難”由作為一種滿足社會成員情感需要、道德追求的社會普遍存在轉變為某一類行業的經營手段與營銷模式,內蘊于“消費苦難”之中的情感認同與道德感動成為該類行業興起與發展的根本因素。出于對此的認識,行業性的“消費苦難”往往在“苦難”這一感知上大做文章,嚴重挑戰著消費者的情感接受底線和道德容忍底線。第三,現代語義下的“消費苦難”是個人獲得社會同情的便捷手段。“同情”的內在情感因素之一就是“認定”,即“同情”包含著“認定”。就個人獲得的認定層次來看,情感認定是最為核心的。當個體獲得社會最為廣泛的認可后,目標的實現近在咫尺。同行業的營銷手段與模式一樣,個體對于社會大眾的情感接受底線、道德容忍底線的挑戰也時有發生。
正因為現代語義下“消費苦難”的哲學認知異化,造成了其背后的道德失真,突出表現在利用“消費苦難”作為存在基點的行業性的道德失真,典型代表就是情感類電視節目。
二、情感類電視節目“消費苦難”背后的道德失真表現
情感類電視節目作為現代社會滿足成員的情感需求、引導社會成員內在“善的系統”的自我發覺的重要傳播介體,其運作核心就是“消費苦難”。當“消費苦難”一詞在現代語義中產生異化時,內蘊于中的道德感動、情感認同和善的追求在原生性上出現信息丟失、價值偏離等問題。將其總括來看,表現為道德失真,即作為道德構成要素的知、情、意、行等在信息傳遞、情感表達時出現了虛假性和不真實性。在以“消費苦難”為吸引觀眾眼球、獲取收益的情感類電視節目中,這主要表現為道德認知失真、道德情感失真、道德判斷失真和道德行為失真。
(一)道德認知失真
情感類電視節目異化“消費苦難”的哲學界定的實質,反映的是對“消費苦難”的認知異化,外在形式上表現為道德認知失真,即對“消費苦難”道德的普遍認知、感知程度等失去了原生性意義,難以反映真實的道德底蘊。第一,情感類電視節目制作人(團隊)對“消費苦難”道德感動的動機認識不純,將該道德感動作為賣點,使其戴上世俗的面具。這種道德認知失真是其“在概念之間來回探索”[10]后的一種認識產物。有意為之形成的認知產物因其出發點存在價值偏離,即不是徹底意義上的希望實現對“善的系統”的自由發覺,故在基調建立上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失真問題。第二,社會大眾對情感類電視節目所傳遞的道德感動在認知上存在失真風險。其根源在于上文所談及的情感類電視節目制作人自身有意而為的對道德感動的偏差性理解。因此,大量虛假的信息導致了社會大眾難以對“消費苦難”存在真實的認知。第三,個體自我有意識地使自己對道德的認知陷入“失真狀態”。這里主要表現為個體因外在需要或實現某種目的而實施的將自我道德認知水平降低、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行為。在以“消費苦難”為核心內容的情感類電視節目中的突出表現,就是過分夸大所經歷的或正在經歷的苦難,甚至虛構苦難。如2011年河北石家莊電視臺雇人扮演情感故事《我為兒子當孫子》,直到不孝子“許峰”主動曝光這是作秀,真相才呈現在人們面前。這種虛構的“苦難”故事,緊緊抓住觀眾認知的情感變化,為的是獲得高收視率。這一“消費苦難”行為的產生,是電視節目制作團隊有意識地進入道德認知的“真空”與扮演者有意識地使自己對道德的認知陷入“失真狀態”共謀的結果。它挑戰了社會大眾的道德認知底線,是情感類電視節目原生功能與內蘊屬性失衡的第一重表現。
(二)道德情感失真
情感是構成道德整體的重要內容,情感的效用,特別是道德情感的效用就在于能形成最普遍的接受與認可。因此,喚起社會大眾的道德感受就成為以“消費苦難”為核心內容的情感類電視節目成敗的關鍵。為此,泛濫的人為道德情感刺激成為這類節目的常用手段,導致其內蘊于“消費苦難”中的道德情感面臨著嚴峻的失真局面。一是情感類電視節目制作人(團隊)虛構能夠引起道德情感共鳴的環節、場景等,增強對社會大眾道德情感的刺激。首先,虛構性地增加刺激物是其重要手段,由于刺激物本身就是虛假的、不真實的,故其傳遞出的道德情感也存在虛假性。其次,虛構性地加工“人、事、物”是其又一重要手段。二是當事人虛構或加工自我的苦難經歷,企圖獲得社會大眾的認可。當事人虛構或加工自我苦難經歷的手法,讓節目在道德情感信息來源上、處理上面臨著失真的詰問。如湖南衛視的《變形計》與韓紅在《中國夢之聲》中對“流浪歌手”進行打假就是這兩者的突出代表。
(三)道德判斷失真
談到道德判斷,必須提及上文闡述過的道德認知與道德情感。道德認知與道德情感作為影響道德判斷的重要因素,自身在以“消費苦難”為核心內容的情感類電視節目中本就面臨著失真的困境,因此,道德判斷作為受道德認知與道德情感共同影響下的一種思維方式與認定方式也面臨著失真的詰問。首先,個體自我虛構或加工外部艱難環境,會影響情感類電視節目制作人(團隊)的道德判斷。其次,以“消費苦難”為核心內容的情感類電視節目制作人(團隊)虛構或虛假性加工的苦難場景、環境、經歷等導致社會大眾的道德判斷失真。就這兩種道德判斷失真的性質來看,二者均由于信息在來源與加工上的非實導致大腦進行思維的材料非實,繼而發生失真情況。前者反映的是隱含在個體道德品質中的“惡性”,因此需要“去惡”;后者反映的是職業道德的不完善性,即未徹底發揮職業道德中的“善的功效”,因此需要“揚善”。前者多見于各類選秀比賽中,參賽選手希望通過虛構自身外部的苦難環境,引起電視節目制作人(團隊)在情感上的“共鳴”和認知上的“感動”;后者則常見于情感類的談話電視節目中,電視節目制作人(團隊)多以預演好的場景和內容向社會大眾傳播,以引發觀眾特定的道德情感,做出制作人預想中的行為反應。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電視節目制作人(團隊)還是社會大眾在進行道德判斷時,往往是剎那間的情感發生作用,并受感性支配。而受理性支配的道德認知或被虛構事實所蒙蔽,或被道德情感所代替,會在進行道德判斷那一刻失真。
(四)道德行為失真
所謂道德行為失真,指的是在進行道德判斷后采取的因道德感動、情感認同而產生的符合一般認識的善的行為失去了客觀真實性,難以滿足主體情感需要。在個體的“認知行為”系統中,道德行為失真是道德判斷失真的外顯。在核心內容為“消費苦難”的情感類電視節目中的主要體現是:社會大眾因苦難當事人和情感類電視節目的有意誤導(即希望社會大眾進行失真性道德判斷)而做出的非初始性情感需要的道德行為。這里需要說明的是,社會大眾因受誤導做出的道德行為是客觀的,是一種滿足情感需要的行為,但由于引發這種情感需要的前提是非情感真實需要的,因此,即使社會大眾獲得了情感滿足也只是一瞬間的,在這一瞬間下的道德行為相對整個過程而言是非真實的。一旦大眾明白自己做出了被設計好的道德行為后,會出現大面積的情感發泄,即由最初的“同情”與因非真實的情感認同做出了非真實的合乎內在善的需要的行為轉變為一種“指責”與群起圍攻。這常見諸于國內多檔電視選秀節目、談話節目、尋親節目及交換節目等,“黑幕”“內定”“打壓”“炒作”“作秀”等一時間成為這些節目的“社會印象”。此外,當苦難當事人為獲得情感類電視節目制作人(團隊)和社會大眾一致的道德同情,而虛構或加工自身的道德堅守時,道德堅守本身不存在滿足當事人的情感受用,這種情況下采用的道德行為也是非真實的,盡管形式上客觀存在。
三、哲學語義下“消費苦難”道德回歸的路徑
情感類電視節目承擔著自身特有的社會責任,即傳遞真實的滿足內在需要的情感,并積極引導人們自由發覺內在的善,最終成為“道德人”。當情感類電視節目因異化“消費苦難”而導致道德失真時,勢必會受到社會大眾的譴責。因此,合理實現情感類電視節目在“消費苦難”哲學語義下的道德回歸,是其擺脫外在指責、內在失調的根本方法。
(一)堅守道德底線,排除道德真空
對于情感表達當事人和情感類電視節目的制作人(團隊)而言,堅守道德底線、排除道德真空是其應遵守的最基本的道德準則。道德底線要求情感表達當事人和電視節目制作人(團隊)做出真實的情感表達與道德行為,不進行“藝術性編撰”和“藝術性加工”。道德真空即無道德存活的空間。涂爾干認為“在道德真空里,甚至連生命的血液都從個體道德中被抽掉了”[11]。情感類電視節目的道德真空表現為情感表達當事人與節目制作人(團隊)虛構道德情感,建立偽道德情感表達命題。這一命題中的道德情感無道德因子生存,無道德血液流動,更無需談其中的“消費苦難”。因此,排除節目中的道德真空狀態是實現“消費苦難”道德回歸的第一步,是實現“消費苦難”哲學語義下的“善的發覺”由設計發現到自我發覺的第一步。為此,首先,情感表達當事人應堅守自身的基礎道德認知,不虛構、不加工“苦難”事實,做到一是一、二是二,盡最大可能還原“苦難”的真實面貌;同時抵抗來自節目制作人(團隊)給出的物質誘惑,不參演虛假的“苦難事實”或經藝術加工已發生變化的“苦難”事實。其次,制作人(團隊)要牢記節目的原生功能,內蘊屬性要服務于原生功能。要對情感表達當事人提供的“苦難”材料進行審核,把好門檻底線。最后,觀眾應對情感表達當事人與節目制作人(團隊)進行監督,這是保障其道德底線的重要外部力量,也是排除道德真空的警示器。
(二)牢筑職業道德,重視行業倫理
電視行業相對于其他行業而言,其從業者有著自身特殊的職業道德要求,尤其是情感類電視節目的從業者,因從事的是記錄、傳播道德情感信息與道德行為的工作,更需要客觀、真實。不能因節目效果、經濟收益等刻意虛構或加工道德情感信息與道德行為,更不能因純粹個人的情感取向、價值取向而有意識地引導社會大眾做出相關的道德判斷和踐行相關的道德行為。因此,“消費苦難”不應成為一種營銷手段,而應作為記錄道德情感信息和傳播道德行為的承載物。此外,重視行業倫理建設也是完善職業道德建設,提高從業者職業道德素質的前提。電視業作為20世紀出現的新興行業,因其自身的特殊性,導致其倫理建設處于相對落后狀態,職業道德建設也處于待發展期。由此看來,異化“消費苦難”的職業行為不僅是職業道德建設未完善的結果,而且是行業倫理引導片面的結果。為此,牢筑職業道德及重視行為倫理要求:一是職業道德建設要與時俱進。情感類電視節目隨著時代的發展,形式上出現了多樣化,內容上出現了隱藏化,影響主體上出現了多元化。因此,從業人員的職業道德建設必須隨著時代的變化而不斷變化。同時,在涉及根本問題上要堅守立場。二是行業倫理的系統建設——政府層面和行業內部,兩者要同向發力,才能保障成效。
(三)恪守道德情操,提高道德判斷能力
恪守道德情操,不僅是對情感表達當事人和節目從業者的道德要求,而且是對社會大眾的道德要求。社會大眾因情感類電視節目傳遞出的道德情感而產生共鳴,由于這種共鳴是客觀存在的,導致一些人打著道德的旗幟,做出“非道德行為”,這應引起我們的重視。因此,恪守道德情操是每個人應具備的基本道德修養,修煉道德情操是人生必修課。一是從常見的道德實踐中發覺其中的道德情操,并積極恪守,不因常見而忽視,由此形成慣性,并發揮出慣性的力量。二是從特殊的道德實踐中發現其中的道德情操,并將其記憶,以供在遇到同一類道德實踐時借以參考。此外,社會大眾需對情感類電視節目有意表達出的道德情感信息加強辨析,進而做出有效的道德判斷。這對社會大眾的道德綜合素質要求極高,因此,社會大眾必須全面提升道德理論、道德實踐和道德認知水平。如果說恪守道德情操是一個從先驗到經驗的過程,因為道德情感先于引起道德情感共鳴的行為和信息存在人心,那么提高道德判斷就是一個從經驗到先驗的過程,因為在對引起道德行為的信息和行為進行判斷后,若認可則會接受,繼而內化于心,成為將來道德共鳴的先驗。由此,恪守道德情操與提高道德判斷是自我自由發覺內在善的意志的重要步驟,是“消費苦難”哲學語義下的方法論,也是情感類電視節目在“消費苦難”哲學語義下道德回歸的重要內容。
(四)完善制度規定,明確行為責任
俗話說,國有國法、行有行規。行規是實現行業活動有效開展的重要保障。情感類電視節目之所以能夠在異化“消費苦難”的內涵下得以“蓬勃發展”,關鍵在于其制度與行規存在漏洞。因此,要完成情感類電視節目在“消費苦難”哲學語義下的道德回歸除自身努力外,還須借助一定的制度與行規進行明確的行為規定和責任追究。制度與行規作為一種外力因素,因其內在結構的特殊性,即存在以強制力為依托的違反后處罰的后果,能夠使從業者明確行為和責任。此外,社會輿論作為監督行業行為的重要方式,大眾評價是影響行業生存、發展的重要因素,也能夠起到提醒和促進行業行為落實的重要作用。因此,形成以國家制度規定、行業規矩規范、社會輿論監督為內容,多邊共向發力的機制,是引導情感類電視節目完成道德回歸的重要手段。具體而言,首先,必須發揮政府在行業規范與社會輿論監督中的主導作用,讓政府做好三者的責任分流工作,并伴以強制力保障,實現三者責任的協調配比,發揮出最佳效果。其次,行業規矩、規范有顯性與隱性之分。顯性的行業規范就是以明確的文字形式確定的規矩,隱性的則是這一行業默認于心的規范,在一定程度上可視為一種對行業的信念與堅守。因此,在完善行業規矩、規范時,必須實現這兩條線的統籌兼顧,并在不同階段有所側重與平衡。最后,社會輿論的監督既是對制度的監察,又是對制度的補充,由此實現制度不斷接近完善的狀態。
四、結?語
有關道德的討論是一個社會永遠不會停止的話題,其根源在于社會越文明發展越需要道德作為社會成員內化在心、外化在行的社會規則,以指導個體獲得全面自由的發展。當然,社會的文明發展不是一帆風順、一蹴而就的,因此,道德的發展也不可能是固定不變、一勞永逸的。當下,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因各類新型行業的職業行為而產生的新型行業性的倫理名詞、職業性的道德名詞充斥在社會之中,深刻影響著社會成員的普遍情感認知。如何看待各類新型行業的職業行為,發揮出各行業性倫理要求、職業性道德要求指導行業良性發展的功效,進而優質地構建社會主義行業倫理和職業道德,并發揮出其原生性的效用,是我們當下不得不進行思考的。
參考文獻:
[1]?尹鴻.公共情感家園——評河北電視臺電視談話節目[J].真情旋律,2005(4):23.
[2] 胡金鳳,胡寶元.關于消費的哲學考察[J].自然辨證法,2003(11):79.
[3] 夏瑩.消費社會理論及其方法論導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111.
[4] 韓玉勝,楊明.中國傳統社會的精神家園的建設及其當代價值[J].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4):1.
[5] 劉麗.西方傳統倫理——道德關系的演進邏輯與馬克思的變革方式[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46.
[6] 休謨.道德原理探究[M].王淑芹,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107.
[7] 王慶節.道德感動與儒家示范倫理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31-33.
[8] 羅衛東.情感·秩序·美德:亞當·斯密的倫理學世界[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43.
[9] 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M].謝宗林,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50.
[10]楊祖陶.康德的三大批判精粹[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1.
[11]愛彌爾·涂爾干.職業倫理與公民道德[M].渠東,付德根,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