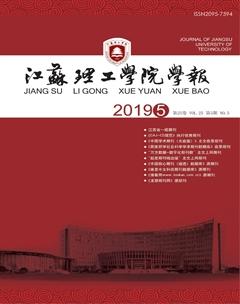論葛洪的子書觀念
摘??? 要:子書觀念在兩漢魏晉時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在這一變化過程中,葛洪的子書觀念呈現出一些值得關注的新特征。葛洪在對子書價值高揚的同時,對子書的性質作了儒學化詮釋,將創作子書詮釋為體認儒者身份和立言助教的途徑;他還推動了子書創作個人化的進一步發展,并將立身處世與立言之間的對應性分割開,為其后著述觀念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葛洪的子書觀念是東晉時期特殊時代文化背景的折射,不但在葛洪的思想體系中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而且對后世子書觀念和子書創作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關鍵詞:葛洪;子書觀念;子體自覺
中圖分類號:I20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7394(2019)05-0031-06
葛洪,字稚川,晉代丹陽郡句容人,是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道教學者。葛洪的著述很多,思想也包羅萬象,其中以《抱樸子內篇》為代表的神仙道教思想歷來為學界所重視,研究成果很多,葛洪也因此被認為是一個“道教學者”。但事實上,葛洪的成就和貢獻遠不限于神仙道教理論的范疇,他在醫藥、化學、政治、文學等方面的貢獻也不容忽視。在葛洪眾多的思想遺產中,他的子書觀念,也就是他關于“子書”的認識,在中古文體辨析和子書觀念的演變中具有較重要的意義和價值。
一、葛洪之前的子書觀念嬗變
“子書”是諸子之書的簡稱,本是中國古代圖書分類的一種,最早見于劉歆的《七略》。《七略》今已不存,但在班固的《漢書·藝文志》中有相關記載:“歆于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1]1701根據班固的記載,在《七略》的圖書分類中,“諸子”是與“詩賦”“術數”“兵書”等圖書并列的一種書籍類別。但在兩漢到魏晉的這個歷史階段,子書觀念發生了較大的變化,開始從一種集體創作的學派文集逐漸轉變成為由著書者獨立撰成的一種文體類別。
早在漢代以前,就已有《老子》《莊子》《孟子》等先秦諸子文本傳世,但據余嘉錫先生等人考證,這些諸子文本往往是“單篇獨行”,并且“不題撰人”,所以并不完全具備后世所謂“書籍”的性質。到劉向等人校書時,將思想相近的諸子文獻集中起來,就形成了后世所看到的“子書”。這些“子書”往往是一家之學的匯集,不僅作者并非一人,而且也非成于一時,其中的文體類型很復雜,體現為文集性質。余嘉錫先生認為:“周、秦、西漢之人,學問既由專門傳授,故其生平各有主張,其發于言而見于文者,皆其道術之所寄,‘九家之說,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不能相通,各有所長,時有所短。則雖其平日因人事之肆應,作為書、疏、論、說,亦所以發明其學理,語百變而不離其宗,承其學者,聚而編之,又以其所見聞,及后師之所講習,相與發明其義者,附入其中,以成一家之學。故西漢以前無文集,而諸子即其文集。”[2]51-52這大概就是子書產生時的最初形態。
到了漢代以后,國家立五經博士,經學成為利祿之途。特別是武帝以后,實行尊崇儒術的國策,先秦諸子所賴以繁盛的師徒傳承的一家之學的模式受到了很大的沖擊,除了五經之外的其他學問,很難再以先秦諸子的模式生存下去,所以民間雖然可能仍存在類似傳承,但很難再形成像先秦諸子那樣的文集式成書模式。新的思想家因其思想缺乏足夠的弟子傳承,所以不得不尋求新的思想傳承模式,著述文章就成了一種必然的選擇。但經學的壟斷性決定了即便是著述文章也未必能傳承下去,除非這些著述的文章能夠具備五經一樣的地位。所以,漢人最早有意在辭賦等之外別有創制的思想家揚雄,在創作他的《太玄》《法言》時,并不是為了創作什么“成一家之言”的子書,而是試圖模仿《周易》《論語》這樣的儒家經典,從而創作出新的“經”。揚雄雖然創制出了《太玄》和《法言》,但這兩部書并沒有能夠成為新的“經”。劉歆就曾說:“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醬瓿也。”[1]3585他的《法言》有一定的流傳,《太玄》卻沒有人能看懂,雖然桓譚認為揚雄的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于圣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為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1]3585但當時,也有人認為揚雄“非圣人而作經”是“誅絕之罪”[1]3585。所以到了王充作《論衡》,面對別人“圣人作,賢者述,以賢而作者,非也”的質疑時就不得不說:“非作也,亦非述也,論也。論者,述之次也。五經之興,可謂作矣。太史公書、劉子政序、班叔皮傳,可謂述矣。桓山君《新論》,鄒伯奇《檢論》,可謂論矣。今觀《論衡》《政務》,桓、鄒之二論也,非所謂作也。”[3]
漢魏諸子所著書雖常以“成一家之言”自期,但一般并不自號為某子,而慣常以論為名,如王充《論衡》、王符《潛夫論》、桓譚《新論》、曹丕《典論》、徐干《中論》等都是如此,這樣一來漢魏諸子新創作的子書就具備了演變成一種“文體”的可能,但在當時這種文體仍然以“論”為名,并沒有穿上諸子的外衣。如果將子書視為一種文體的話,那么在這個時期,這種文體的創作明顯還沒有成為一種自覺。
劉勰在《文心雕龍·諸子》篇中說:“若夫陸賈《典語》,賈誼《新書》,揚雄《法言》,劉向《說苑》,王符《潛夫》,崔實《政論》,仲長《昌言》,杜夷《幽求》,咸敘經典。或明經術,雖標論名,歸乎諸子。”[4]162而余嘉錫先生則認為“漢以后著作名為‘子書,其實‘論也。”[2]74但其實無論漢魏諸子的論著是算作“諸子”還是“論”,都昭示著一個同樣的事實:子書有了從圖書類別轉變為文體類別的可能。
到曹魏時,子書的地位越來越為世人所重。如曹丕在《與吳質書》中說:“偉長著《中論》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后;此子為不朽矣。”[5]1897曹植《與楊德祖書》也說:“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云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德薄,位為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勛績,辭賦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于名山,將以傳之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5]1903-1904仔細體味曹丕和曹植的話,我們可以發現:到三國時期,在辭賦文章之外撰著“成一家之言”的子書已經被視為一種通向不朽的極高理想。
值得注意的是:漢魏士人雖頗為重視子書創作,但如揚雄、王充等人往往是在晚年“道窮望絕”之后才開始創作子書;而曹植更是明言只有當自己“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的志向不能實現時,才會去創作子書。所以,可以說漢魏士人的子書創作仍然是不得已而為之的第二選擇,真正將創作子書作為一生事業的是葛洪,而子書的文體自覺在葛洪那里也更加明晰。
二、葛洪的子書觀念
葛洪當然不是第一個創作子書的人,但他大概是第一個明確將著述一部子書作為一生事業的人。他在《抱樸子·自敘》中毫不避忌地說:“洪少有定志,決不出身,每覽巢許、子州、北人石戶、二姜、兩袁、法真、子龍之傳,嘗廢書前席,慕其為人。念精治五經,著一部子書,令後世知其為文儒而已。”[6]710如果說漢魏諸子是“不能出身”迫不得已才著子書,那么葛洪則是從一開始就已經下定決心絕不出仕,而將著作子書作為自己一生的事業。因而葛洪的子書觀念較之漢魏諸子又有新的變化,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對子書價值的高揚,極為重視子書的價值,認為子書價值不但高于詩賦,也高于讖緯、術數等學問;二是對子書進行了儒學化,認為子書源自五經,是文儒身份的體認途徑;三是子書創作個人化,認為子書創作完全是個人之事,不但獨力完成,而且自分內、外篇,自定家派歸屬;四是將子書創作與立身之道的分離,認為子書的內容與作者的處世方式不必一致,隱逸和討論政治并不矛盾。
(一)葛洪對子書價值的高揚
三國時期,曹丕、曹植等人就已經極為重視子書的價值,葛洪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對子書價值進行了高揚。他不但將子書的價值放到詩賦雜文之上,甚至將其放置到漢代流行的神秘的讖緯、術數等學問之上。
首先,葛洪將子書與詩賦等進行比較,他說:“或貴愛詩賦淺近之細文,忽薄深美富博之子書,以磋切之至言為騃拙,以虛華之小辯為妍巧,真偽顛倒,玉石混淆,同廣樂于桑間,鈞龍章于卉服。悠悠皆然,可嘆可慨也!”[6]105葛洪將詩賦稱為“淺近之細文”,而對子書則用“深美博富”來形容,并且認為貴愛詩賦而忽薄子書是“真偽顛倒、玉石混淆”,是“可嘆可慨”的,其重子書輕詩賦的觀點顯而易見。并且在《抱樸子·自敘》中葛洪進一步重申了這一觀點,他說:“洪年二十余,乃計作細碎小文,妨棄功日,未若立一家之言,乃草創子書。”[6]697與創作子書相比,葛洪甚至說作細碎小文是“防棄功日”的浪費時間的行為,很明顯,葛洪是將子書的價值放在詩賦等文章之上的。雖然這與自揚雄以來鄙薄辭賦的傳統一致,但葛洪將子書譽為“深美博富”,而將詩賦視為淺近細文,抬高子書價值的意圖可謂不言而喻。
其次,葛洪將子書與漢代流行的讖緯、術數等學問進行比較,他認為子書的價值也高于這些學問。他說:“其河、洛圖緯,一視便止,不得留意也。不喜星書及算術、九宮、三棋、太一、飛符之屬,了不從焉,由其苦人而少氣味也。晚學風角、望氣、三元、遁甲、六壬、太一之法,粗知其旨,又不研精。亦計此輩率是為人用之事,同出身情,無急以此自勞役,不如省子書之有益。”[6]656河、洛圖緯等讖緯、術數的學問,在漢魏時期被稱為密不外傳的“內學”,一向受當時學者珍視。但葛洪認為研習這些學問不但是“苦人而少氣味”的無趣之事,而且從價值上看,也“不如省子書之有益”。很明顯,葛洪將子書的價值置于這些讖緯、術數等學問之上,也是為了高揚子書的價值。
總之,在葛洪的子書觀念的價值維度層面,葛洪認為子書的價值不但高于詩賦雜文,而且也比讖緯、術數等學問更有趣味、更有價值。而對子書價值的高揚,則為通過創作子書“立言助教”體認“文儒”身份提供了合理的理由。
(二)葛洪對子書的儒學化詮釋
在葛洪生活的時代,儒學雖然已經受到道教和外來的佛教等思想的沖擊,但在社會生活中依然占據著統治的地位,有時候甚至成為統治者清除異己的借口。如曹操殺孔融,司馬氏殺嵇康等都是如此。葛洪要將子書創作作為合理合法的一生功業,就不得不解決子書與儒學的關系問題,如果像嵇康那樣“非湯武而薄周孔”當然是不行的,因此,葛洪在論述子書的性質時,對其作了儒學化的詮釋。
1.葛洪從主旨方面對子書進行了儒學化的詮釋
葛洪說:“正經為道義之淵海,子書為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則林薄之裨嵩岳也。雖津途殊辟,而進德同歸;雖離於舉趾,而合於興化。故通人總原本以括流末,操綱領而得一致焉。”[6]98葛洪將儒家的五經稱之為“正經”,比喻為道義的淵海,而將子書比作增加淵海深度的河流,其實就是說子書和五經本質上是一致的,是殊途同歸的,子書不但無損于儒學,而且是正經的有益補充,是有助于“進德”和“興化”的。這種“進德”和“興化”的子書主旨表述正與《漢書·藝文志·諸子略》中班固對儒家者流“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的描述相合,顯然葛洪對子書的性質作了儒學化的處理。
2.葛洪從思想淵源方面對子書作了儒學化的詮釋
葛洪說:“洪少有定志,決不出身,每覽巢許、子州、北人石戶、二姜、兩袁、法真、子龍之傳,嘗廢書前席,慕其為人。念精治五經,著一部子書,令後世知其為文儒而已。”[6]710我們看到,葛洪將著作“子書”建立在對“五經”的精治之上,這樣一來,從思想淵源上講,子書也是來源于五經,自然應該“屬于儒家”。而且葛洪將著作子書視為文儒身份體認的方法和途徑,無疑是將《漢書·藝文志》中分為九流十家的諸子統統納入儒家的麾下,這樣一來,子書所謂的“成一家之言”的“一家”,已不再像是先秦諸子那樣與儒家并立的關系,而是成為儒家之中的一個思想分支。
通過對子書的儒學化詮釋,葛洪將子書裝扮成“興化助教”的儒學的一個組成部分,這雖然是漢代儒術獨尊以后學術發展的必然結果,但也從側面反映出正始以來的政治高壓,特別是嵇康被殺、向秀入洛等事件對士人心態所造成的潛在影響,隱逸的合法性已經成為需要辯護的問題,而葛洪將子書儒學化,無疑為這種合法性提供了有力的支撐。
(三)子書創作的進一步個人化
葛洪子書觀念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子書創作的個人化。這首先表現在子書的撰寫方面,葛洪的《抱樸子》完全是由他自己獨力完成,而且是自覺主動的創作。他在《自敘》中說:“洪年二十余,乃計作細碎小文,防棄功日,未若立一家之言,乃草創子書,會遇兵亂,流離播越,有所亡失。連在道路,不復投筆十余年。至建武中,乃定。”[6]697根據這段論述,我們可以知道,葛洪從二十多歲時就已經開始自覺地起草撰寫子書,歷經十多年的時間到建武中定稿,在這個過程中全是葛洪獨力創作,而且葛洪還自己對所作子書作了多次修訂完善,他說:“他人文成,便呼快意,余才鈍思遲,實不能爾。作文章每一更字,輒自轉勝。”[6]696子書創作個人化趨向非常明顯。
葛洪子書觀念中,子書創作個人化還體現在對子書的歸類方面。他在《自敘》中說:“凡著《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其《內篇》言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卻禍之事,屬道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事臧否,屬儒家。”[6]698《漢書·藝文志》將諸子之書歸為九流十家,子書的家派歸屬乃是劉向、劉歆父子等后人根據一定的依據所定,而葛洪在《自敘》中,卻是自己將所作子書作了家派歸屬界定,這種子書歸類的自我界定,無疑說明了葛洪子書觀念中的個人化傾向。
(四)子書創作與立身處世的分離
在葛洪之前,“立言”往往都是對立身處事之道的總結,言行一致是一種自然要求,孔子講“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就是這種情況的反映。但在葛洪的子書觀念中,卻將二者隔離開來,他一方面宣稱“少有定志,決不出身”,另一方面卻在所著《抱樸子》中討論了大量的“君道”“臣節”等政治內容,所以在當時就引起了一些人的論難:“今先生高尚勿用,身不服事,而著《君道》《臣節》之書;不交于世,而作譏俗、救生之論;甚愛汗毛,而綴用兵戰守之法;不營進趨,而有《審舉》《窮達》之篇。蒙竊惑焉。”[6]408對此,葛洪回答說:“君臣之大,次于天地。思樂有道,出處一情,隱顯任時,言亦何系?大人君子,與事變通。老子無為者也,鬼谷終隱者也,而著其書,咸論世務,何必身居其位,然后乃言其事乎?”[6]409葛洪認為子書的內容與立身處世是兩回事,是隱居還是出仕是要根據時事決定,但無論是隱居還是出仕都“思樂有道”的“情”都是一樣的,因此他的隱居與論政是“出處同歸,行止一致”[6]411的 。
總而言之,葛洪的子書觀念較之前一階段又有了新的發展,葛洪一方面高揚子書的價值,以“深美博富”稱揚子書,將之駕于詩賦等文章、學問之上,另一方面對子書作了儒學化詮釋,將隱逸著述和立言助教結合起來,力圖消弭漢代以來士人與政治的疏離關系,在進一步推動子書創作個人化的同時,也開始將子書創作與立身處世分離,使得創作子書進一步脫離了“身份”的束縛,為將來蕭綱“立身之道,與文章異”觀點的提出提供了理論依據。
三、葛洪子書觀念的成因及其價值與影響
葛洪的子書觀念是對其之前子書觀念的繼承和進一步發展,也是晉代文學思潮發展的內在要求,不但在葛洪的思想體系構建中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而且對葛洪之后子書觀念的發展和子書創作的模式也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是我們考察晉代思想史和文學史的一個重要觀照視角。
(一)葛洪子書觀念的成因
葛洪的子書觀念當然是在前一階段子書觀念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的結果,但葛洪子書觀念特性的形成,與晉代文學思潮和社會環境也存在密不可分的關系。葛洪之所以特重子書,將子書凌駕于詩賦和讖緯、術數等學問之上,體現出一種求真務實的精神,與西晉崇尚玄談的風氣有關。葛洪著述《抱樸子》時,正當西晉由內爭走向潰亂滅亡的時期,當時社會上流行的觀點傾向于將西晉的滅亡歸結為玄談之風的空談誤國,劉義慶《世說新語·輕詆》篇載:“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虛,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7]979王夷甫就是西晉玄談的主要人物王衍,東晉桓溫將西晉滅亡的原因歸于玄學空談,雖然未必完全符合事實,但至少表明西晉滅亡后,社會上開始有一種對玄學反思的潮流。葛洪在《抱樸子》中說:“常恨莊生言行自伐,桎梏世業。身居漆園,而多誕談。好畫鬼魅,憎圖狗馬。狹細忠貞,貶毀仁義。可謂雕虎畫龍,難以征風云;空板億萬,不能救無錢;孺子之竹馬,不免于腳剝;土柈之盈案,無益于腹虛也。”[6]411莊生就是莊子,葛洪批判《莊子》空虛無用,而《莊子》恰恰正是玄學家理論核心的“三玄”之一,葛洪在《抱樸子》中對玄學、放達和飲酒等現象的批判無不顯示出時代風尚對葛洪子書觀念的潛在影響。
西晉文學本不輕詩賦,陸機、左思、潘岳等人都以詩賦名家。陸機《文賦》說:“辭程才以效伎”,又說:“收百世之闕文,采千載之遺韻。謝朝華于已披,啟夕秀于未振。”[5]763就是其詩賦觀的極好注腳。但西晉的詩賦極重辭采,以繁縟為基本特征。沈約在《宋書·謝靈運傳論》中說:“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5]2218-2219明確點出了西晉文學重辭采的特征。葛洪以“深美博富”譽子書,以“辭贍義豐”為文學價值的評判標準,均說明葛洪并不反對辭采,他將“深”置于“美”和博富之前,而將詩賦斥為“淺近之細文”,更多的可能是為了喚起對子書“義”的層面的關注,而不僅僅是停留在“文”的層面。
葛洪將子書儒學化,不但是漢代以來儒術獨尊的發展結果,而且也與時代氛圍息息相關。葛洪之所以不停地強調隱居著述是“立言助教”,與整個魏晉時期的政治形勢也有關系。早在漢末時,由于政治的黑暗腐敗,士人就與大一統政權產生了疏離;正始時期,司馬氏與曹氏爭權,導致“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8]而《世說新語·言語篇》的一段記載,將士人隱居不仕的危險描繪得十分真切:“嵇中散既被誅,向子期舉郡計。入洛,文王引進,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對曰:‘巢許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7]93司馬氏殺嵇康的原因雖然比較復雜,但最明顯的原因就是他“非湯武而薄周孔”,不與司馬氏同流,所以嵇康被殺對天下名士的震動是很大的。沒有正當理由的隱居不仕,實在是有“以自己的高潔,顯朝廷污濁”的嫌疑,所以葛洪說:“仆所以逍遙於丘園,斂跡乎草澤者,誠以才非政事,器乏治民,……若擁經著述,可以全真成名,有補末化;……雖無立朝之勛,即戎之勞;然切磋後生,弘道養正,殊涂一致,非損(化)之民也。劣者全其一介,何及於許由,圣世恕而容之,同曠於有唐,不亦可乎!”[9]59而在《逸民篇》中士人的話更是這種危險的直接表述:“然時移俗異,世務不拘,故木食山棲,外物遺累者,古之清高,今之逋逃也。”[9]64在這種情況下,葛洪力辯自己之所以不出仕,是因為自己沒有從政的才干,而且自己雖然不仕,但擁經著述,也是有補于教化的,這也是他將所作子書作儒學化詮釋的又一原因。
(二)葛洪的子書觀念在其思想體系構建中的理論價值
葛洪的子書觀念對于他的思想體系的建構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葛洪的思想其實是內神仙而外儒術的,他的思想核心是神仙道教的,但他在著述子書時,通過《外篇》的著述和將子書儒家化的詮釋,獲得了“立言助教”的合法外衣,他在《自敘》中說:“凡著《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其《內篇》言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卻禍之事,屬道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事臧否,屬儒家。”[6]698他通過將子書的創作和學派歸屬的個人自定,以及將立身處世與立言分離開來,進一步解放了“立言”的身份限制和社會限制,使得創作子書成為名正言順的合理選擇。
(三)葛洪的子書觀念對后世子書的影響
葛洪的子書觀念對其后的子書思想和子書創作也有較大影響。如蕭繹在《金樓子序》中說:“蓋以金樓子為文也,氣不遂文,文常使氣。材不值運,必欲師心;霞間得語,莫非撫臆。松石能言,必解其趣;風云元感,倘獲見知。今纂開辟以來,至乎耳目所接,即以先生為號,名曰金樓子。蓋士安之玄宴,稚川之抱樸者焉。”[10]249-250蕭繹是將葛洪著作《抱樸子》作為自己的效法對象。另外,劉勰在《文心雕龍》中以“博明萬事為子,適辨一理為論”[4]162將子體和論體區分開來,與葛洪崇博尚深子書價值觀一脈相承,可見葛洪的子書觀念對后世的影響。
參考文獻:
[1] 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
[2] 余嘉錫.古書通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3] 黃暉.論衡校釋[M].北京:中華書局,1990:1180-1181.
[4] 周振甫.文心雕龍今譯[M].北京:中華書局,2013.
[5] 蕭統.文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6] 楊明照.抱樸子外篇校箋:下[M].北京:中華書局,1997.
[7]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M].北京:中華書局,2007.
[8] 房玄齡.晉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1360.
[9] 楊明照.抱樸子外篇校箋:上[M].北京:中華書局,1991.
[10] 柯慶明,曾永義.兩漢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料匯編[M].臺北:成文出版社,1978:249-250.
The Zishu Concept of Ge Hong
WU Xiang-ju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Jiangs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213001, China)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the Zishu changed greatly in the Han Dynasty, Wei and Jin dynasties, and Ge Hongs concept of the Zishu showed some new characteristics worthy of attention in the process of this change. At the same time, GE Hong made a Confuci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nature of the Zishu, interpreting the creation of the Zishu as the way to recognize the identity of Confucianism and the way of teaching assistants. He also promoted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individualization of the creation of the Zishu and separated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standing up and speaking, which laid a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writing after the creation of the Zishu, which made a Confuci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nature of the books and interpreted the nature of the books as well as the nature of the books, and interpreted the creation of the books as the way to recognize the identity of Confucianism and the way of teaching assistants. GE Hongs concept of the Zishu is a reflection of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special era of Jin Dynasty, which not only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in Ge Hongs ideological system, but also ha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The concept of later
generations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Zishu have also had a certain impact.
Key? words: Ge Hong;Zishu emphasize concepts;self-awakening of Zhuzi Style
責任編輯??? 趙文清
收稿日期:2019-07-15
基金項目:江蘇省教育廳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空間維度的晉代江南文學研究”(2017SJB1737);江蘇理工學院社科基金項目“葛洪研究”(KYY14524)
作者簡介:吳祥軍,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古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