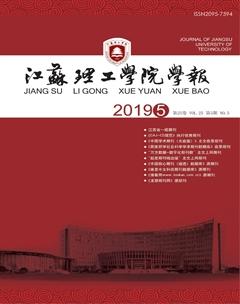南朝吳聲曲辭的敘事色彩
摘??? 要:南朝文學作品中存有470余首樂府民歌,其中吳歌曲辭占有絕對比例。它們作為吳地文學的代表,展現出鮮明的敘事色彩。從吳聲曲辭敘事性的成因入手,探究其在內容、結構、語言方面的敘事性表現,并分析南朝吳聲曲辭敘事性所產生的歷史影響。
關鍵詞:南朝樂府詩;吳地文學;吳聲曲辭;敘事性
中圖分類號: I22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7394(2019)05-0037-04
在南北朝文學史中,樂府歌辭定是濃墨重彩的一筆。這一時期的樂府詩歌已然發展到成熟階段,它具有民間文學的蓬勃生氣,出語天然而不加雕飾,內容質樸又貼近生活,情感真摯能打動人心,詩風明快朗朗上口。所以,樂府詩的創作模式很快就在全社會流傳開來,從市井走向宮廷,從民間蔓延至上層,將新鮮的血液輸入文人的創作中去。
南北朝樂府詩以南朝為重,而南朝樂府詩又集中發軔于長江流域,是歷代江南文學的典型代表。從數量上看,南朝樂府詩近500首,全部存錄于宋代郭茂倩編纂的《樂府詩集》中,其中絕大多數被歸入“清商曲辭”一目,只有《西洲曲》《蘇小小歌》《東飛伯勞歌》等不足10首詩列在“雜曲歌辭”和“雜歌謠辭”類目下。“清商曲辭”又分為“吳聲曲辭”和“西曲歌”兩類,其中有“吳歌”326首,“西曲”142首。從地理位置上看,以六朝都城建鄴(今南京)為中心的長江下游地區自古為“吳地”,故此處的樂府民歌被稱作“吳歌曲辭”。《晉書·樂志》有言:“吳歌雜曲,并出江南。”[1]675《樂府詩集》曰:“蓋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陳,咸都建鄴。吳聲歌曲,起于此也。”[2]570而長江中游的江漢地區是南朝西部重鎮和經濟文化中心,故其民歌是為“西曲歌”。《樂府詩集》引《古今樂錄》載:“西曲出于荊、郢、樊、鄧之間,而其聲、節、送、和與吳歌亦異。”[2]607由此可見:吳聲曲辭在體例和內容上都是南朝樂府詩的縮影,是當時社會文化背景在文學中的投射,故而本文將探究吳聲曲辭的敘事性成分,分析其文化價值下的文學特征。
一、吳聲曲辭的敘事性成因
吳聲曲辭的敘事性題材和內容,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它們或從文學的源流繼承角度為吳聲曲辭敘事打下基礎,或從客觀的外部社會環境為吳聲曲辭敘事提供素材,兩者共同作用下才形成了豐富的吳聲曲辭敘事性。
從文學史的角度看,以吳聲曲辭為代表的南朝樂府詩,保留了古風詩歌的特征,沿襲了古體詩的敘事傳統。從《詩經》到漢樂府民歌,其題材內容均來源于真實社會生活,行文以質樸自然為主,語言平實,不講究嚴格的韻律規則,常采用動作描寫、語言描寫等手法突出敘事元素,具有鮮明的敘事性。南朝樂府詩與漢樂府民歌一脈相承,從文體類型到藝術特點,均保持了高度的相似性,從而構成了吳聲曲辭敘事性的主要成因。
從社會政治文化環境的角度而言,吳聲曲辭發軔于六朝時期,學術思想較為開放,描寫百態生活和真實情感就成為這一時期的文學常態,所以敘事的元素也隨之增多,敘事性亦增強。魏晉南北朝政權更替頻繁,傳統道德規范失去約束力,統治者對人民的思想控制較為寬松,追求人生的快樂、情感的滿足,成為一種普遍的心理趨勢。如《晉紀·總論》載:“其婦女……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佚之過,不拘妒忌之惡。”[1]125這樣的社會風氣投射在文學中,導致文學創作并無太多避諱,涌現出大批描寫男女愛情生活及情感的作品。
從地理經濟和歷史人文的角度而言,江南則是樂府詩歌成長、繁榮的沃土,它獨特的地理、人文環境為吳聲曲辭提供了發展空間,可以入詩的事物層出不窮,同樣促進了文學敘事性的發展。首先,江南地區的自然環境得天獨厚——山川明媚,水土豐茂,物產豐富,氣候溫宜,擁有歷史悠久的農耕文明;東晉以后,吳地的商業、手工業也得到長足發展,讓吳地更加富庶。優渥的經濟環境,使江南人民生活得較為愜意,培養出他們溫婉多情又細膩浪漫的性格特點。其次,吳文化的歷史源遠流長,創作民歌的傳統可以追溯至春秋的吳越時期,《漢書·藝文志》便記載漢樂府中有“吳楚汝南歌詩十五篇”。在這種天然美好的環境中,曲辭易于發達。悠閑又善感的男女們,常常為生活中的瑣事而觸動,生發出纏綿的喟嘆。《南史·循吏列傳》載:“(宋世太平之際)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歌謠舞蹈,觸處成群。……永明繼運……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聲舞節,袨服華妝,桃花淥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無往非適。”[3]
從創作群體的文學素養而言,吳聲曲辭大多出自底層人民之口,主要反映中下層百姓的生活和感情,所以敘事的成分居多,形成了吳聲曲辭的敘事性。南朝樂府詩的作者來源既有文化水平較高的文人群體,也有普通的平民百姓,且民間創作的樂府詩占絕大多數。由于受學識學養所限,底層人民對抽象化、藝術化的規范行文模式并不熟悉,只能用平實的語言和直白的敘述方式自由地淺唱低吟,歌唱的內容也是大家能接觸到的日常生活和由瑣事生發出的情感。所以,吳聲曲辭不僅非常貼近百姓的心理,而且口語化色彩濃厚,作品的敘事成分比重大,從而形成了鮮明的敘事性。
二、吳聲曲辭的敘事性表現
吳聲曲辭的敘事性在其題材內容、表達手法、情節結構等方面得到體現。
首先,吳聲曲辭作為南朝樂府詩的重要組成部分,繼承了漢樂府民歌“緣事而發”的特征,在題材內容上表現出與事件的密切相關,呈現出的文本也是針對某一事件的概述。事件不僅是構成全篇的基礎,也是作者抒發情感的主要動因。以吳聲曲辭的代表作《子夜歌》為例。相傳《子夜歌》的曲調是晉代一位名叫子夜的女子創作,抒寫哀怨或眷戀之情,據《宋書·樂志》記載:“《子夜歌》者,有女子名子夜,造此聲。”故名。《樂府詩集》中收錄五言四句式的《子夜歌》共42首,其內容是以一位女子的口吻,講述了自己和情郎從甜蜜相依到被無情拋棄的過程,這些詩作既能夠獨立成篇,也可以合在一起形成組詩,與《子夜歌》曲調的內涵相合。全文從“落日出前門”起筆,點明時間和事件的起因;當男女二人相見時,“宿昔不梳頭,絲發披兩肩。婉伸郎膝上,何處不可憐。”這一場景描寫展現出濃烈的柔情蜜意;待到分別時,女子不舍地問道:“今夕已歡別,合會在何時?”但隨著分離的時日漸久,女子的生活充滿了悲情,在“別后涕流連,相思情悲滿”的同時,還要接受“郎為傍人取,負儂非一事”的現實,原本美好的愿望落空了,留給她的只有一縷織不成匹的亂絲。將全篇貫穿起來賞析該詩,更能看出敘事情節的跌宕起伏——多個片斷場景串聯在一起,便于把握女主人公的情感波動,由敘事元素衍展出抒情話語的展開,解讀更加透徹。所以,“緣事而發”的詩歌創作要求作者在構思中采用韻文的形式,將一個事件拆分開來,與抒情性的語句雜糅在一起,豐富了詩歌的意蘊層面。由此可以看出,吳聲曲辭不僅具有樂府曲辭的音樂性、抒情性特征,而且還充盈著豐富的故事情節,呈現出濃厚的敘事色彩,是南朝樂府詩具有敘事性的有力佐證。
其次,吳聲曲辭大量采用對話或獨白的語言描寫形式進行敘事。將語言描寫引入詩句,是韻文敘事性的典型表現之一,它是將人物語言與情節發展融為一體,直接用故事主人公的口吻說明事件的節點,使詩歌的情節性更強,更具有感染力和說服力。吳聲曲辭常為描寫男女愛情題材的情歌,且以女性口吻居多,故而詩歌中存在大量的語言描寫,它們或是對話,或是獨白,大膽突破宗法禮教思想的束縛,熱烈而堅定地唱出她們的愛情心聲。在吳聲曲辭中,常見人稱代詞“我”“妾”“君”“郎”等,皆是女性對自己的自稱與對情人的昵稱,是語言描寫的獨特標志。如“始欲識郎時,兩心望如一。”(《子夜歌》)是女子在自言自語中抒發對愛情的渴望;“我心如松柏,君情復何似。”(《子夜四時歌·冬歌》)是女子面對困境,堅定地表示對愛情的矢志不渝;“人傳歡負情,我自未嘗見。”(《子夜變歌》)是癡情的女子對于負心漢的盲目無視,自我欺騙。這些帶有豐富感情的口語化表達方式體現出樂府歌辭率真自然、不加雕飾的風格特點。《大子夜歌》有云:“歌謠數百種,子夜最可憐。慷慨吐清音,明轉出天然。”這首本為點評子夜女悲情的歌謠,也從側面點明《子夜歌》的語言特征,即“清音”“天然”,這正是以吳聲曲辭為代表的南朝樂府詩所具有的敘事性表現。
再次,吳聲曲辭中有很多對具體生活情狀的描寫,它們不僅成為記錄當時社會現實的史料性依據,而且還具有曲折的情節性,構成了敘述事件的過程,這些帶有“詩史”性質的文學敘述即為吳聲曲辭敘事性的體現。如《讀曲歌》中的兩首詩:
家貧近店肆,出入引長事。郎君不浮華,誰能呈實意?
登店賣三葛, 郎來買丈余。合匹與郎去,誰解斷粗疏?
從詩的首句即能看出主人公身份,“家貧近店肆”和“登店賣三葛”表明這是一位生活在城市底層的商家,并且生活不富裕;接著,詩中又出現了“郎君”“郎”等詞,是女子對情人的昵稱,進一步補充說明主人公是一位商戶女子。而普通市民的主要衣料也是葛布,且購買力有限,“丈余”剛好是做一件衣服所需。由此可以得知,六朝時期,百姓的生活仍然非常艱苦,但封建禮教對人民的束縛較弱,女子能夠拋頭露面做生意,這與當時的政治是有關聯的——六朝社會混亂,朝代更迭頻繁,統治者忙于組織自己的勢力,對于文化方面的控制還未顧及,所以對百姓而言,一方面生活艱難,另一方面思想卻開放。通過這兩首詩,即可窺見一斑。所以,吳聲曲辭從側面反映出當時的歷史現實,這是敘事性在文學中的巨大價值。
三、《子夜四時歌》的文學史影響
吳聲曲辭所代表的緣事而發、語言質樸、記錄現實的表達方式,對當時和后世文學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甚至影響了后世文學創作的思維方式。蕭滌非在其《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一書中談及:“南朝樂府,以前期民歌為主干,梁陳擬作,則其附庸。然不有此種擬作,則民歌影響,亦莫由而著。溯自東晉開國,下迄齊亡,百八十余年間,民間樂府已達其最高潮;而梁武以開國能文之主,雅好音樂,吟詠之士,云集殿庭,于是取前期民歌咀嚼之,消化之,或沿舊曲而譜新詞,或改舊曲而創新調,文人之作,遂盛極一時……”[4]由此可知,南朝的民間文學已形成一股詩歌思潮,極大地推動了文人詩歌的發展。
南朝時期的文人在接受樂府民歌的基礎上,沿用舊題擬作新聲,創作了大量文人樂府詩,將樸素的民間文學雅化、規則化,開始以文人的視角觀察并敘述人民的生活風貌。其中,《子夜歌》是數量最多、流傳最廣、唱和率最高的樂府曲辭,同時代出現的《子夜四時歌》《大子夜歌》《子夜警歌》等多首變調,僅梁武帝蕭衍一人,便沿用舊曲譜新辭,創制出7首《子夜四時歌》。樂府詩不僅從市井走入宮廷,還從江南地區深入江漢地區。《宋書·樂志》稱:“隨王誕在襄陽,造《襄陽樂》;南平穆王為豫州,造《壽陽樂》;荊州刺史沈攸之又造《西烏飛哥曲》,并列于樂宮。歌詞多淫哇不典正。”[2]607這幾篇作品即為“清商曲辭”類目下的“西曲歌”一類,是被朝廷樂官收集并整理后,進入宮廷音樂的樂府詩雛形。
吳聲曲辭的敘事模式,還對后代文學產生了重要影響。唐代著名詩人李白在仿照南朝樂府《子夜四時歌》的基礎上,創作了同名組詩《子夜四時歌四首》:
春歌
秦地羅敷女,采桑綠水邊。素手青條上,紅妝白日鮮。蠶饑妾欲去,五馬莫留連。
夏歌
鏡湖三百里,菡萏發荷花。五月西施采,人看隘若耶。回舟不待月,歸去越王家。
秋歌
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何日平胡虜,良人罷遠征?
冬歌
明朝驛使發,一夜絮征袍。素手抽針冷,那堪把剪刀。裁縫寄遠道,幾日到臨洮?
詩人分別以春、夏、秋、冬四時情景分別敘述了四件事——《春歌》采用了檃栝手法,將漢樂府民歌《陌上桑》的故事進行了改寫,以主人公秦羅敷在河邊采桑的事件為起因,將羅敷拒絕使君的對話語言“蠶饑妾欲去”等敘事因素在詩中得到明顯體現,敘事色彩濃厚;《夏歌》以紹興鑒湖夏景為敘事背景,講述了身為浣紗女的西施在若耶溪采蓮的歷史故事;《秋歌》寫戍婦為征人織布搗衣之事,運用了獨白式的語言描寫“何日平胡虜,良人罷遠征”,體現出該詩的敘事性;《冬歌》承接上篇《秋歌》,也是描寫戍婦為征夫縫制棉衣之事,詩中不僅運用獨白體的語言描寫,還加入了“抽針”“把剪刀”等動作描寫,敘事元素更加豐富。通觀四首詩,用四季形成組詩的串聯方式妥帖且巧妙,層次分明,結構嚴謹。
綜上所述,吳聲曲辭作為南朝樂府詩的典型代表,其敘事色彩是不容忽視的一個研究方面。它植根于當時的社會環境,又反映了相應的社會現實,并且在文學史上留下深遠的影響。
參考文獻:
[1] 房玄齡.晉書[M].北京:中華書局,1997.
[2] 郭茂倩.樂府詩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3] 李延壽.南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5:1696-1697.
[4] 蕭滌非.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M].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284.
On the Narration of Wu Dialect Poetry in the Southern Dynasties
XU Meng-jie
(School of Human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Jiangs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213101,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more than 470 Yuefu folk songs in the Southern Dynasty literary works. Among them, Wu dialect poetry has an absolute proportion. As representatives of Wu area literature, they show a distinct narrative color. This thesis intends to start from the origin of Wu dialect poetrys narrative, explore its narrative
performance in terms of content, structure and language, and analyze the historical influence of the narrative of Wu dialect poetry in the Southern Dynasty.
Key words: Southern Yuefu poems;Wudi literature;Wu dialect poetry;narrative
責任編輯??? 趙文清
收稿日期:2019-08-12
作者簡介:許夢婕,講師,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