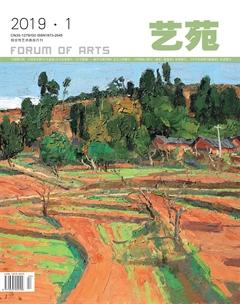短視頻形式與形象化內容:《如果國寶會說話》的變異修辭
姜常鵬
【摘要】 紀錄片的定義中蘊含其修辭表達的根基,后現代主義修辭學與廣義修辭學的出現也為我們從修辭學視野討論紀錄片的修辭藝術提供了可能性。紀錄片《如果國寶會說話》以短視頻形式和形象化的內容對接當下媒體融合的語境和觀眾的審美需求,在真實性基礎上使用擬人、演示、異語等多種變異修辭手段,把文物生動可感、鮮明直觀地呈現出來并取得了極好的接收效果,讓紀錄片領域的“媒體融合”有了一個更為具象和生動的樣本。
【關鍵詞】 短視頻;《如果國寶會說話》;變異修辭;距離;修辭格
[中圖分類號]J90? [文獻標識碼]A
百集紀錄片《如果國寶會說話》(以下簡稱《國寶》)自第一季播出以來便取得良好的口碑,第二季于2018年7月23日開播后也獲得極高的評分,播放量迅速過億。該紀錄片通過多樣的手段賦予文物人格化特征,以5分鐘的體量承載起厚重的歷史,既有效對接了當下媒體融合的語境,又恰切投合了接受者的心理狀態與情感情緒。其中值得思索的是,面對同樣的歷史、同樣的文物,制作者對紀錄片的形式、影像和聲音采取“反傳統”的調配、整合后,取得了與傳統文物類紀錄片大不相同的表達效果。我們認為,此種在真實基礎上對影像和聲音的調配可以看作為一種修辭活動,因為修辭的本質是思維層面的現象[1],其用來調配的語言、結構等不過是修辭思維的表現形式。如此,紀錄片《國寶》在形式與內容上采用了何種突破常軌的修辭手段就成為值得關注和討論的問題。
一、距離的協商:紀錄片與修辭
修辭作為一門古老的藝術,起初致力于探究各類演說技巧,古典主義修辭學的代表人物亞里士多德將修辭定義為“在每一種事情上找出其中的說服方式”。[2]142而后新亞里士多德主義修辭學把研究范圍轉移至文字作品,用以分析作品的修辭技巧和藝術特征,這與我國的修辭學相似。20世紀中后期興起的新修辭學則把修辭行為拓展至人類普遍的生存環境中,其推動者肯尼斯·伯克認為修辭因素存在于一切話語里,修辭現象無處不在。之后新修辭學轉向后現代主義修辭,其關注的對象也更加廣泛,幾乎包含一切文化形式和現象,如電視、廣告、電影、國家形象、戰爭修辭、行為修辭等。正如道格拉斯·埃寧格所說:“修辭不僅蘊藏于人類一切傳播活動中,而且它組織和規范人類的思想和行為的各個方面。人不可避免的是修辭動物。”[3]20這也為我們從修辭學視野討論紀錄片的表達方式提供了可能性,而且廣義上講,紀錄片似乎囊括了演說、言語和視覺等多個層面的修辭。
我們認為紀錄片的修辭性首先要從它的定義談起,因為其中蘊含著紀錄片修辭表達的根基。與修辭學概念的動態性一樣,紀錄片的定義在不同時期和地域也不盡相同,但歷史上針對紀錄片定義的各種討論其實大都圍繞格里爾遜在1930年代所提出的定義展開,即對真實事物的創造性處理,這也是迄今為止最經常被紀錄片研究者和制作者引用的定義。顯然格里爾遜是從自身的制作實踐中塑造了人們對紀錄片這個稱謂的看法,他把紀錄片當成一把鐵錘而不僅僅是一面反映社會的鏡子并用來“敲醒”大眾。紀錄片理論家布萊恩·溫斯頓詳細解析了格里爾遜的這一說法,認為其中的“創造性”是指向紀錄片作為藝術,“處理”指的是紀錄片的戲劇化,而“真實事物”則指紀錄片所處理的事實證據。說明格里爾遜所定義的紀錄片不是對事實的純粹紀錄,而是要以事實證據為基礎對某個論點進行詮釋,其要旨在于對事實素材的操作。但此類創造性的處理和操作并不會否定紀錄片的真實性,首先它們以事實為根底,其次對客觀世界進行主觀化解讀是人類的本能行為。比如當面對陶鷹鼎這一文物時,我們會產生可愛、萌胖、美妙等多種感覺,制作者同樣如此,但紀錄片的敘述只是以多種可能的方式重構了作為“幻象”的遠古器物,陶鷹鼎僅偏離了它在考古學上的意義進入到影像藝術中,而這種事實基礎上的“偏離”和“變異”正是紀錄片的修辭性所在,它重構的“幻象”即是修辭學中的修辭幻象。也可以普泛地說客觀世界一旦進入主觀視野,便具有了某種修辭化特征。[4]47所以紀錄片中的修辭現象并不是對真實性的否定,而是為了更多樣化地、令人信服地展示事實,對紀錄片中修辭手段的討論亦是建立在真實性表達的基礎之上。
比爾·尼科爾斯同樣認為紀錄片是對真實世界的創造性處理,而不是一次忠實的復制。紀錄片制作者往往把所拍攝的事實予以排列,進而建構自己對真實世界的觀察角度或論點,呈現的是一種修辭性回應。[5]36因此紀錄片文本、拍攝對象及接受者之間存有一條鴻溝將三者分隔開,否則受眾直接參與到真實世界中即可,并不需要透過紀錄片來認知世界。這三者之間的距離正是紀錄片修辭性的來源,也是形成紀錄美學的前提。法國修辭學者米歇爾·梅耶曾把修辭學定義為“是圍繞一個具體問題,個體們之間距離的協商”[6]8,將說話者、受眾及表達問題和回答時所用語言置于平等位置進行討論。由此紀錄片的修辭藝術可以理解為圍繞某一問題(論點)所造成之距離的協商,其中“距離”就是制作者、拍攝對象和接受者間的鴻溝,“協商”即為實現預定的表達效果而采用的修辭手段。
可見,紀錄片的修辭性源自再現世界、真實世界及觀眾之間的距離,但論點、距離、協商的形成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按照梅耶的說法就是:“個體之間的距離越大,激情介入的程度越小;距離越小,激情便越強烈。”[6]135此處所說的“激情”即是主觀性介入,對應紀錄片中“創造性處理”的問題,也即修辭手段的選擇和應用。而按照“距離”遠近,修辭手段通常被分為兩種,規范性修辭和變異性修辭,前者相當于陳望道先生所說的消極修辭,后者則與積極修辭相當。所謂規范性修辭就是從規范的角度來說明言語表達的修辭效果,它是以平實地記敘事物的條理為目的[7]35;變異修辭指的是突破常軌的、創造性的修辭手段,它是人們根據實際需要而采取的一些有效的、異于規范的表達方式[8]6,以生動地表現生活為目的,往往能夠產生新穎獨特的表達效果。若將此分類移入紀錄片領域,規范性修辭則相當于對事實的平實記錄,變異性修辭則是在真實基礎上采用的修辭手段。由此紀錄片敘述中的變異修辭同樣相對于常規修辭而存在,它的形成也是建立在對“常規”的變異上。本文論述的《如果國寶會說話》在呈現形式、語體和影像等表達手段中的變異修辭現象亦是相對于傳統歷史文物類紀錄片規范、嚴謹的敘事策略而言。
二、短視頻形式:語境的對接與意圖的投合
藝術作品的內容與形式是密不可分的,內容總要以相應的形式予以呈現,任何修辭活動也都無法脫離形式。陳望道說:“修辭上所說的內容,就是文章和說話的內容。修辭上所說的形式,就是文章和說話的形式。” [9]5紀錄片也是如此,其內容即是展示的事實,形式就是展示事實的形式。這既是紀錄片修辭性的來源,也決定了其修辭活動的多樣性,因為赤裸事實的本身不會表示任何意義,只有以相應的形式陳述它才會產生意義。紀錄片的修辭活動中,其內容和修辭須依托一定的形式,例如紀錄長片、紀錄短片、系列紀錄片或直接電影、真實電影等。伯克把修辭形式定義為對欲望的激發和滿足[10]49,即為接受者創造一種期待并予以滿足,他認為許多形式上的模式也可以產生欲望并引導受眾積極參與,僅通過形式的創新能夠與接受者取得同一。尤其在網絡新媒體興盛并與傳統媒體進行融合之時,單以內容美學為主導的原則不足以支撐紀錄片的發展,正如席勒提到的:內容只能對個別起作用,只有形式才能對人的整體起作用。[11]482
紀錄片《如果國寶會說話》擯棄以往文物類紀錄片“長篇論述式”的呈現形式,轉而以分集和季播方式,采用小而精的短視頻形式對國寶予以展示即是一種變異的修辭形式。雖然此種突破常規的形式并非首創,如先前出現的微紀錄片《故宮100》《上海一百》《城殤》等皆以短視頻形式對歷史、文物進行陳述,但《國寶》的成功之處在于它妥善調和了修辭形式與修辭內容的矛盾狀態,這主要表現于兩方面:修辭形式同語境的對接;修辭形式與表達意圖的投合。
在修辭活動中,依賴特定的語境突破現行規范而創造性地運用修辭形式往往能夠增強作品的表現力,獲得意想不到的接受效果。參照伯克的理論就是變異的修辭形式首先能夠誘使接受者注意或參與到作品中,并有可能被新穎的呈現形式所感染,而后能夠與這種形式所表達的內容和觀點達成同一。對于紀錄片《國寶》而言,順應媒體融合的趨勢,借用時興的短視頻形式,符合新媒體語境下受眾短時間內閱讀信息的需要,恰切的適應了網絡傳播短、平、快的特性。隨著移動媒體的快速發展,如抖音、快手的流行,人們以碎片化、快節奏、可拆解、淺顯易懂、板塊形式為特征的接受習慣早已形成,而《國寶》以五分鐘的體量、快節奏的敘述、網絡化的語言和精美的畫面讓“國寶”活起來,不僅雅俗共賞,適宜網絡媒體傳播,也能把古、今相連,有效傳達文物背后的意義,其采取的短視頻形式能夠同新媒體的特質和觀眾的審美習慣實現無縫對接,成為一種可供多類媒介、不同受眾共享的形式。例如《國寶》每季由25集時長5分鐘的短紀錄片組成,它們既可單集點播,也可連集播放。但是與內容的拼貼不同,形式上的拼貼特征并不會產生新的意義而影響紀錄片原本的表達意圖,短視頻形式的采用及其拼貼特征更多的是為了迎合新媒體語境下受眾移動、跳躍的接受習慣和網絡媒體碎片化、互動性的傳播方式。
其實,紀錄片的制作借用短視頻的思維和樣式同樣存有弊端。首先時長的縮短擠壓了思考的時間與空間,觀眾或許會以直觀感性的狀態讀解呈現的事物,而得到的則可能是一種缺少判斷的感性認知;其次它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紀錄題材與內容的選擇。像《故宮100》《城殤》等短視頻式紀錄片,其選題多是靜態的、適宜在共時性上進行多角度描述的,如文物、建筑、歷史、文化,很少對現時事件的發生過程予以呈現。因為與虛構電影不同,紀錄片不是一種可以極度濃縮和升華的藝術形態,而現時真實的呈現正需要時間的積累與過程的展示,否則就無異于新聞短片。但是反過來講,短視頻形式的靈活多變性也恰好彌補了此類題材靜止、乏味、無趣的缺欠,以短時長、精美的鏡頭和較快的節奏對事物進行靈活呈現,很好的投合了媒介融合環境下大眾審美習慣的變遷。這使得紀錄片《國寶》在形式層面迎合新媒體特性的同時亦能承載起較為厚重的歷史和文化,避免形式上的淺層閱讀特征延伸至內容層面,如第二季《鷹頂金冠飾》一集里在五分鐘內通過多樣的修辭手段不僅展示了文物本身,還引申出草原民族與農耕文明的對峙和交融,揭示文物背后的歷史文化。這樣,迎合新媒體語境的短視頻形式與展現華夏文明的表達意圖在《國寶》的修辭活動里實現對接,讓紀錄片領域的“媒體融合”有了一個更為具象和生動的樣本。
三、形象化內容:生動可感與鮮明直觀
如前所述,藝術作品的內容和形式如同一對矛盾的兩個側面,不能截然分開。修辭活動同樣不能離開內容來講形式,也不能離開形式來講內容。[9]5前文討論了紀錄片《國寶》采用的短視頻形式,下文主要論述其內容的表達手段。馮廣藝在《變異修辭學》一書中認為:“共時意義上的言語變異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一個方面就是修辭格的運用,所以變異與辭格是緊密相連的。”[8]225法國美學家迪·馬爾塞斯也認為,修辭格就是通過一種特殊的變異而有別于其他講法方式。對紀錄片而言,修辭格的選擇與使用涉及的即是真實內容的表達手段。也如陳望道先生所說:“語言的內容,對于寫說的內容只能算是一種形式的內容。”[7]31那么,紀錄片《國寶》所采用的短視頻形式是宏觀上內容的呈現形式,具體至內容的表達手段時指涉的則是修辭格的使用。但是與虛構的藝術作品不同,紀錄片修辭中的辭格以真實為根底,力圖更形象生動、令人信服地展示事實。《國寶》相比于以往的文物類紀錄片,采用了更多的變異修辭手段,如比喻與擬人、演示與動畫、異語和移時等,這種真實性基礎上使用的修辭格不僅能夠準確傳達理性的信息,還可以生動鮮明的表達內容,傳達出美感信息,進而適度的增加信息量。
(一)生動可感:比喻與擬人
比喻是最常用的修辭方式之一,紀錄片文本中的比喻是在真實事物基礎上的同義選擇和轉化。《國寶》中介紹里耶秦簡時把它說成像“戶口本”“身份證”;串聯絲縷玉衣的紅線被比喻為“紅色血脈”;講述秦始皇兵馬俑時把大地比喻成鏡子,而將陶俑描繪為“鏡中折射的帝國”等都使用了比喻辭格。可以看到比喻能夠更為具體、形象地傳達創作者的意圖,縮小事實與文本的距離,同時也可以將抽象深奧的事理說的淺顯具體,把靜止的文物描繪的生動可感,再如《霍去病墓石刻》一集里用“閃電”來比喻驃騎將軍閃耀而短暫的一生。比喻本質上是通過某一相似性的特點把兩個不同的事物聯系在一起,紀錄片文本中構建于真實基礎上的比喻能夠擴大和增深所展現事物的印象,利于調動接受者的興趣,同時經過接受者的再造性想象還可以擴添展示對象的內涵和意義。這讓出現在紀錄片文本中的文物“生動活潑”的同時又不失嚴肅高雅,符合當下觀眾的價值需求。
擬人就是將物擬作人,把沒有生命或思想的事物當作人來描寫,并賦予它們以人類的特性。紀錄片《如果國寶會說話》的片名即是一種擬人化的表達,意在讓文物如同人類一樣擁有自己的性格,并能夠進行自我講述。而且《國寶》在史實的基礎上也實現了這一表達效果,例如陶鷹鼎的萌胖、人頭壺的凝望、漆盤上的喵星人、漢代石刻的生命與志向,《陶鷹鼎》一集中“假如陶鷹鼎會說話,它也許會告訴我們六千年前它在熔爐內外的日日夜夜吧”,《擊鼓說唱俑》一集里以第一人稱“自賣自夸”的陶俑等均是擬人化的表達。其實比擬本質上就是把事物從一個世界移入到另一個世界里進行描繪,尤其擬人手法將物我打通、合一后,賦予表現對象靈動性,自然會使接受者深受感染。但是紀錄片文本里比喻、擬人等辭格的使用要真實、準確地抓住本體和喻體、擬體之間的相似點,不能違背事物本身的邏輯,否則不但得不到相應的表達效果,還會觸及紀錄片真實性的底線。
(二)鮮明直觀:演示與動畫
西塞羅在《論公共演講的理論》中曾提到“直觀演示”這一修辭手段,認為當某個事件被詞語描述得好像事情就在眼前發生那樣生動就是直觀演示。[12]136而在以影像和聲音進行“演說”的紀錄片里,被拍攝的事物已然生動地呈現于觀眾面前,不需要過多言語描述。由此我們認為紀錄片修辭中的演示即是為更加直觀明了、生動形象地展示事物或原理而進行的人為的模擬演示,它不是現實流程中自然發生的,而是作為紀錄片的修辭手段特別拍攝和制作的,可以分為人物演示和動畫模擬兩種。
紀錄片修辭活動中的人物演示與動畫模擬分別同漢語修辭格里的示現和圖示相似,前者致力于把未來的、過去的或想象中未發生的事繪聲繪色的描述出來;后者則是行文中用圖形符號代替語言中的詞語。在紀錄片《國寶》的敘述中廣泛使用了演示和動畫兩種修辭手段,《二十八宿圓盤圭表》一集里石云里教授對圭表用法的演示,《戰國商鞅方升》里商鞅立木的真人扮演,《霍去病墓石刻》中驃騎將軍駕馬馳騁的再現等皆是運用了人物演示的修辭手段;而人頭壺注水、流淚,后母戊鼎制造工藝的推測,《鷹頂金冠飾》一集中草原游牧民族與中原農耕人們對峙、交流的過程展示等都使用了動畫模擬的手法。這兩種非常規的變異修辭手段從其表達效果來看新穎生動、直觀形象,能夠讓靜止乏味的文物“活”起來,給觀眾帶來過去文物類紀錄片中或是博物館里得不到的體驗,縮短紀錄片文本、受眾與文物間的距離,從而構建出“重疊區域”[13]35,使接受者形成一種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覺,可以在文本的讀解中獲取更多快慰和審美情趣。
當然紀錄片《如果國寶會說話》中也存在其它的變異修辭現象,例如用“顏值”形容跪射俑,說趙佗是“待機時間最長的王”、趙眜是“玉粉”,把龍山蛋殼黑陶杯的制作工藝喻為“黑科技”,用“小確幸”形容辛追夫人等,此種網絡流行語的使用類似修辭學中的異語辭格和移時辭格,而《素紗單衣》一集里以現代模特展示衣物的形態又有些許旁逸辭格的韻味。這些辭格的使用都為紀錄片的敘述增添了活力,改觀了過去文物類紀錄片的冗繁,讓文本生動而富有情味,但它們也被適度的限制于一定的界限內。因為紀錄片的變異修辭應當遵循適度的原則,制作者可以追尋形式的多變和內容的生動可感,只是不能逾越真實的底線,消解紀錄片應有的高雅和嚴正。紀錄片的修辭活動應在“真實性”的限度內進行,若跨越了這個臨界點,量的變化會引起質的變化,不但得不到相應的表達效果,還會讓紀錄片丟失其魅力和本性。
結 語
紀錄片的變異修辭是在真實性基礎上,相對于規范性修辭而言的,《如果國寶會說話》的敘述中也使用了許多規范性修辭手段,如布局、邏輯推導與視點轉換等,它們多是對事實的平實記錄和展示,以求多角度客觀地呈現文物,也屬消極修辭手段。變異性修辭即是對此類規范性的偏離和變異,但這種偏離也有正負之分,正偏離是創新,對紀錄片真實性的表達起積極作用,負偏離則是反面的,不適用于紀錄片的修辭活動。紀錄片文本中變異修辭的作用和目的就如同伯克說的那樣,不再是尋求在每一件事上發現可行的說服方法,而是為了解決分歧、消除隔閡、縮短距離、促進共同的理解。[14]紀錄片《國寶》突破文物類紀錄片的傳統范式,轉而在真實性基礎上使用短視頻形式和多種辭格,符合新媒體語境下受眾的接受習慣和審美需求,精確處理文物、紀錄片文本、接受者之間距離的同時取得了預想的表達效果,成為“未來紀錄片”的一個開端。[15]
參考文獻:
[1]張宗正.宏觀視野下的修辭行為[J].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5).
[2](古希臘)亞里士多德.修辭學[M].羅念生,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6.
[3](美)肯尼斯·博克,等.當代西方修辭學:演講與話語批評[M].常昌富,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4]譚學純,朱玲.廣義修辭學[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5](美)比爾·尼科爾斯.紀錄片導論[M].陳犀禾,等,譯.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15.
[6](法)米歇爾·梅耶.修辭學原理:論據化的一種一般理論[M].史忠義,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
[7]陳望道.修辭學發凡[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
[8]馮廣藝.變異修辭學[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9]康家瓏.趣味修辭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10]鄧志勇.修辭理論與修辭哲學:關于修辭學泰斗肯尼斯·伯克研究[M].上海:學林出版社,2011.
[11]朱光潛.西方美學史[M].北京:中華書局,2013.
[12](古羅馬)西塞羅.西塞羅全集·修辭學[M].王曉朝,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13]鞠玉梅.社會認知修辭學:理論與實踐[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1.
[14]溫科學.當代西方修辭學理論的發展與創新[J].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6).
[15]常松.專訪梁紅:《如果國寶會說話》只是“未來紀錄片”的一個開端[EB/OL].廣電時評(微信公眾號),2018-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