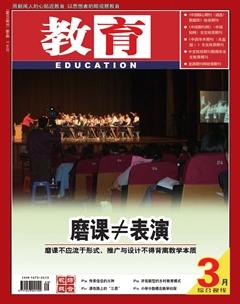習作與批改
蔣伯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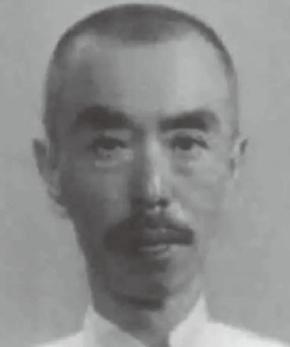
所謂“批改”,也不限于作文;周記、筆記、書信以及文法練習的改正和批評,都應當包括在內。周記、筆記,由教員批改,是各校常有的事,不過簡略些而已。書信的批改,卻是少有的。我在浙江教書時,常鼓勵學生和我在假期內通信,把原信批改了寄還。這辦法,我覺得很有效益。文法黑板練習,除當場改正錯誤外,可以把所以要改的理由,口頭說明,這就等于“批”了。
最重要的,自然是作文的批改。關于“改”,我以為多改不如少改,增加字句不如刪減字句。有些熱心改文的教員,往往把原語抹去一大段,改上幾行,或增入幾行,這是勞而少功的。體裁語氣不合,層次結構不好,固須改正;文法上用詞造句的錯誤,以及錯字別字,尤必須加以改正。改作文,不是要把它們改成杰作,是要把它們改成文從字順的文章。“批”是批評,不但要指出原作的錯誤,而且最好能說明其所以然。例如“步”字何以下半從“少”是多了一點,“盜”字何以上半從“次”是少了一點;根“本”之本何以不當作“本”,“來”往之來 何以不當作“耒”;“徘徊”“彷徨”本都是疊韻組合的復詞,以雙聲關系而演變的,何以使用時又有區別;“我在紙上寫字”可以改作“我寫字在紙上”,何以同用“在”字,句式亦同,“我在書房里寫字”不能改做“我寫字在書房里”,都須使學生明了其所以然,以后方不至重犯這種錯誤。
所以照理想,每有一字一句的改動,必須有一個說明所以然的批語。這些零碎的寫在眉端的批語,叫做“眉批”,眉批是愈多愈細愈好的。至于“總批”,寫在篇末的,則以批示全篇為主。或內容思想上須加批評補充,或結構層次上需要指導斟酌,或全篇最大的疵累是什么,以后作文須注意何處,力求改進,都應在總批中說出。如其不需要,總批盡可以省卻。那些科舉時代傳統的四字八字、不著邊際的總批,我以為大可不必。標點應在初中一年級學習,以后批改作文,盡須留意,校正其錯誤。最好把多數學生常犯的錯誤,記錄下來,于學期末了,再提示一次;學期考試,不妨據以命題,促使注意。以上所說都是消極方面“批”的。反之,如果有好的句語、好的篇章,也得提示出來;舊式濃圈密點的方法仍可采用,批語中也可加以贊揚。特別好的作文,可以揭示或傳觀,以資觀摩,以示鼓勵。進步快的,習作努力的,應公開加以獎勵;反之,退步的,不努力的,應加以規誡。
還有一種方法,我曾試驗過,且覺有效。那時,我在某中學只教一班國文(因兼別的教課和職務),學生只有三十人。我先規定各種記號,告訴學生。在作文中有須改正的地方,先加上各種記號,發交學生在課內自己訂正。改得多的,須重抄,連原本同繳。批改定在下午課畢后或星期日,改某生的文,即把某生邀來,坐在旁邊,和他問答、商量,邊改邊談。改完后,然后細加眉批,當面發還。這辦法,可以養成學生自己修改作文的能力與習慣,可以增進學生對批改的注意與了解。不過,師生多費點時間而已。
批改不限于教師。同學、朋友也都可以擔任這種工作。韓愈、賈島“推敲”的故事,是大家都知道的。作者自己修改,尤覺親切。歐陽修做《書錦堂記》,寫好送出,又追回來,首二句各加上一個“而”字(“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做《醉翁亭記》草稿已成,又把首段抹去,只用“環滁皆山也”一句,這些故事,也是大家都知道的。歐陽修嘗說作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所謂“商量”,即是批改。不但師友,自己也得常和自己商量。周遲明先生所舉的例,教師從不改文,而這班學生中竟有成績很好的,安知不是同學或自己修改的效果?“新詩改罷自長呤”,古代詩人、文人對于自己作品的一再修改,原是常有的呀!
從前,我和朱自清、劉延陵二先生同在某校教國文。朱先生和我是努力批改作文的;劉先生卻從不批改,而且常笑我們,“可憐無補費精神”。有一天,校工替我們買了一包花生米來,包的紙便是我仔細批改、三天前發還學生的作文。這正給了劉先生一個有力的證據。我被兜頭澆了一杓冷水,頓時涼了半截。朱先生卻鼓勵我,認為這僅是極少數的偶發事項,不能以此概括全體學生;而且這或者正可證明我們底批改不很得法,不夠努力,所以不能引起學生底注意。
(選自《中學國文教學法》北京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原載于中華書局194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