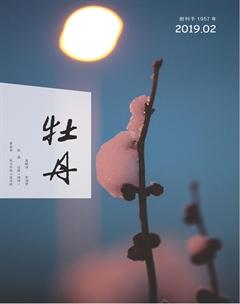論國畫創作過程的特殊性
王曉桐 霍澤群
國畫的歷史源遠流長,它是中國繪畫藝術的核心,反映和融會了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和審美情趣,體現了中華先民對自然、社會及與之相關聯的政治、哲學、宗教、道德、文藝等方面的認識。本文主要從“九朽一罷”與隨機應變兩方面探討國畫創作的特殊性。
九朽一罷式的創作方法,正是建立在對視覺印象進行反復修正以求表現精確酷肖的目標基礎上的。它代表了早期中國畫尚未建立自身審美特征和形式特征時必然會產生的觀念。但問題并不那么簡單。畫種與畫風的區別也是一個關鍵的因素。人物畫對畫面形象的要求很嚴,而山水、花鳥畫相對松動些,九朽一罷的創作方式在人物畫中應用當然較多。直到今天,特別在進行大幅人物畫創作或是有形象特指的人物畫創作時,反復起稿還是十分必要的,當然未必要朽九次才罷休,這只是一個約數而已。此外,工筆畫與寫意畫之間對形象的要求也不一。工筆畫的創作過程較為理性,要求步驟明確而且反復次數也多,對畫面形象結構要求交代清晰無誤。它的“九朽”功夫當然要求較高,寫意畫追求過程中的時間屬性,揮灑不太受限制而結構交代可以適當地從“意”,它就不必多此一舉,故人們在寫意花鳥畫中很少看到有打稿的現象,而工筆花鳥畫幾乎無畫不“朽”。
寫實要求還是個主導因素。相比于山水花鳥畫而言,人物畫的寫實要求與生俱來;相比于抒發性靈的寫意而言,工筆畫的寫實要求即形象的清晰度要求較高;相比于中晚期文人畫講格調、講意境、講主體精神而言,早期繪畫的重形似的傾向也極明顯。寫實、重客體再現,始終是“九朽一罷”式創作方式生存的溫床。
分歧產生于寫意繪畫的崛起之后。山水、花鳥畫形式媒介以及它們對現實觀察的特殊方法,為寫意精神提供了最好的馳騁天地。強調主體、強調意趣與精神的自然抒發,強調畫面形式的人性化與人格化,使得古典的九朽一罷式反復修改顯得特別蒼白無力。更關鍵的是,它缺乏一種意趣流露所必須依存的時間“流”。它缺乏感情在萌生、展開、再現、尾聲等各部分前后銜接連貫的鏈。種種繪畫法則的靜止狀態和孤立狀態,會使得寫意畫家很難將之貫串融會進自己的感情激流中,因而使畫面顯得牽強湊合,索然寡味。
在宋元以后的悠悠千年中,寫意畫籠罩一切而工筆畫茍延殘喘,山水花鳥畫至高無上而人物、釋道、寫真種種屈居卜僚,中國畫的發展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期,從觀念到形式都成果累累的時期。雖說人們在其中也看到了某種程度上的單調與新的守成不變,成就畢竟是顯赫的。大革命大動蕩帶來的超長時間的穩定前行,對于中國畫后期歷史而言,這是一個最明顯也最值得總結的特征。新的守成不變與穩定前行,從宏觀的角度去看當然未必是好事,但它不也從反面啟示人們:臨機應變式的創作方法自身具有極強的適應性和極完美的成熟性嗎?對于穩定不變延續千年這一事實,不也應該看成是歷史老人對它所作出的評價嗎?
時間的銜接、線與點之間的銜接并非都是那么有條不紊的。就像人的心理活動也不會很條理化一樣。感情抒泄到一定的積量之后會有某些突變,它意味著對原有形象思維定向的一種轉變,這是就其大者而言。于是,原想追求流暢便捷的畫面效果,在一瞬間由于某個點或某一條線乃至某一塊顏色的特殊性而導致轉向,或許轉成以下銜接的新的意義:蒼茫渾樸或厚重華滋的新的效果。從躁動到平和、從輕飄到拙重、從濃艷到淡泊,轉變可以從一點一畫開始,也可以從某一局部開始。如果人們從正常的順向銜接中能找到一種穩定不變的基調的話,那么突變式的銜接轉換則意味著墓調的轉換。基調在這里,指的是藝術風格、形式語匯、審美類型等多方面的、能決定作品總體的那些元素。
人們在這里看到的,是時間的展開而不僅僅是空間的靜態確立。九朽一罷式的時間過程,顯然是被割裂的、零碎而缺乏秩序的,隨機應變式的時間展開則具有非常清晰的軌跡和有序性。“一點為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準”,這是孫過庭在《書譜》中的樞機之談,它對中國畫同樣具有形式上的意義——當然不是“書畫同源”之類的泛泛之談,而是從時間這一宇宙生存基點出發,又以相似的審美觀作為支撐的一種吻合。表面上看,它是偶然的,然而從根本點上說,兩者存在深層的必然性格。由此可以引出一個非常有意義的研究課題:書法對中國畫的外加影響。
強調隨機應變的靈活姿態,使畫家對空問塑造的觀念發生了巨大變化,空間本身的內涵也發生了變化。作為視覺印象的繪畫空間,本身應該有著明確的形態標志。但在中國畫中,形態的明確性被規律性所替代。明人李開先在《中麓畫品·序》中有一段頗發人深思的議論:“萬物之多,一物一理耳。惟夫繪事,雖一物而萬理具焉。”
重理重象不僅使空間觀念發生了變化,而且使空間這一概念有了新解。瞬間視覺空間印象的單純性,被反復交疊的視覺印象的綜合性所取代。一形要具萬物之理,本身就具備了萬物交疊綜合后所求得的共數的特點。而空間的從靜止直觀到印象交迭,有如反復多次曝光所產生的特殊印相效果,每一次曝光所得的視覺印象自成畫面,重迭多次又構成更復雜也更有情趣的畫面,這種視覺印象的空間性格,具有運動的交叉重復的豐富性格。
其次是“目不見絹素,手不知筆墨”。要塑造形象空間,但又要不見不知,要忘記這是一個可能存在的空間。欲正先反,欲擒故縱,正是中國人的哲學觀。人們在此中看到了時間的滲透力。從某種程度上說,“目見絹素,手知筆墨”式的創作,是典型的九朽一罷式的靜態空間的標志,而“不見”“不知”倒證明了空間自身的不規定性和不靜止性。一切都需要在時間“流”中決定取去,空間構造也不例外,臨機應變是空間構成的唯一手段。
空間印象重迭的復雜性使九朽一罷的創作模式顯出它的貧乏性,因為它是建立在瞬間空間固定印象獲得確認的基礎之上的。空間印象構成的不定向性使九朽一罷的創作模式顯得單調和老套。因為它的結果在預料之中,缺乏突如其來的激情和喜出望外的興奮。由是,中國畫毫不猶豫地在為擺脫它而努力。“畫梅謂之寫梅,畫竹謂之寫竹,畫蘭謂之寫蘭”(元湯里《畫鑒》),一個“寫”字點出中國畫的時間特征。堆砌、藻飾、雜湊者被決絕地拋棄,而貫氣、取神、一意旋折、一瀉千里的創作要求卻被提到突出的地位上來。臨機應變的“寫”的性格,正是在九朽一罷的“做”的風格對比下顯示出它的寶貴性。無疑,這是一種只有中國畫才有而為其他畫種望塵莫及的特殊性格。
關于中國畫形式中感情元與邏輯元的關系問題,從一個根本的立場出發進行思考,形式所反映的客體是一種固定的存在。它的邏輯性格——形、光、色的有序構成不言而喻,形式自身的存在也是一個事實,對創作者而言,它的“規范”與“規定”的邏輯特征也不言而喻,它們都屬于邏輯元的內容。而畫家本人的創作激情、心理活動、審美情緒等,卻不是一個凝固不變的實體。它每時每刻都在變幻并要求得到釋放。感情元與邏輯元的關系,說到底就是主觀與客觀(對象客體、形式客體)之間的關系。通常,客體總是對主體施加某種限制,而主體也總企圖打破這種限制。在控制與反控制的矛盾斗爭中,一些畫家采取拋棄客體、唯主體獨尊的方法,行動畫派之流即是這類方法的典型;另一些畫家則對客體頂禮膜拜,努力使主觀創造力屈服于對客觀形象的再現,照相現實主義之流即是此中的楷范。中國畫在悠悠千年以前即己考慮到這樣有深度的深題。古人最后采取了不絕對的辦法,以主體的原動力,以客體為形式構成的媒介,在前者中保存了旺盛的創造力,而在后者則保存了形象法則與形式法則的存在意義。
因此,中國畫家個人與形式、對象之間的矛盾從來也沒有達到不可調和的地步,個人的創造力在形式中總是能很好地得到尊重。感情元作為主動方面,即便是在相對恒常的文人畫形式中也決不會失去它的價值。在一個互相對立、沖突的領域中,人們看到中國畫的特殊性格——協調。
(河北農業大學藝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