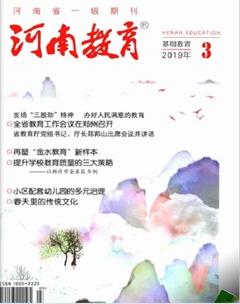春天里的傳統文化
叢培業
春天,冰雪融化,萬物萌動;春天,和風拂面,桃紅柳綠;春天,生機勃勃,詩情畫意……
常言道:“一年之計在于春。”我們能有足夠的想象力建構、勝出這一“計”嗎?在農耕時代,隨順四時,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人們在天人合一的狀態中,尋求五谷豐登。面對自然界的萬千變化,中國古代智者與勞動人民通過生產實踐形成二十四節氣的知識體系。就整個春天而言,從立春開始,經雨水、驚蟄,到春分、清明,直至谷雨,人們遵循節氣的變化,開展與農耕生產相匹配的勞動生活,由此衍生出豐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
在農事上,人們遵循“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的原則。立春,意味著每年農事的開始,忙碌于春耕也就成為中國古人一種基本的生存狀態。作為傳統的農耕大國,古人在開啟農業生產時踐行十足的儀式感。每逢立春,皇帝和地方官員都會通過一系列“迎春”禮儀向老百姓“勸耕”,老百姓也通過“迎春”禮儀祈愿一年風調雨順、五谷豐登、萬事順遂。古代皇帝還有“親耕”的傳統。據說漢文帝劉恒就是第一位親自耕作的皇帝,他在即位之初接受賈誼“躬耕以勸百姓”的建議,多次“親耕以率天下之民”。此后,這一做法得到歷代皇帝效仿和支持,尤其到了明清兩代,每年的農歷二月二,皇帝都要到先農壇行祭農耕籍之禮。到了康熙年間,“演耕”作為法律被確定下來,每年春季由皇帝親自率領王公大臣扶犁耕地,舉行“演耕”之禮。無疑,在農業社會,農耕活動是國之大計、立國之本,而且它在歷史的沉淀中,也使具有中國特色的農耕文化日漸豐厚。
經過一冬的蟄伏,春天萬物生長、生機勃發,美麗的愛情故事總是與春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周禮·地官·媒氏》中就有記載: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仲春二月是男女結婚的日子。為方便青年男女的感情交流,古代還設定了固定的春游節日——三月三“上巳節”,它又被稱為“中國的情人節”。《詩經·鄭風·溱洧》記載:“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放眼望去,在清波蕩漾的溱水、洧水之畔,鄭國的“士與女,殷其盈矣”,這些來郊游的鄭國男女,站得到處都是,“秉蘭”相會、笑語“相謔”,互相贈送著象征愛情的“勺藥”,尋找自己的愛情。《詩經》中記載的愛情故事也發生在郊游期間。在《國風·鄭風·出其東門》中,“出其東門,有女如云”,出了城東門,滿眼都是花枝招展的郊游女子。“出其闉闍,有女如荼”,走出了外城門,只見女子多如花。由此可見,當時鄭國人喜春游,每年春天許多男士便會利用這個機會尋找自己的“真愛”。在一起結伴郊游的過程中,姑娘小伙兒相互了解,兩情相悅,互贈信物,約定終身。
應該說,農耕生活與愛情故事都是人類社會得以延續不可或缺的必要元素。除此以外,在古人的春天里還有怎樣的生活呢?“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古人似乎更深諳此道,他們迫不及待地走出家門,讓盎然的春心與復蘇的自然相遇,與草長鶯飛的春天相擁。其中賞花是不能少的,“勝日尋芳泗水濱”“萬紫千紅總是春”“若待上林花似錦,出門俱是看花人”。探春踏青與歷代文人墨客有著不解之緣,他們吟詩作賦,抒發春游感懷。這一生活情趣可以追溯到先秦,費著的《歲華紀麗譜》中說:“二月二日踏青節,韌郡人游賞散四郊。”杜審言《和晉陵陸丞早春游望》:“獨有宦游人,偏驚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白居易《錢塘湖春行》:“孤山寺北賈亭西,水面初平云腳低。幾處早鶯爭暖樹,誰家春燕啄新泥。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陰里白沙堤。”古人踏青,內容豐富,觀賞山川風光,游覽名勝古跡,進行野餐會飲,狩獵,放風箏,蹴鞠,不一而足,令人神往。
清明節是祭祖掃墓的日子,是中華民族紀念祖先的傳統節日。而這種祭祀活動有著悠久而深厚的歷史,反映著中國倫理道德的規范與要求,印刻著“孝”文化的精神訴求與深遠影響。夫子言:“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這些都是中國傳統祭祀文化的重要依據。千百年來,人們在這個“氣清景明”的日子里,上墳掃墓,祭祀祖先,向已逝的先人莊重地奉上思念與敬意。
談及祭祀就不能不說到“修禊”之事。修禊,是古代傳統民俗。季春時,士人百姓都到水邊嬉游,是古已有之的消災祈福儀式,后來演變成中國古代詩人雅聚的經典范式,其中以發生在東晉會稽郡山陰城的蘭亭修禊最為著名。王羲之在《蘭亭集序》中記載:“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公元353年的三月初三,40多位賢人雅士歡聚蘭亭,觀賞山水,飲酒賦詩。王羲之匯集各人的詩文編成集子,并乘興作《蘭亭集序》,文采燦爛,雋永典雅,書法更是遒勁剛健,氣勢飄逸,被后世推為“天下第一行書”。
關于“修禊”之事,《正字通》:禊有二,論語:浴乎沂。王羲之蘭亭修禊事,此春禊也。《論語·先進》“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一章,四個弟子各言其志。曾晳說:“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對這段話,人們大都把它理解為“暮春三月,換上春裝,五六位成人,六七個孩童,到沂河里洗澡,在舞雩臺上吹風,一路唱著歌回家”。其實,此中別有深意,請注意這段話的人員構成,“冠者”與“童子”,暗含“焉知來者不如今”“后生可畏”的意蘊,正是儒家生生不息、剛健弘毅的旨趣。“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浴”,受沂水之教,即沐浴孔子之德教,習禮樂,立于禮,成于樂。“雩”,祭祀之臺,沂水之畔,預示在此地的活動及性質。“詠而歸”,詠歌而祭,隨后歸家。
正是因為曾晳將夫子之教深植于心,有效表達,描繪出雍雍穆穆、王道樂土之情景,所以,才會有“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孔子之喟然也認證了儒家經典《學記》中的“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思想,這也是孔子人生追求的真實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