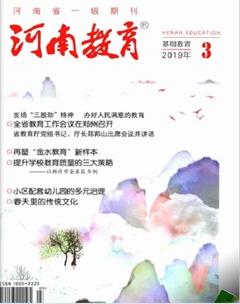初入北京師范學校
冉乃彥
1953年,為響應“共青團員去當小學教師”的號召,懷著要當優秀小學教師的愿望,我來到了北京師范學校。在北師,一般稱高年級的同學是師哥師姐,稱低年級的同學是師弟師妹,同年級的同學相互則叫“師平”。
北京師范學校是名副其實的小學教師成長的搖籃,解放前培養了老舍這樣的文學大家,解放后培養了劉厚明、從維熙等青年文學家。當然,最多的還是小學教師。
學校坐落在幽靜的端王府夾道8號。踏著青石臺階,通過一扇磨磚對縫、鑲有精美磚雕的校門,就可以進到里面。圖書館是木質結構的二層樓,在此曾經拍攝過《早春二月》等電影,重要的景點有“月牙池”“海棠齋”“練琴房”等。
我在初中畢業時身高只有1.53米,那是因為吃不好(有時候吃塊白薯就算一頓飯),睡不好(開夜車復習功課),又不重視鍛煉身體。到了北師后,情況大有轉變:伙食好,營養有保證;有嚴格的作息制度,睡眠有保證;每天早上和大家一起在官園體育場長跑,運動有保證。所以,我一年就躥到了1.73米,舊衣褲明顯變短了。(見右上圖,最右邊站立的是我)
借助這張老照片,我介紹一下北京師范學校的領導和學生干部。
前排就座的左一是史文炳老師,他負責學生思想教育和黨支部工作。左二是白主任,他負責總務工作。左三是德高望重的晁湧光校長。左四是王勝川主任,負責全校的教育教學工作,他在學生中有很高的威望。他的講話很有激情,常常贏得學生經久不息的掌聲。他后來創辦北京工讀學校,又調至教育部工讀司擔任司長。左五是尹福庭,大師哥,學生會主席,學生時代入黨。我旁邊是一年級的馮世忠,團總支干部。后排右四是田玉坦,團總支干部,后來是北京第一實驗小學校長,退休后去廣東辦學。田玉坦右前方是薛秀英,團總支書記,學生時代入黨。白主任后面的是我的大師姐李伯英,生活福利部部長,工作上對我幫助很大。
師范學校不交學費,包吃包住,每月還有文娛活動費。當時學生中家庭經濟困難的居多,大多數人都肯吃苦,學習努力,責任心比較強。這也成了我們這一批教師的一個特點。
記得新入學的一年級共8個班,4個男生班、4個女生班。男生班的第一、第二班是應屆初中畢業生,第三、第四班多數是年齡比較大的,有的已經工作,甚至結婚生子了。剛入學,100多名男生都住在一個“百人大齋”里。我離其中一個門最近,剛開始幾乎夜夜失眠,因為開門關門聲不斷,夜風陣陣,直撲床鋪。好在不久,每個班分了一個宿舍。我們的宿舍叫“海棠齋”,因門前有一棵海棠樹而得名。十幾張雙人床密密麻麻,安排得十分巧妙,每個人都有進出的通道。
師范生的課,與普通高中有區別,音樂、美術課時比較多。音樂課重視教學生技能技巧,彈琴是一項重要內容,大家也都認真練習,琴房雖然多,仍然供不應求。平時我們只能在老師發明的一種“鍵盤板”(木板上畫有黑鍵、白鍵,但是不可能彈出聲音)上練指法。師范學校取消了數學、外語(我這時候開始自學俄語;若干年后,為了取得大專學歷,又自學了高中全部數學,出于興趣還接著自學了微積分)。
學校還開設了教育學、心理學和兒童文學課(由趙德南老師講授),這都是我們喜歡的課程,這些為將來做一個優秀教師提供了知識儲備。我買了《蓋達爾的道路》等書籍,讀了不少兒童文學作品,還試著寫了一點作品。
北京師范學校很重視專業思想教育,經常組織我們接觸兒童學習活動,聽師哥師姐作報告,看蘇聯電影《鄉村女教師》。整個學校的氣氛是積極向上的,大家都為將來能從事教育事業為榮。作為年輕人,想到一輩子要去教書育人,內心油然產生出一種神圣感。
讓我沒有想到的是,一入學,學校就安排我到學生會去工作,擔任生活福利部副部長。作為師范學校,這個部門很重要。因為師范生長期生活在學校(有一些遠郊學生,星期天也在學校),吃喝拉撒睡樣樣都需要學校考慮周到。我印象最深的是伙食問題。我經常去大廚房,和大師傅們都很熟。這個大廚房每天要供應近千人的一日三餐,就像打仗一般:吆喝聲此起彼伏,動作快而不亂。我還學會了“起屜”的活兒——滿是米飯、饅頭或者包子的大籠屜(直徑一米多),必須由兩個人從熱鍋上迅速抬下來,如果動作慢了,很容易被高溫蒸汽燙傷。
大師傅們對自己的工作很自豪,他們常常告訴我:“同學們吃得好,大師傅才能直起腰。”
當時沒有擴音器,學生會通知事情也很別致。先到大食堂的一個角,請附近同學們齊聲喊:“同學們,請安靜!”然后我才扯著嗓子喊:“今天下午5點,各班生活委員到學生會開會。”要在大食堂的四個角都重復喊一遍,然后再到其他小食堂去喊。
當時學生伙食不錯,尤其是肉炒飯最受歡迎。大師傅把一大簸籮炒飯抬進食堂,立刻就被圍得水泄不通。偶爾也有糧食緊張的時候,我記得有一次,全天只吃蠶豆,每人一大海碗,開始還覺得很好吃,沒想到第二天腮幫子腫痛,吃飯也困難。畢竟這是新中國建國初期,這些困難大家都能理解,我們要與國家同甘共苦,一心想著早日走上工作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