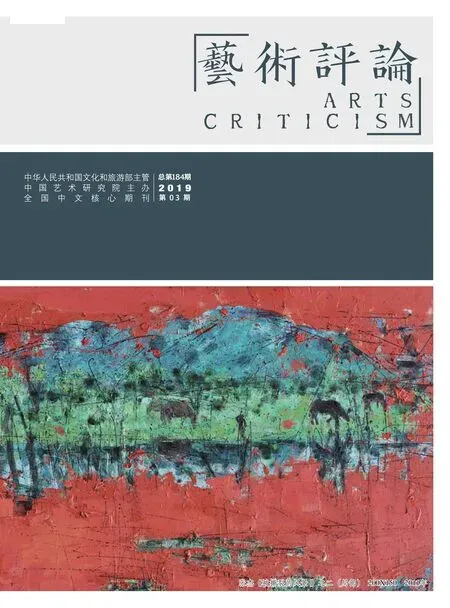以作品鏈接中希,讓經典對話世界
——中國國家話劇院《阿伽門農》觀后
景俊美
毫無疑問,埃斯庫羅斯的悲劇之美影響了整個世界,其“悲劇之父”的美譽名副其實。多少觀眾因為他的劇作而產生了“卡塔西斯”效應,進而實現了人生態度的轉變或對生活世界的認知。埃斯庫羅斯的劇作《俄瑞斯忒亞》是現存唯一的古希臘“三部曲”,它由《阿伽門農》《奠酒人》和《復仇女神》組成,其中的《阿伽門農》是較早地揭開人類社會由野蠻邁入文明這一巨大歷史轉變的扛鼎之作。那么,后世之人是如何看待和演繹埃斯庫羅斯之《阿伽門農》這部希臘經典的?不同的創作者和演繹者有不同的闡釋方式。近日,由中國國家話劇院和希臘國家劇院聯合制作、希臘國家劇院藝術總監艾夫斯塔修斯·利瓦西諾斯執導、在國家話劇院上演的中希雙語版話劇《阿伽門農》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一、跨中希、鏈古今的藝術構想
作為文化和旅游部直屬的國家藝術院團,中國國家話劇院一直以創作和演出高質量、高品位的古今中外優秀劇作為己任,堅持“中國原創、世界經典、實驗探索”的創作理念,較好地發揮了國家藝術院團的代表、示范與導向作用。曾經排演的《薩勒姆的女巫》《死無葬身之地》《哥本哈根》《紀念碑》《戰馬》等國外優秀劇作,成功地實現了對世界經典的學習與借鑒。在一個個具體劇目的創作與排演中,國家話劇院不斷探索與國外藝術院團的合作形式。2018年王曉鷹執導的中希雙語版話劇《趙氏孤兒》是此次中希雙語版話劇《阿伽門農》的前傳,該劇在希臘國家劇院的成功上演,激發了希臘導演利瓦西諾斯的創作興趣。他從《趙氏孤兒》中看到了文化、文明以及語言的沖擊力,進而對《阿伽門農》有了自己的定位,于是我們得以欣賞到兩種文化再一次的“有趣相遇”。

《阿伽門農》劇照 王雨晨攝
此次利瓦西諾斯導演執導的中希雙語版話劇《阿伽門農》首先是一次中方、希方的合作。創作團隊以希臘方為主,包括導演本人、舞美設計、燈光設計、編舞各1人,另外還有飾演克呂泰墨斯特拉和卡珊德拉的兩名演員。演出方以中方為主,除了國王阿伽門農、歌隊、守望人、埃奎斯托斯、侍女、傳令官等演員外,還包括現場的配樂組合。舞臺上希方和中方不同國度的演員分別講著自己的母語,不同的語言孕育出不同的藝術表現形式和文化張力。雖然排練時有語言的障礙,但是在創作團隊和演員的反復磨合中,觀眾的所觀、所聽、所感覺到的或對話或獨白是在一個氣場里面的藝術震撼。與演員表演相得益彰的是現場演奏出來的音樂氛圍,它們又是另一種中西融合,打擊樂、電吉他為主的西洋樂器,配以琵琶這一中國傳統樂器的代表,配樂的創新、融合與劇情同進出,在必要的時刻渲染出適宜的情緒,使演出進入一種渾然不覺的情愫。如果說上帝為了防止人類的智慧所向無敵而制造了不同的語言,那么在情感的深處、人性的本質以及音樂的律動中,人類依然找到了相通的介質。有研究者指出“埃斯庫羅斯的劇作善于渲染氣氛而不是戲劇沖突”,那么音樂在這里所起的作用便恰到好處。這大概正是導演所希望傾訴的該劇在表現形式上的一種現代性。于是,在語言和音樂的激蕩中,觀者可以獲得一種特別強烈的間離效果。
其次,雙語版話劇《阿伽門農》的演出是一次貫古今的藝術創作。古希臘悲劇的震撼力主要源于悲劇的嚴肅性,即亞里士多德所認為的:“悲劇的目的是要引起觀眾對劇中人物的憐憫和對變幻無常之命運的恐懼,由此使感情得到凈化。”悲劇中那難以調和的帶有宿命論的沖突,是人類從神話時代走向理性世界的見證。阿喀琉斯、阿伽門農、赫克托爾、奧德賽、俄瑞斯忒斯等悲劇里的英雄,他們的原始感性不附加任何道德條件,卻映現著古希臘人的處事法則:“世界是由一些神圣的法則所規范的,這些法則和規律是不可違背的,所以,人類的一切行為必然有其后果。錯誤判斷所導致的行為必然產生不愉快的后果,這便是以后希臘觀念中的一個基本觀點——秩序法則。”后世的人類生活印證了秩序法則的意義,它不僅存續在原始人類的記憶里,而且存續在他們創作的藝術作品里。今天,一代又一代、一個又一個國家的藝術創作者一次次去觸碰古希臘悲劇,卻不再僅僅為了重復古人的“秩序”,相反,他們要表達與時代、與生命、與自身相激蕩著的當下生活。比如希臘導演提奧多羅斯·特爾佐普羅斯于2016年也執導過一部《阿伽門農》,劇中的肢體語言、鏡像表達和隱喻謎面實現的是導演的創作意圖:“在《阿伽門農》中,埃斯庫羅斯揭示了人類靈魂和思想的黑暗面;在那種契約背景下,人類靈魂往往通過暴力的方式來表現自身。”
二、藝術呈現的獨特意義與豐韻表達
無獨有偶,此次國家話劇院推出的中希雙語版話劇《阿伽門農》所要表達的文化內涵也不外乎人對悲劇、對人性、對人自身的當代性思考,于是我們看到舞臺上有關藝術和語言、創作方法與表演技巧、民族與文化的東西格外凸顯。
在創作過程中,導演利瓦西諾斯特別強調《阿伽門農》的語言性。他以英國來舉例,指出:“一個英國演員若掌握了莎劇的表演風格,他的每句臺詞一定用特殊的臺詞處理方式處理重點詞和邏輯重音。”但就現實的翻譯文本來看,一般的文學翻譯只是將文本翻譯出來,未必有鮮明的行動性。而當語言沒有行動性時,文本對演員來說是沒有力量的。所以,移植于其他語言的舞臺藝術首先要選好翻譯文本、選對翻譯人員。有了這樣的基礎,原作中的神韻才能得以鮮活呈現。中希雙語版話劇《阿伽門農》的舞臺呈現,得益于著名希臘語翻譯、導演、制作人羅彤的加入。作為《阿伽門農》首位中文譯者羅念生的孫女,羅彤與父親羅錦鱗、祖父羅念生一家三代都從事著希臘研究和翻譯工作,是真正的“希臘通”。這次演出羅彤擔任劇本翻譯,特別注重了原文的詩體美,并一定量地加入了一些現代人能夠理解的語言元素。《中國藝術報》的采訪中說:“今天呈現在舞臺上的《阿伽門農》已經有很多版本了,羅念生在1961年出版的老版本是根據弗倫凱爾1950年牛津版本古希臘原本翻譯,而此次《阿伽門農》新版的翻譯是采用了1957年的牛津版本,這個版本是利瓦西諾斯導演親自為羅彤提供的,同時也借助了K.Ch.米利斯的古文轉譯,就是翻譯成現代希臘語,因此這個版本的《阿伽門農》劇本是集合了古希臘語與現代希臘語共同翻譯而成的。”所以,演出中觀眾能夠聽到臺詞里既有類似“宙斯,是他引導凡人/走向智慧之路,并立下有效的法則,告訴我們/苦難乃智慧之母”這樣的詩性語言,也有“我忍不住第一個跳起舞來/因為主子的幸運就是我自己的幸福/這火光的信號就好像我中了頭彩”之類的當代語匯。除此之外,中希雙語的交織使用,也是導演彰顯創作意圖的一個載體。即便是最萬能的翻譯也未必能百分之百地傳遞來自母語的那種抑揚頓挫和優美動聽,那么我們就直接聽它的最真實。事實上這樣的選擇在當下并不鮮見,比如很多觀者在欣賞好萊塢佳作時只愿意聽原聲,也是這個道理。
舞臺調度上,利瓦西諾斯結合舞美設計婀勒妮·瑪諾蘿普露和燈光設計阿勒科斯·阿納斯塔蘇的藝術構想,加入了很多肢體語言的藝術表達。比如該劇一開場是守望人從睡夢中醒來,雖然他最終看到了“光”。但是從睡夢中醒來到看到“光”是有一個過程的,這個過程需要語言的動作性表達,更需要肢體的直觀性傳遞。有時候演員因為對題材的陌生,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去“急于表達”,這樣反而會破壞劇作的流動性。所以導演強調要表演一個過程,要記住“他”作為守望人是一個普通的人,演員演的是“從不知會發生”到“發生了”這樣一個過程。利瓦西諾斯導演提倡“戲劇是身與心的結合”,所以他贊賞演員在行動和實踐中去體會、摸索和創造,進而用身體去思考、去感知。通過這次合作,阿伽門農王的扮演者杜振清的感受很強烈,他覺得:“這部戲不像我們平時看到的話劇,它運用了大量的肢體語言,許多爬、滾、跪的動作,配上悲壯的臺詞,對于中國觀眾來說是一個全新的體驗。”如果語言和聲音讓世界太嘈雜,請不要忘記那讓人沉靜、讓人思考的肢體表達。中希雙語版話劇《阿伽門農》不僅采用了中、希雙語,而且采用了音樂、肢體等第三種、第四種語言去詮釋藝術經典的魅力,去張揚那種發自內心、來自原初、共享于未來的巨大的藝術感召力。

《阿伽門農》劇照 王雨晨攝
三、中希合作的意義與需要審慎的問題
雖然中國國家話劇院和希臘國家劇院的合作并非首次,但是此次合作的意義依然是非凡的、不可估量的。誠如導演利瓦西諾斯所說的:“這部作品是中國和希臘國家劇院的一項非凡實驗,國家話劇院應當是先鋒藝術的代表,用中希雙語呈現一部劇作,讓觀眾聽見兩種語言,看見兩種表演流派、兩種類型的演員,是個冒險的嘗試。”一語中的,導演的話包括兩重含義:一重是合作的重要意義不容忽視,另一重是合作中也確實存在著冒險性與不可預測的東西。
首先,該劇賦予了劇作以現代性,并實現了中國藝術的國際意義。《阿伽門農》作為一部世界經典,很有必要被中國觀眾了解,也有必要讓中國觀眾看到來自其他國度不同的演繹方式,這新的演繹方式以一種開放、包容和探索的姿態進行,同時,它又是對此前合作過的《趙氏孤兒》合作精神和創作狀態的一種延續,真正激蕩起中國和希臘這兩個有著悠久文化傳統的國家在戲劇藝術領域文化深度交流與融合的潮流。一如荷馬與孔子一樣,他們不僅僅只屬于自己的國家和民族,他們還是屬于全人類和世界文明的偉大人物。正是因為這一次又一次的國際性合作,戲劇從業者會越來越明晰藝術的價值,對戲劇本質意義的理解與體現也會有更加豐富和深刻的體會,同時還能看到、學習到國外團隊的一些新的藝術創作理念,包括先進的管理經驗以及舞美燈光服裝化妝的處理手段等。視覺是人類認識世界的主要方式,舞臺上舞美和燈光的意義便是強化這種視覺沖擊力。比如該劇的舞美形式感強,主平臺宛如一把利劍,舞臺上還有許多具有象征意義的元素:不潔的床榻、充滿誘惑卻暗藏危險的石頭、鏡像意義的水簾等,引起人的遐想,也賦予該劇以多維性和現代意義。
當然,探索性的創作未必能全部實現期待中的圓滿,有得有失是常態。如果只沉浸在一時的掌聲之中,創作者迷失的不只是今天的收獲,還有屬于未來的各種可能。北小京對《阿伽門農》有很深的期待,他認為“雙語演出本身并不是障礙,障礙在于雙方演員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演繹《阿伽門農》這個悲劇劇情,而沒有進入到‘悲劇性'”,而“悲劇性”的意義在于“跨越了時代與地域的鴻溝,直抵當代人心”。筆者以為,當下的文藝評論界高度贊譽多于誠摯批評。而真正有責任心的評論,往往來自于那些愛得深沉的人。因著這種“愛”,其“責”中往往包含著建設性的方向。除了這種“悲劇性”的不足之外,筆者還擔心類似這樣的實驗性演出不要只是一時新鮮而成為過往。希臘導演走了,希臘演員走了,我們是否還能一樣延續甚至提升戲劇語言的詩性和韻律感,是否也能夠在今后的創作中探索出既不過度奢華又具有高度形式感和充滿藝術張力的舞美效果。任何一個事件都不是孤立發生的。好的藝術創作就像《俄瑞斯忒亞》三部曲一樣,英雄的悲劇會在觀者心里激蕩起無法控制的悸動。
一人之成長,有一人之特別軌跡。一院團之成長,亦有一院團之特別軌跡。中國國家話劇院在“中國原創”“世界經典”“實驗探索”的創作理念下,創作了一批又一批經典劇目,《阿伽門農》將是其特別軌跡中的一筆記錄。多年之后,或者百年以至于千年之后,該劇若能像《阿伽門農》劇作一樣被傳承和延續,則該劇的意義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