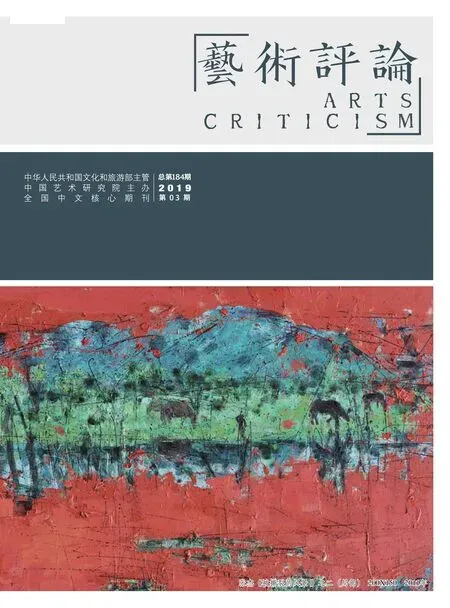“誰在那?”
——哈姆雷特的意念與凝視
林偉瑜
隨著話劇演出成本的日益升高,商業價值對當代話劇制作的支配性幾乎無可抵擋,即便是具有先鋒戲劇傾向的作品也無法不顧慮市場和觀眾,因為過于挑戰觀眾的審美習慣(特別是讓觀眾看不懂)將會造成極高的市場風險。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中,李六乙稱得上是異數。他過去“惹得”觀眾與劇評人對他惡言相向的作品不在少數,究其原因,除了一直存在讓觀眾“看不懂”的問題,亦和他多次大膽“顛覆”經典有關。此外,他的作品也經常與當代觀眾認為一出“好看”的戲劇應有的原則背道而馳。在凡事講求快速、用過即丟、連付費只消瞬間的消費社會里,一出戲要好看,除了故事性與戲劇性強、演員陣容之外,快節奏(或至少不能慢)與幻變萬千的舞臺視覺更是關鍵。畢竟在影像世紀中,提供易消化的內容與眨眼就換畫面的視覺索求,是每日便利生活的一部分,不能否認這種生活習慣形塑了當代觀眾的審美口味。相對于此,李六乙作品不但有不易得出結論的內容,而且慢得出奇,慢得令當代人坐不住。
比起李六乙早期作品的令觀眾摸不著頭腦,他在2018年導演的《哈姆雷特》延續了2017年創作《李爾王》時保留經典完整性的做法,也就是他不僅維持了情節的完整度,戲中臺詞與人物表演之間也保持較多的一致性,觀眾不致感覺看不懂。不像在過去作品中,李六乙為了實踐其“純粹戲劇”理念中,所欲達到的戲劇多重時空和人物多重意識狀態,常讓人物表演與臺詞各自表達不同內容(甚至場面調度也表達著另一個內容),這種臺詞、人物、場面調度的“分裂”狀態,雖然可以創造意識與時空的復雜多元狀態,但卻是觀眾看不懂的主因,同時也是李六乙作品被不少人視為是具有“解構”和“顛覆”特征的證據。
雖說李六乙有以上看似極大的改變,但此次《哈姆雷特》的舞臺呈現,仍充滿了他在早期實驗性較強的作品所發展出來的導演語匯、手法和特征,尤其是:“一景到底”的舞美、舞臺多重時空的并置(借由不在場人物于場上的游走、演員間的觀看與被觀看關系)、演員的多重意識狀態(舞臺上的演員/人物并不只存在單一戲劇時空中)、“純粹戲劇”的戲劇觀(意圖直接表現人的多元與復雜的精神意念,而非外在的戲劇行動)。
根據我的觀察,他近年的大劇場作品,較少有早期作品中存在上述提及的“分裂”情形,原因恐怕并非是李六乙在固有的創作策略中遇到困境,所以放棄“解構”和“顛覆”,而更多是因為近年來他在表演實踐上獲得了某種突破。他已不再需要借由臺詞、人物、場面調度的分裂,來創造他要追求的多重時空和意識,因為他只要透過演員的表演即可完成,不必再大費周章、拐彎抹角地改造劇本。這可能也是為何李六乙近年的大劇場作品大多能保留完整故事,以及人物表演與臺詞間不過度分裂的主因。故事線的保留,使得觀眾對他的作品接受度增加了,并較大程度允許不同觀眾以不同欣賞策略來“閱讀”他的作品。較敏銳的觀眾可掌握到其導演語匯所欲傳達的內容;而無法突破寫實主義式戲劇的觀眾則有敘事線可依附。
《哈姆雷特》舞臺是李六乙作品典型的一景到底的設計。舞美設計是他合作多次的德裔瑞士籍設計家Michael Simon,在結構上極度簡約,僅由一個轉動的圓盤和可移動的懸吊銀球組成。兩個元素均極具動能,在燈光變化的輔助下,僅由轉盤高低轉動以及銀球上下左右移動,便能創造豐富的視覺意象,搭配上梵音般的女聲,在演出中創造出宇宙行星、星際運行的意象。在這種視覺意象和聽覺感受中,時間感與空間感是消逝的,永恒感遂生,劇場的形上氛圍就由這些非文字和非戲劇性的元素傳達給我們。此外,另一個聲音元素——京胡更多是用來創造戲劇性氛圍,除了可創造緊張懸疑,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慢速拉弓的京胡音所創造的人物情感和戲劇性感受。李六乙對這兩個音樂元素的選擇可謂是相當本質性的,與舞美設計一樣,簡單卻豐富,并具穿透性,一則傳遞悠遠、恒常的精神性,另一則予人具體的戲劇情感。
我傾向把上述舞臺燈光聲音等元素視為李六乙為此劇設置的導演“規定情境”。在這個具有宇宙感和永恒感的規定情境中,李六乙雖保留了故事情節、臺詞順序與人物關系,但是從舞臺呈現來看,這些傳統上用來創造戲劇性與行動的元素,似乎并非他要表現的重點。仔細觀察,李六乙所加重處理的,是一段段的獨白及其相應的視覺意象。那些制造戲劇性的慣有元素,如懸疑、糾葛、沖突、危機、人物性格等,某種程度被弱化,而人物的對話很多時候被獨白化了,這尤其體現在重要的戲劇時刻,人物的主要臺詞多被處理為直接對觀眾講述,這使得呈現的重點不在劇中人物間的關系,而在臺詞意涵與人物的意識/意念。這里我們還可發現,李六乙以兩種基本方式來傳達這些時刻中的戲劇、臺詞與人物的意涵,一是創造具有象征性的舞臺調度與視覺意象,二則是演員表演進入心理或意識層次。尤其是哈姆雷特的幾段重要臺詞,如“在果核里想象自己是無限大疆域的國王”“去修道院吧”(對奧菲利亞)、“在與不在”的獨白。而不只哈姆雷特,克勞提斯(如懺悔)、母后與奧菲利亞(如格楚描述奧菲利亞的死亡)都有此現象,就連霍拉旭、雷厄提斯的重要臺詞也是這樣處理的。
這種“獨白化時刻”的處理,讓我們更多看到的是人物的意念或意識,而不是人物的行動,某種程度來說,這是一種頗為現象學“還原式”的表達方式,把具體環境、細節懸置起來(或說隱而不論),僅集中看人意識中的經驗流所展現的是什么。
從這里來討論李六乙版《哈姆雷特》中人的意識流動與多重意識時空的并置是有意義的。其開場頗耐人尋味,哈姆雷特(胡軍飾)戲一開始便躺在圓盤上,極度昏暗的燈光中輕輕說出“誰在那”后,便開啟了整場戲。這場戲原無哈姆雷特,此句臺詞本是哨兵所說,雖然哈姆雷特整場戲都在場,但他并沒有跟這場的戲劇時空實例化交流,其表演更多展現出一種沉思與默想狀態。由此,舞臺上明顯有兩個時空:第一場的戲劇時空與哈姆雷特意識中的時空。而在最后一場比劍后哈姆雷特倒地死去后,又再度起身,說出“誰在那”,暗示先前的戲劇過程是人物或演員意識中想象之物。類似藝術概念與手法其實在過去李六乙的作品頗為常見,從稍早的《原野》《穆桂英》《我這一輩子》,到近年的《小城之春》《櫻桃園》等都可見到類似的蹤跡。

《哈姆雷特》 劇照 曹山攝影

《哈姆雷特》 劇照 史春陽攝影
在第一幕第三場雷歐提斯與父親、奧菲利亞告別的戲中,本不應在場的哈姆雷特也在場上。這場戲可看到李六乙典型的多重意識時空并置的處理,也就是導演與演員的表現重點并不在執行這場戲的外部戲劇動作,而是在這場戲中人物各自意識狀態的展現。這場戲的戲劇時空是,雷歐提斯前往法國前與妹妹、父親的告別。當雷歐提斯提醒奧菲利亞小心哈姆雷特的求愛之時,在表演上,奧菲利亞卻是看著哈姆雷特,顯示她處在自己的意識時空而非該場的戲劇時空,而當波洛涅斯對雷歐提斯耳提面命之時,雷歐提斯的意識卻在妹妹身上,而不在與父親的對話中。而此刻在場上游走的哈姆雷特以及他對其他人物的觀看,則提醒我們,這一切又或是哈姆雷特意識中的產物。至此,短短幾分鐘的戲在場上至少創造了四個意識時空,說明了李六乙只需靠演員的表演手段,而不需要修改劇本就能達到舞臺多重時空的呈現,不像他過去在《原野》中嘗試要創造這種多重意識時空時,需要大幅剪接劇本內容才能達到。
這種多重意識時空的創造,又迫使演員不能只為單一戲劇行動與時空服務,他/她的表演必須具有雙重性甚至多重性,與其對戲的演員同樣的也需具備多重性。尤其李六乙對于在表演上創造多重性的要求,并不透過當代西方劇場所偏愛的外在肢體展現,而更多要求演員將意識狀態轉換為一種精神存在狀態來呈現。這是一種較為內在和內隱的表演,需要演員在舞臺上具備高度的專注力始能達到,這對演員是困難的挑戰(在話劇表演上有同樣追求者,如林兆華)。若進一步問,為何林兆華、李六乙等這類導演都想追求人物和演員的雙重或多重性?我尚無法完全了解這個問題(雖然林兆華、李六乙有各自的理由)。初步推測,他們更多地將演員的表演狀態本身視為一種戲劇的存在,而這種存在狀態是他們戲劇追求的核心或理想境界。而這種境界通常是存在于表演的自由境界,亦即:于每場演出中能表現演出當下的存在,才是創造真實,并且要避免每日再現式地扮演人物的單一戲劇時空,落入重復所帶來的虛假表演。加上當代戲劇對于戲劇時空表現的繁復性早已超出單一的戲劇時空,過去斯坦尼式的人物塑造方式對他們已不敷使用,而傳統上以“跳進跳出”方式來變換人物身份,卻又被他們視為仍是虛假且單一的表演而被摒棄。李六乙的《哈姆雷特》中多是他合作多年的演員,他們對于這種雙重與多重意識并存的表演(或說不只存在人物之中的表演)可說是相當熟悉,尤其是濮存昕、盧芳、荊浩、苗弛、強巴才丹等,他們對于創造表演多重性已有豐富的經驗。
我認為李六乙版《哈姆雷特》最高明的處理是《哈姆雷特》最后的場景,也是此劇令我感到最為驚艷之處。吊詭的是它幾乎不在戲劇情節之內,在這里李六乙搭建一個從戲內溢出/延伸到戲外的中介:在哈姆雷特將死的最后一段臺詞中,母后、國王、雷歐提斯等在舞臺上死亡的位置,正好圍繞哈姆雷特形成一個三角。在這段臺詞中,死去的母后、國王、雷歐提斯緩緩站起,以魂靈之姿凝視哈姆雷特講述此段臺詞與倒下死去,靜待他來到他們的世界。當哈姆雷特再度坐起身說“誰在那”時,他已非哈姆雷特,那么他是誰?或許是哈姆雷特的靈魂,或許是胡軍,也或許是劇作家李靜在評論此劇時所說的“大寫之人”。
當胡軍從哈姆雷特的死亡中站起來,舞臺轉盤緩慢轉起,所有演員在移動中逐漸形成群體;胡軍逐漸遠離他們走下圓盤與之形成對角,與劇中所有死去的魂靈相互凝視,在一切愛恨情仇之后,越過生命門坎,這一忽見五蘊皆空、平靜如水卻意味深長的凝視,在視覺意象上的宗教性非常強烈。當舞臺如同宇宙中的行星運轉般旋動起來,哈姆雷特之靈從《哈姆雷特》世界中解離出來,并以手臂推動圓盤舞臺,將其他人送出觀眾視野,轉盤在此刻具有多重意涵,既是哈姆雷特的世界,亦有人類的命運、全宇宙等意涵,帶領觀眾進入對《哈姆雷特》的后設/元觀看視角。
對我來說,全劇最重要的高潮是在最后哈姆雷特的獨白。當胡軍把圓盤的正面再度推到觀眾眼前時,他走上圓盤舞臺到銀球下方,開始“to be or not to be”的獨白。此段臺詞原在劇中已說過,但當再度被重述于整個故事結束后,李六乙才讓它真正的意涵顯現出來,讓它轉變為越過死亡之后的生命提問,使其意涵得以從故事中超脫出來,超越了原情節中哈姆雷特個人對自身遭遇和命運產生疑惑的意涵,進入到更具普遍性層次的、對人之存在的提問。從這里來看,該劇將“to be or not to be”譯為“在還是不在”顯然有其深意。

《哈姆雷特》 劇照 史春陽攝影

《哈姆雷特》 劇中“在還是不在”的獨白 曹山攝影
胡軍這段獨白的表演很值得討論,我們可看到他的表演更多是脫去了人物,回復到人的樣態。這讓此段獨白的表現有了新的突破:讓哈姆雷特從歷史、特定的軀殼中破繭而出,平實地以“人”(或說是內在自我)的存在表達,使得這段獨白的意涵具有了更為廣闊的力量。我認為在這段表演中,胡軍甚少有“扮演/演”的痕跡,而更多的是以演員之姿在表達屬于胡軍/自我的存在。他以一種穩定、自我審視式的表達來呈現,讓這段獨白以一種未被多余的、添油加醋的戲劇化表演“污染”,清澈如水般地將意念直接傳遞給觀眾。這只能是透過一種極為內隱、高乘的表演,因為演員(胡軍)自身的存在便是要被傳達之物。而由此我們意外發現莎翁這段臺詞蘊含的生命與宗教性體悟的可能性,當我首次看到這段表演的時候受到極大感動,并認為是我所看過的當代中國話劇中稀有的表演(濮存昕在《建筑大師》中展現過類似的表演)。這也讓我聯想到,為何彼得布魯克、契訶夫等戲劇家有時不喜愛過于戲劇性的表演,或許是戲劇化的表演有時對于“真實的表達”是一種無益的添加物。胡軍的這種表達方式當然與李六乙的純粹戲劇理念有關,即希望表演可以直接傳達精神意念。只是面對多數觀眾抱著期待“情感豐沛”“有力量”“惟妙惟肖塑造人物”才是好表演的標準,就像在吃食中習慣了添加物帶給我們“美味”之后,對某些貴在本質的食材,也容易喪失品嘗、覺察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