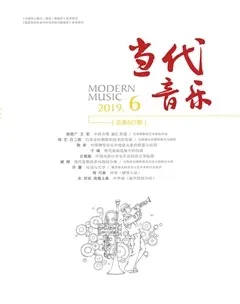昆曲藝術(shù)與箱鼓的舞臺演繹融合
[摘 要]昆曲在中國璀璨的戲劇藝術(shù)殿堂上有著重要的地位,坐擁“百戲之祖”的榮譽稱號。就其發(fā)展歷史而言就長達600多年,而完美的表現(xiàn)以及獨特的韻味更是讓其獲得了觀眾們的無限青睞;就其表演方面而言又具有較為厚重的唯美寫意之感;且在審美上又頗具浪漫主義的色彩。源于秘魯?shù)倪h方樂器箱鼓正因各種原因而傳播于世界各個國家,它以其外觀簡約、攜帶方便、音色變化豐富正被越來越多的專業(yè)打擊樂手與音樂人認(rèn)可,也被應(yīng)用在各種舞臺表演中。本文通過對兩種舞臺表演形式的介紹以及探究,對兩種表演形式融合后的舞臺效果進行探究。
[關(guān)鍵詞]昆曲;箱鼓;舞臺演繹
[中圖分類號]J607"[文獻標(biāo)識碼]A"[文章編號]1007-2233(2019)06-0105-02
一、昆曲的歷史沿革及寫作手法
昆腔或者昆劇是昆曲的兩個別名,而昆曲則是中國的傳統(tǒng)戲劇表演藝術(shù)種類里的主要代表之一,亦是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主要代表之一。因為昆曲的主要發(fā)源地為當(dāng)今的江蘇昆山地區(qū),此乃取名為昆曲的主要原因。在其發(fā)展的早期是以臺下清唱的形式為主,與舞臺無關(guān),直至梁辰魚的出現(xiàn)才將昆曲從臺下班上了臺上,其創(chuàng)作的名傳奇《浣紗記》就是昆曲的經(jīng)典篇目之一。該曲采用了傳奇文學(xué)和新聲腔表演藝術(shù)特色相結(jié)合的做法,將昆曲的雅致淋漓盡致地在舞臺上展現(xiàn)出來,昆曲這種戲曲門類也因此大受歡迎,故而,當(dāng)時社會上的文人雅士以及民間的樂師都爭相為昆曲創(chuàng)作相應(yīng)的傳奇以及學(xué)習(xí)昆曲的板眼與伴奏。由此,昆曲逐漸被更多人知曉接受,并逐漸趨于成熟。[1]與此同時,現(xiàn)實主義以及浪漫主義兩種寫作手法成了為昆曲創(chuàng)作傳奇的主要方法,兩種方式各有特色,皆為昆曲的文學(xué)劇本提供了真善美三者相融合的藝術(shù)特色,前者主要是偏向于現(xiàn)實生活真實感受以及場面的刻畫及描寫,后者主要是通過使用一些象征或者想象等寫作方式來刻畫人物以及抒發(fā)情感。[2]昆曲的代表名作有很多,主要有《牡丹亭》以及《桃花扇》等作品,都是其中的優(yōu)秀代表。
二、昆曲的舞臺表演藝術(shù)
昆曲需要將曲中所塑造的藝術(shù)形象以及人物的真摯情感在進行舞臺表演之時細(xì)膩精致地表現(xiàn)出來,加之昆曲讓人熟知的劇目中,在內(nèi)容上很多都與夢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3]昆曲中基于現(xiàn)實而又虛擬的人物形象以及真摯而細(xì)膩的情感,是現(xiàn)實主義以及浪漫主義兩者相結(jié)合后產(chǎn)生的意會效果,而通過婉轉(zhuǎn)又纏綿的唱腔可以將其情感抒發(fā)出來,作為舞臺藝術(shù)的昆曲,從曲調(diào)、旋律這個角度上看,在當(dāng)時達到了中國戲曲音樂的最高峰。音樂的內(nèi)在曲律的變化有三種:一是民歌小調(diào),二是板腔體,三是曲牌體。昆曲是戲曲劇種曲牌最高的顯示,音樂上達到極致。在表演上,細(xì)致入微到極致。昆曲是“無聲不歌”,就是所有聲音包括念白都要有歌唱和韻律的成分;“無動不舞”,所有的動作都要有舞蹈的成分。這種極致,是其他劇種所不具備的。正是因為這樣,昆曲才成為地方戲?qū)W習(xí)的對象,也被稱為“百戲之祖”。
三、“床頭柜”——箱鼓的前世今生
(一)箱鼓的歷史沿革
近幾年,一種獨特的世界民族打擊樂器——箱鼓(Cajòn)逐漸走入大眾視野。箱鼓又叫作木箱鼓、卡宏鼓、卡宏木箱鼓,原文為Cajòn,是西班牙文,意思是木箱子。正如單詞所譯,這個打擊樂器外觀看起來就是一個普通的木箱子,好像并無特別之處,但所謂“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這種打擊樂器歷經(jīng)百年的發(fā)展而長盛不衰,而且從外形到內(nèi)部結(jié)構(gòu)越來越完備,之所以能夠火遍全球,自然有其過人之處。[4]
關(guān)于箱鼓的由來,百年來眾說紛紜,也有很多傳說。早在15世紀(jì),非洲的尼日利亞等地就出現(xiàn)了方形、三角形的木質(zhì)盒子,只不過當(dāng)時并沒有大面積地發(fā)展、改良成為像非洲鼓一樣重要的打擊樂器,而是非洲勞動人民手中的一樣普通玩具。真正的箱鼓原型,傳說是于19世紀(jì)在秘魯沿海地區(qū)出現(xiàn)。當(dāng)時,中、西非地區(qū)的黑人被葡萄牙、西班牙的殖民者們相繼販賣至秘魯沿海地區(qū)成為搬運茶葉箱子的奴隸。殖民者們頒布了禁止黑人奴隸演奏音樂的法律,殖民者知道這些來自中、西非的奴隸的家鄉(xiāng)有一種打擊樂器叫作非洲鼓,除了勞動之余的娛樂工具之外,還有號召、聚集的意思,為此,更是果斷禁止把非洲鼓帶到殖民地。
奴隸制被廢除后,箱鼓這件樂器得到了進一步發(fā)展,在制作方面更加匠心獨運,將六面體的木質(zhì)箱體的其中一面用較為輕薄的木材作為打擊面板,這一面叫作“塔帕”面。爾后,為了進一步獲取箱鼓本身更大的音量,就在這個箱子“塔帕”面的對面,挖開了一個圓孔,讓音量傳遞得更遠,箱鼓在秘魯最終成型。
(二)箱鼓分類以及舞臺演奏風(fēng)格
1. 秘魯傳統(tǒng)風(fēng)格
秘魯是一個擁有箱鼓演奏傳統(tǒng)的國家,同時,箱鼓也是秘魯?shù)姆俏镔|(zhì)文化遺產(chǎn),每年都有箱鼓藝術(shù)節(jié),萬人齊奏箱鼓的場面也被列為世界吉尼斯紀(jì)錄。秘魯?shù)貐^(qū)的箱鼓演奏可謂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5]百年來,秘魯當(dāng)?shù)匾淮忠淮南涔乃囆g(shù)家不斷改良發(fā)展,最終形成了獨特秘魯打擊手法。首先,在低音區(qū)域,秘魯當(dāng)?shù)氐囊魳芳視r常將自己的整個手掌拱起,手掌內(nèi)部形成中空的狀態(tài),這樣做的目的是要讓自己的手指尖更好地在箱鼓表面進行擊打。此外,在中高音位,秘魯?shù)南涔乃囆g(shù)家常用手指的第一關(guān)節(jié)以上的部分來演奏箱鼓上沿和邊沿, 整個手指與手掌保持一個平面, 在這樣的手型下?lián)舸虺鰜淼闹懈咭羯容^干凈、清脆。
2. 古巴傳統(tǒng)風(fēng)格
古巴屬于拉丁美洲國家,也是拉丁音樂風(fēng)格的典型區(qū)域,當(dāng)?shù)氐拇驌魳菲饕钥导压模–onga)、邦戈鼓(Bongo)、箱鼓等較為常用。[6]在箱鼓演奏的手法方面,受到了康佳鼓的影響和啟發(fā),古巴傳統(tǒng)箱鼓演奏手法借鑒了康佳鼓的演奏方法,在演奏低音區(qū)域時,整個手掌完全放平,得到堅實、有力的低頻音色,非常飽滿,很有力量。此外,在中高頻段,特別是在頂部邊緣的高音區(qū)到中心低音區(qū)的演奏位置距離也相應(yīng)變小,在演奏頂部邊緣高音區(qū)域。 因此,必須使用部分手掌以及所有手部,包括手指及手指關(guān)節(jié)。
四、昆曲藝術(shù)與箱鼓的舞臺演繹融合表現(xiàn)
(一)昆曲唱詞與箱鼓律動的融合
盡管在昆曲的眾多唱詞里,有數(shù)篇唱詞可稱之為名篇佳句,流傳至今,但湯顯祖所創(chuàng)作的《牡丹亭》卻是不可不提的一首唱詞,甚至可與唐詩宋詞相媲美。而在昆曲的唱詞里,箱鼓便是一個很好和舞臺融合搭配的律動樂器,箱鼓的即興演奏空間很大,因此給昆曲念白這方面的伴奏樂器,帶來了舞臺上與眾不同的風(fēng)格演繹。[7]例如“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此句描寫爛漫的春光和寂寥的閨閣生活的巨大反差,揭示出吟唱者杜麗娘的春心萌動。箱鼓可使用鼓刷搭配镲片運用拉丁音樂體系中的慢速波薩諾瓦律動來表現(xiàn)這種獨特的人物心情,與此結(jié)合,恰如其分地表達出杜麗娘內(nèi)心懷春的情感。
再比如“遍青山啼紅了杜鵑,那荼蘼外煙絲醉軟,那牡丹雖好,他春歸怎占的先”“則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使用優(yōu)美的語言為昆曲創(chuàng)作唱詞,聽來可以令人心情愉悅、印象深刻,同時也可以進一步促進戲劇的情節(jié)發(fā)展,豐富人物的形象,更是創(chuàng)造性地將慢速布魯斯律動運用箱鼓演繹出來,讓整個昆曲唱段在舞臺演繹和音樂律動效果上實現(xiàn)中西結(jié)合,打破原有昆曲的板眼規(guī)則,以律動中的套拍實現(xiàn)與昆曲板眼的新融合。讓古老的昆曲融入西方精華的律動元素,在昆曲伴奏音樂律動方面做出新的嘗試和探索。
(二)昆曲藝術(shù)與箱鼓的演奏技巧的舞臺融合
聲音大小高低的控制、節(jié)奏快慢的把握以及速度的調(diào)節(jié)或者說咬字發(fā)音是否準(zhǔn)確到位都可以成為影響昆曲演唱的因素,就昆曲的演唱技巧而言就十分細(xì)膩講究。昆曲的唱腔分有多種腔法,例如“豁”“疊”“擻”“嚯”等,昆曲中每一個角色會主動調(diào)整并采用與自身角色要求相符合的唱法。但是在現(xiàn)實中的表演中,隨著劇情的深入發(fā)展或者為了更好地塑造人物、表達人物的情感而改變拍唱腔以及節(jié)拍。而箱鼓具有民族傳統(tǒng)打擊樂器所沒有的音響效果和節(jié)奏律動,在演奏技巧上復(fù)雜多變,可運用拳擊、叩擊、掌擊、彈擊等,使之音色可渾厚、可清脆、可顆粒,這使得箱鼓在舞臺上的可塑性變得更強,箱鼓運用不同的演奏技巧與昆曲的演唱者現(xiàn)場即興配合,兩者相融合,在舞臺演繹效果上碰撞出新特色。此外,箱鼓演奏技巧上還可以借鑒諸如康佳鼓、中東鼓、坦布拉鼓等其他世界打擊樂演奏技法,進一步豐富與昆曲的現(xiàn)場配合,在視聽上給予觀眾更多美的感官享受。
注釋:
[1]古兆申.長言雅音論昆曲[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3:60.
[2]李"漁.閑情偶寄[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88.
[3]索緒爾.普通語言學(xué)教程[M].高名凱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0:178—180.
[4]柏格森.時間與自由意志[M].吳士棟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58:30.
[5]羅蘭·巴爾特.小說的準(zhǔn)備[M].李幼蒸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0:148.
[6]汪曾祺.人間有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71—72.
[7]趙"圣.淺談箱鼓演奏藝術(shù)中的手法技巧[J].藝術(shù)評鑒,2018(19):53—54.
(責(zé)任編輯:崔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