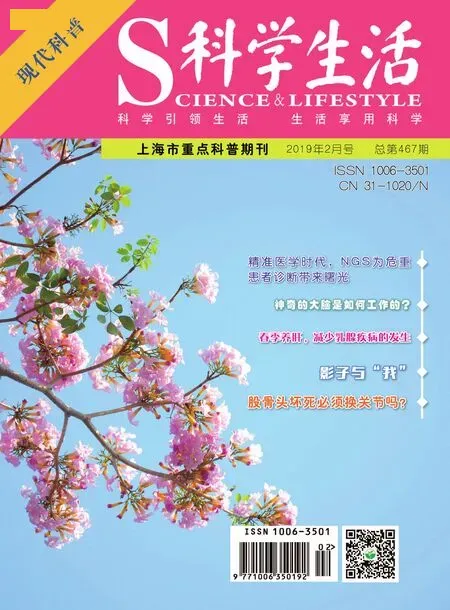古詩詞中的紡織服裝史話
文/馮憲 編輯/丙丁
古詩詞是中華傳統文化中的瑰寶,閱讀古詩詞不但可以感受作者的心境,體味他們的學識、氣度、抱負、審美情趣和熱愛自然、熱愛國家、體恤人民的胸懷,而且還能還原歷史,有助于讀者窺見當時的社會生活場景……本文僅從專業視角出發,羅列與分析古詩詞當中一些與紡織服裝有關話題,盡管這些內容現今已經不大提及了,但它可以讓人們知曉紡織業悠遠的過去,看到一路走來的源頭。

▲ 明代的絺绤道袍
一、絺綌
最早出自于《詩經》的《周南·葛覃》。詩中有“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為絺為綌,服之無斁”的描述。意思是:葛藤長得長又長,漫山遍谷都有藏,藤葉茂密又繁昌。割葛蒸煮紡紗忙,織成細布或粗布,成衣穿著真舒暢。民國時期《川沙縣志·物產》中也有記載:“葛,草蕩最多,村野亦有之,蔓生二三丈,莖多纖維,可為絺綌”。“絺”字的發音為“chi,音同吃”,“綌”字的發音為“xi,音同戲”,“絺綌”最初是指用葛藤纖維紡紗后織成的布,“絺”為細葛布,“綌”為粗葛布,后來“絺綌”延伸為指用葛布制成的衣衫。當時用葛藤纖維紡紗、織布、制衣已十分普遍。我國周代就曾專門設立名為“掌葛”的官吏來管理葛藤的采集、種植、加工和紡織,并有“山農”之葛(織葛布)和“澤農”之葛(供食用)的區分。葛布透氣性和散熱性好,適合于制作單衣(亦稱為葛衣),供人們在炎熱的夏季穿用,故戰國末期《韓非子·五蠹》一文中有“冬日麑裘,夏日葛衣”的記載。絺綌的加工到東漢時期達到鼎盛,葛布之產地以吳越、嶺南兩地最為出名。據有關史料記載,當時上等的細葛布可以達到“絲縷細入毫芒,視若無有”,“卷其一端,可以出入筆管”,外觀“薄如蟬翅,重僅數銖”,簡直可與現今的蕾絲面料媲美。到了魏晉時期,粗葛布不僅用于制作衣服,還成為男子頭頂發鬏飾物(稱為葛巾)的來源。當時生產的粗細葛布早已在民間廣泛應用,且因上貢朝廷,以至京城“榜人必著葛布”。葛布還曾隨古瓷器等工藝品,沿海上絲綢之路,遠銷異國他鄉。至唐乾封元年(公元666年),一種名為“郁林”的葛布被列為上等貢品,并延續了一千余年。
二、浣紗
尤其出名的是唐代著名山水畫家、詩人王維七言古詩《洛陽女兒行》中的“誰憐越女顏如玉,貧賤江頭自浣紗”一句。該詩描寫的是洛陽一位年過15歲的女孩子,嫁與富貴人家后一步登天,過上了讓人羨慕的富庶生活。然而,此詩最后兩句“城中相識盡繁華,日夜經過趙李家。誰憐越女顏如玉,貧賤江頭自浣紗”卻峰回路轉,道出了當時社會存在的城鄉差別與貧富差別,使得該詩具有了深刻的社會內容與評判功能。“浣”字的釋義為洗滌、滌除,三點水的偏旁表明“浣”的實施與操作離不開水。所謂“浣紗”,最早是古代葛麻類纖維制作加工的一道環節,即用流動的水源將煮過的葛麻絨毛表皮洗去,邊洗邊曬,直至把所有的絨毛表皮洗盡,剩下曬干的便是紡紗可以使用的葛麻類纖維狀物質了。所以,宋元及以前時期的中原及長江中下游地區,當棉花種植與用作紡織主要原料還未普及時,“浣紗”是紡紗織布必不可少的前道工序,出現頻率自然很高,比如春秋戰國時期就有“西施浣紗”的傳說。隨后,這道工序因棉花加工生產的出現與普及而變得不多見了,“浣紗”一詞的含義也逐步演變為“洗衣”了。順便提一下,后人一些繪畫作品把“西施浣紗”描畫成洗衣物是存在謬誤的。

▲ 五代周文矩的《西子浣紗圖》

▲ 唐代張萱的《搗練圖》(局部)及現代版的“搗衣”
三、搗衣
出自唐代著名詩人李白《子夜吳歌·秋歌》中的“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一句。此處“搗衣”的含義是“捶衣”,即用棒槌將衣料放在平坦的石砧或木板上捶擊,使衣料變得綿軟而便于裁縫與穿著。此詞傳遞出來的傳統紡織服裝史話有兩方面。一是最初使用的紡織原料問題。因為在宋元以前,中原地區的棉花栽種尚未普及,故服裝面料來源只有葛麻及絲織品。來自于蠶絲的絲織品,因加工工序復雜,生產不易且數量有限,當然只能供少數的王公貴族穿著,而大多數尋常百姓長期以來都穿著用葛麻面料制成的衣裳。葛麻織品最明顯的缺點就是纖維質地太硬,紡紗織布后縫紉衣裳費力不說,穿著后還有毛刺感,體感不舒適,所以當時在制作或穿用衣裳之前,需要通過捶打方式使其變得柔軟平服些,這便是李白“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中所說的“搗衣”情形的由來。二是這一紡織專用名詞含義的轉化。宋元之后,隨著棉花種植及加工技術在中原地區普及開來,棉布逐漸替代了葛麻織物。由于棉布的穿著舒適度要大大高過葛麻織物,所以先前為提高縫制便利性和穿著舒適性的“搗衣”這樣的加工環節,也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線。然而“搗衣”一詞并沒有在民間消失,而是轉換成一種對紡織品服裝維護保養方式的描述,并且延續至今。現如今,雖然洗衣機已經十分普及,但是在一些偏遠的農村或山區,仍可見一些村婦在水邊平整的石頭上,用棒槌敲打的方式清洗衣物的情景。故現在人們說起“搗衣”一詞,多半會與“洗衣”聯系在一起。

▲ 蠶婦淚
四、羅綺
出自北宋詩人張俞所作《蠶婦》一詩:“昨日入城市,歸來淚滿巾。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詩人用樸素的語言通過對一個農村養蠶婦女的經歷與感受的描寫,表達了對下層勞動人民處境的深切關懷與同情。詩中雖不帶一字的議論,卻無聲地揭示了當時封建社會存在的不公現象。一個住在鄉下以養蠶為生的婦女,到城市里去出售蠶絲,返回的時候她淚流不斷,傷心的淚水甚至把手巾都浸濕了。因為她在都市中看到,全身穿著漂亮、昂貴絲綢衣服的人,卻不是辛苦勞作的養蠶人,暗喻“富人羅綺遍身,窮人麻布成衣”的社會不公現象。“羅綺”是當時對蠶絲織物的一種稱謂。“羅”指顏色素淡或者質地較為稀薄的絲織品。“綺”指帶有花紋或圖案的絲織品。在詩中,“羅綺”特指用珍貴絲綢面料做成的服裝。在現代社會,常用“綾羅綢緞”來描繪絲綢織物,表明隨著時代的發展,以及絲綢紡織技術手段的豐富,絲織品的種類要比原先更加多樣化了。
五、績麻
出自南宋詩人范成大《夏日田園雜興·其七》中的“晝出耘田夜績麻,村莊兒女各當家”一句。“績麻”一詞,與傳統的紡織技藝有關。“績”在這里做動詞用,意為“用手搓”,“麻”便是指當時的一種紡織材料——來自苧麻的纖維。所謂“績麻”就是用手搓的方法,把苧麻纖維搓成紗線,供織布用。其具體操作方法是將自然漂白后的苧麻撕開成片,卷成一縷縷,放入清水盆中浸泡,用手指將其梳理成一根根的苧麻細絲,然后引出細絲再放到大腿上用手搓捻,使其連接成纖細的麻紗線,達到一定長度之后,再卷繞成有如蠶繭狀的小團縷,成為織布用的紗綻。可見在紡車尚未普及的時期,我國中原及長江流域地區紗線形成的方式是“績”,而非“紡”,“績麻”“績緒”應該是我國最早出現的紡織專用名詞了。作名詞用的“績”,古代有功、業、事之含義,由此看來,現代漢語中的“成績”最初的意思恐怕也是指“績麻成紗”吧。時過境遷,現如今的“績麻”已經成為一項非物質文化遺產了。

▲ 現代版的績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