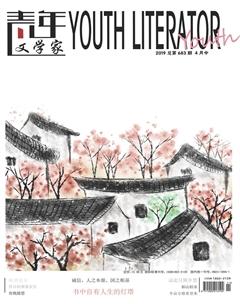論莫言《故鄉人事》中歷史和人性的交融
摘? 要:莫言作為當代文壇舉足輕重的作家,其創作思維和視野具有獨特和犀利的特點。他在敘述中通常不對人物形象作出定義性的評價,而是通過鋪設故事背景和人物之間的對話慢慢凸顯出人物形象。他在小說創作中經常以某個特定的時間段作為大背景凸顯出受歷史因素所影響的人性,并在不同年代的對比和新舊幾輩人的摩擦中深刻揭示封建思想對人的鉗制以及新時代年輕人敢于沖破束縛開辟新世界的勇氣,體現了莫言對愚昧過去的控訴和對新時代的期望。
關鍵詞:莫言;《故鄉人事》;歷史;人性
作者簡介:陳思遠(1995.2-),女,陜西省漢中市人,研究生,在讀于西藏民族大學,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11-0-02
莫言曾說:“故鄉不是封閉的,而是不斷擴展的。作家往往有著把異鄉當故鄉的能力。鄉土是無邊的。我有野心把‘高密東北鄉當成中國的縮影,希望通過我對故鄉的描述,讓人們聯想到人類的生存和發展。”[1]因此他時常給人物性格賦予一定的時代精神,如以旁觀者角度看待建國初期農村大變革的《生死疲勞》,計劃生育大背景下人們生理和心理受到雙重摧殘的《蛙》。莫言突出的是整個大時代背景下人們的生活境況和精神面貌,他詼諧的語言背后隱藏的是他對歷史和人性的犀利剖析。他的新作《故鄉人事》同樣將一些個性鮮明的人物和令人深思的故事放進了高密東北鄉,通過人物之間的對話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展現出不同時代中平凡人不平凡的人生境遇和體悟。他用簡單的對話操縱潮起潮落,用微縮的景觀映射人生百態,這樣的寫作方法使看似平常的旁家瑣事變得富有深意,耐人尋味,同時也顯示出莫言別具一格的創作思維和對人性的深刻思考。
一、階級斗爭下判斷標準的失衡
在以農村生活為題材的小說中經常可以看見“地主”“中農”“貧下中農”這些字眼。地主階級在舊社會本應是被供奉的團體,卻在建國初期被人民狠狠地踩在了腳底,從這以后每個人都被打上了有確切“成分”的標簽,這樣明顯的區分也使人們的價值觀和是非觀發生了改變,對于一個人或是一個家庭的評價不是基于他們的人品和功過,而是以“成分”作為唯一的評判標準。
《地主的眼神》對此有明顯而深刻的揭示。首先,小說開頭因為“我”少時的一篇作文而激發了人們批判地主的熱情,老地主孫敬賢代表地主階級、富農、反革命分子成為了眾矢之的,盡管孫敬賢一家被劃為地主成分是另有隱情的,但所有被打上地主印記的都是不容被反駁的被批斗被打倒的對象。孫敬賢的二兒子孫雙亮說:“我們家劃成地主,你們家劃成中農。我爹勞動改造,你爹當上會計。我們是地主子女,連學都不讓上,你們可以上學,還寫作文糟蹋我們……”[2]作者用這簡單的幾句話體現出當時社會因為成分劃分所造成的人們生活上的天壤之別,而這樣的“代代相傳”使地主階級變得唯唯諾諾抬不起頭,也讓他們的后代成為了無辜的犧牲品。
其次,人們對于地主階級的排斥使長幼尊卑的概念也漸漸模糊。作為一個后輩,文中的“我”對于長輩孫敬賢不僅沒有尊重,還將他塑造成批斗的典型,并且在割麥的時候還對他抱有不屑的態度。又如在割麥的時候,生病的孫敬賢被稱為裝病,吐血也是因為過去喝貧下中農的血太多,這些描寫處處體現著人們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思維的極端和片面。莫言設置的反轉和沖突無一例外地凸顯出了真實的人性,體現出在對與錯被賦予絕對界限的年代人們的價值觀被具體的規范所引導從而失去了自我辨別和判斷的能力。
小說中還講到了孫敬賢大兒子孫雙庫同媳婦于紅霞的戀愛史。在當時那個年代,被劃為地主成分的人不僅在日常生活和應有權利上受到歧視和不公平待遇,甚至在婚戀上都會存在極大的限制,這對于人們的心理和精神都造成了一定的傷害。莫言描寫那個年代人們的婚戀狀況,體現出了他對于人的本能的情感和社會現實之間沖突的深刻研究,也體現了他對于所謂“絕對”對錯對于人性的迫害的批評和控訴。
二、封建倫理束縛下人性的扭曲
莫言曾在《紅高粱》中這樣描寫他的高密東北鄉:“無疑是地球上最美麗最丑陋、最超脫最世俗、最圣潔最齷齪、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愛的地方。”[3]可見莫言對他所建造的高密東北鄉充滿了激情和熱愛,但他并沒有把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填充進這個空間,而是在看似一片祥和中暴露出封建殘余所造成的人性的缺點。在高密東北鄉這片熱土上,世世代代生活在這里的鄉民沉浸在傳統的儒家人倫中,并自覺用傳統倫理來規約現世生活,但當人們過于信奉封建禮教的時候,它就變成了一把枷鎖將人們牢牢鉗住。
小說《左鐮》中的少年田奎因為被冤枉而被父親剁掉了右手,這在當下的社會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一個父親在面對自己親生兒子的時候,竟然可以為了維護自己的臉面而下狠手。莫言用鐵匠打制左鐮為題為全文設置了懸念,然后讓田奎用簡單的一句“自從我爹剁掉了我的手,我就什么也不怕了”解開了左鐮的謎,他對于田奎的語言描寫冷靜卻充滿了同情和悲哀,將他塑造成那個殘留著封建氣息空間里的犧牲品。
在小說《左鐮》中,作為故事講述者的“我”和哥哥在面對盛怒之下的父親時選擇了說謊。從這里可以看出,作為父系家庭的家長,父親這一角色的地位和威望不容被撼動,父親永遠站在一個評判的制高點,在這種情況下就會使成孩子變得膽怯和懦弱。莫言在講述這些看似人情淡漠的故事的時候實際上是想喚醒真實的人性,他在開頭一直描述的鐵匠打鐵的細節從另一個方面似乎也映射出了人就是在千錘百煉中變得扎實有韌勁,就像被剁掉手卻從此變得堅韌穩重的田奎。
小說《斗士》中塑造了一個誰也惹不起的“無賴”鄉民武功,他似乎和這世上所有的事物都沒辦法和平共處,斗爭時始終帶著魚死網破的決心,究其原因還是因為他的出身不好。對于武功來說,看什么都不順眼,見誰都想打罵,這事實上是一種強調自身存在感的行為,因為被人輕視甚至是蔑視,加之生活上的壓迫和封建人倫的根深蒂固,使他的精神處于極度的壓抑狀態,莫言形容他是一個“睚眥必報的兇殘的弱者”。事實上,作為弱者他也只能用這種方式來盡力維護自己的尊嚴,他這種人性上的病態也是同歷史發展和生活環境密不可分的。
莫言在小說中沒有直接點出鄉民的愚昧和自私,但卻在字里行間透露著對受害者的同情與惋惜,封建思想蠶食了本應保持善良和純真的人性,也破壞了很多人本應擁有的幸福婚姻和美滿人生。
三、時代交錯中新舊思想的碰撞
當新思想產生的時候才會顯示出舊思想的落后和陳腐,莫言的小說可以說是與時俱進的,在他的小說中不僅僅是對過去發生的事進行講述,而是時常會出現新舊事物之間的矛盾和對比,這樣的手法將不同的歷史階段和不同年代人的精神面貌融合起來,更能凸顯出歷史的滄桑感和人性的沉浮。在《地主的眼神》中,如果說孫敬賢兒子那一輩還生活在地主階級的陰影里,那么孫輩來雨就完全扔掉了這個包袱,充滿激情地創造自己的新生活。通過孫來雨形象,莫言展現了當代社會新農村的發展水平,也提醒人們只有放下沒有意義的階級斗爭、開拓眼界、轉變思維,才能使物質和精神層次并駕齊驅。
不僅是新舊時代物質生活的對比,莫言還將新一輩的思維穿插進小說中。《地主的眼神》末尾描述了地主孫敬賢豪華葬禮的場景,明明是舉行葬禮,孫雙庫感受到的卻是前所未有的幸福。相反,孫雙庫的兒子孫來雨認為孫雙庫這樣的做法是毫無意義的:“就像對著仇人的墳墓揮舞拳頭一樣。”這里也體現出了新舊思想的碰撞,在這個故事里孫來雨代表的不僅僅是他個人,而是代表著大部分新時代的年輕人,他們有著靈活的頭腦,充足的熱情以及對封建思想絕對的丟棄。作者在這篇小說中譴責迂腐思想的同時又對年輕一輩的精神面貌給予了肯定。
縱觀這三篇小說,都無一例外地講到了歷史和人性的關系。莫言在回首故鄉往事的同時也讓當下和過去形成了對比,深度挖掘了在特定歷史條件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們處理問題的方式和人的情感宣泄。他對于封建倫理有著明確的批判立場,但又對被封建思想禁錮的人們抱有深切的同情。莫言娓娓道來的故鄉人事既是用過去的故事敲響了當下的警鐘,又是以現世的繁榮填補了過去的創傷,同時也體現出了他對新時代和年輕一輩的殷切期望。
參考文獻:
[1]錢歡青.莫言:高密東北鄉是中國縮影.濟南時報[N],2011.
[2]莫言.故鄉人事[J].收獲,2017(5).
[3]莫言.紅高粱[M].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7.
[4]陳思和.在講故事背后——莫言《講故事的人》讀解[J].學術月刊,2013(1).
[5]胡沛萍.狂歡化寫作:莫言小說的藝術特征與叛逆精神[M].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4
[6]王春林.民間、啟蒙與悲憫情懷——關于莫言的文學近作[J].當代文,,2018(1).
[7]張曉琴.莫言的歸去來辭[J].文藝報,2017(7).
[8]楊光祖.莫言歸來的敗象[J].文學自由談,20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