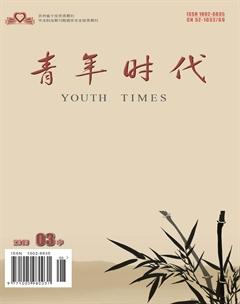“無直接利益沖突”國內研究綜述
倪佳瑜
摘 要:“無直接利益沖突”型群體性事件因其較強的突發性和較大的破壞性,引起了多學科學者的廣泛關注與深入探討。目前我國學者對“無直接利益沖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從定義角度來研究沖突事件的內涵、從心理角度來研究參與者的參與動機、從體制癥結角度來研究沖突事件的形成原因、從化解矛盾角度來研究沖突事件的治理路徑。
關鍵詞:無直接利益沖突;文獻綜述;研究展望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人民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征程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我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從0.37萬億元(1978年)增長到82.71萬億元(2017年),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隨著改革的逐步深入,各種社會矛盾也日益凸顯。在經濟新常態的大背景下,我國的社會結構和利益格局無時無刻不在發生著重大變化。雖然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極大的提高,但由社會不公造成的矛盾也在日益加劇。特別是由貧富差距產生的“相對剝奪心理”不斷蔓延,滋生了各種擾亂社會秩序的行為,群體性事件就是社會矛盾的爆發性表現。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的群體性事件呈現出一種新的態勢,即事件的參與主體與事件本身并沒有直接關聯,也沒有明確的利益訴求;其參與沖突事件具有很強的情緒因素,只是“借題發揮”,通過打、砸、搶、燒等暴力手段發泄不滿情緒。目前主流學界把此類事件稱之為“無直接利益沖突型群體性事件”。因參與者具有明顯的“泄憤心理”特征,也有學者稱其為“泄憤型群體性事件”。典型案例包括:萬州事件、甕安事件、永昌事件等。“無直接利益沖突”的頻繁發生,深刻地反映出我國社會體制存在的弊病。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鮮明地指出要打造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堅決打贏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攻堅戰。如何加快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機制的建設,不僅關系到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而且影響著政府的公信力和黨的執政信用。因而對“無直接利益沖突”事件的研究,一直是學界關注的熱點。目前我國學界對“無直接利益沖突”的研究廣泛分布于法學、政治學、社會學和管理學等具體學科中,取得了不少有價值的研究成果。目前學界主要是從三個方面對無直接利益沖突型群體事件開展研究。
第一,從定義角度來研究沖突事件的內涵。《瞭望新聞周刊》的記者鐘玉明等人最早提出“無直接利益沖突”這個概念,他們認為此類事件是“社會矛盾新警號”,事件的參與主體與本體事件并無直接利益關聯,其參與事件的動因是為了發泄不滿情緒。黃順康并不認同“無直接利益沖突”這種提法,他認為此類事件應該被稱之為“非直接利益沖突”,因為沖突的參與主體并不是完全沒有“直接利益訴求”,而是并非因自己的直接利益而參與事件。還有學者出于本體事件(直接利益沖突)與變體事件(非直接利益沖突)存在關聯性的考慮,把此類事件稱之為“半直接利益沖突”,認為沖突的參與者是“主動地訴求利益,被動地表達的行動”。雖然學界存在著“無直接利益沖突”、“非直接利益沖突”和“半直接利益沖突”等不同提法,但是眾多學者普遍認同事件中的參與者存在著情緒動因。因而文鳳華等人又把此類事件稱之為“情緒主導型群體性事件”,認為事件中的參與者具有典型的非理性特征,事件的發展要經過情緒積累、情緒激發和接受暗示三個階段。而于建嶸則根據事件的“泄憤”特點,從參與者行為角度把此類事件歸類為“泄憤型群體性事件”,認為其屬于“基于不滿宣泄的集群行為”,以此強調不滿情緒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在此基礎之上,部分學者又對“無直接利益沖突”的內涵做了進一步探討。李培林提出“無直接利益沖突”屬于非階層性沖突的觀點,強調參與者的來源多元化。謝海軍則客觀地指出了“無直接利益沖突”中存在著一定的暴力違法行為,認為此類事件的內涵應為“具有對抗形式的非對抗性行為”,仍屬于人民內部矛盾范疇。由于《瞭望新聞周刊》等主流媒體先入為主的影響,“無直接利益沖突”這種表述得到了學界的普遍接受和認同,作為一個專有名詞的使用也最為廣泛。
第二,從心理角度來研究參與者的參與動機。相較于一般性群體事件,“無直接利益沖突”中的參與者具有明顯的情緒化特點,因此很多學者從心理角度來研究參與者的參與動機。陳相光最早對沖突事件的社會心理進行了系統的研究,他具體分析了參與者的個體心理和集體心理,認為事件的心理沖突能量向行動沖突能量轉化具有七種方式。王雅君認為調控社會心態是解決“無直接利益沖突”的重要途徑。一方面要從宏觀角度改善社會心態環境;另一方面要從微觀角度入手,重新樹立民眾對黨和政府的信心。劉勇發現“無直接利益沖突”的參與者具有五種心理:失落消極心理、排斥逆反心理、借機發泄心理、盲目從眾心理和政治參與心理。他在具體分析群體心理誘發因素的基礎之上,提出了構建心理疏導機制的一系列建議。單光鼐認為“無直接利益沖突”的誘因事件起到了“情感集體喚醒”的作用,而謠言的無序傳播起到了“情景震撼”的效果,讓參與者生成了“命運共同體”的感受,從而“抱團取暖”參與進沖突。孫德梅等人在分析社會心態向社會行為轉化路徑的基礎之上,以“冰山模型”研究消極社會行為,詳細分析了社會情緒的潛伏期、爆發期和消退期三個階段,并就不同階段的管理措施提出了合理建議。朱志玲關注到了“無直接利益沖突”中參與者的怨恨情緒,并對這種情緒的生成邏輯進了探究。她認為“傷害和比較”是社會怨恨情緒的邏輯起點,“公正失衡心理”是社會怨恨情緒的初始形態,“無能感”是社會怨恨情緒的發酵機制,“情緒感染和互聯網平臺”是怨恨情緒的擴散機制。龔志宏吸收了科塞社會沖突功能論的觀點,認為“無直接利益沖突”中的群體心理具有兩面性,參與者表現出的社會心理并不完全都是消極和負面的,也有積極和正面的成分,應采取有效措施對參與者的心理進行優化。
第三,從體制癥結角度來研究沖突事件的形成原因。無直接利益沖突型群體性事件的發生,和我國社會的體制癥結有著很大關聯。學界把此類事件作為觀察我國社會矛盾的重要窗口,對其形成原因展開了廣泛探討。劉孝云等人針對當前基層政府和部分官員的失當行為(官僚作風、貪污腐敗、決策錯位等)展開研究,認為政府構造方面的缺陷和民眾不信任的政治心理是引起“無直接利益沖突”的重要原因。高傳勇通過研究得出結論,誘發“無直接利益沖突”現象的體制癥結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利益表達渠道不順暢、社會利益結構失衡、地方政府權威弱化、社會治理機制存在缺陷。他認為此類沖突是我國社會矛盾日趨復雜的激烈表現,只有對體制癥結進行改革,才能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陳世瑞指出官民矛盾是群體性事件生成的重要原因,他具體分析了官民矛盾的形成機理和表現形態,認為官民矛盾會讓中國社會陷入群體性事件之困,并給出了突破官民矛盾困境的具體措施。周海生發現地方政府在應對“無直接利益沖突”的過程中存在著三重缺失:其一是理念誤區、其二是體制障礙、其三是現場應對失當。冉光仙認為弱勢群體在“無直接利益沖突”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這是因為轉型時期社會不公問題突出,弱勢群體權力得不到充分保障,造成了黨的執政資源流變,為沖突事件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第四,從化解矛盾角度來研究沖突事件的治理路徑。因為“無直接利益沖突”事件具有巨大的破壞性,直接威脅到地方政府的有效統治,所以對其治理策略的研究一直是學界關注的熱點。王巖等人認為,化解“無直接利益沖突”應遵循以下理念:把以人為本作為化解矛盾的根本原則,把包容貴和作為化解矛盾的心理保障,把共享共建作為化解矛盾的內在訴求,把公平正義作為化解矛盾的根本目標。顧紹梅指出了地方政府在應對“無直接利益沖突”中存在的幾點誤區,比如盲目處理干部、用“躲”的方式拖延,或者直接“拿錢買穩定”。她建議地方政府應加快預防機制的構建,形成應對事件的新思路;同時規范問責機制,加強縣鄉領導的心理培訓和心理疏導。李志強等人從提升政府公信力的角度,來探討“無直接利益沖突”的治理路徑。他們認為政府應該提升政策公信力、廉潔公信力、誠信公信力和政治控制公信力。錢穎萍研究了政府的回應機制,認為有關部門在治理“無直接利益沖突”的過程中,應完善應急協調制度,構建制度化常態化的回應平臺,并積極引導民眾合法地表達利益訴求。程昆在具體分析“無直接利益沖突”事件成因的基礎之上,提出要通過創新社會管理的方式來化解社會矛盾,比如創新社會財富分配機制和創新社會管理組織模式等。黃剛認為“無直接利益沖突”本質上屬于利益矛盾,權力不平等和貧富差距等原因造成了弱勢群體產生“相對剝奪心理”,因而此類沖突事件不是簡單的情緒發泄,而是一種間接表達利益訴求的群體性事件。要從根本上化解這種沖突,一方面要充分發展經濟,持續改善民生,使人民共享改革的成果;另一方面要格外重視對弱勢群體權益的保護,積極完善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
雖然我國學者對“無直接利益沖突”進行了較為廣泛的研究,但是目前仍在存在著諸多不足之處。首先,對于西方現有的研究成果吸納不足。雖然“無直接利益沖突”是在我國話語體系中的特有詞匯,但是并不意味著西方沒有相關的研究。西方學者對于類似的社會沖突事件——騷亂,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如美國學者斯托弗提出的“相對剝奪感”概念,對于我國的“無直接利益沖突”有很強的解釋力;再比如科塞提出的社會安全閥理論,為化解“無直接利益沖突”提供了可供借鑒的有益思路。其次,囿于事件的相對敏感性,目前我國學界對于此類案例的研究,仍然處于“管中窺豹”的境地,尚沒有相關部門或者學者能夠建立起此類案例的數據庫。在大數據時代,一個全面的數據庫不僅能夠方便學界深入開展實證研究,而且可以進一步提升研究成果的全面性和客觀性。最后,國內學界對于“無直接利益沖突”背后所反映出的社會負面心理,乃至集體性怨恨情緒研究程度仍顯不足。圍繞著“民怨”這一研究對象,如何開展社會心態監測,預警不良情緒,并構建科學的消解或釋放機制,仍是擺在我們面前的突出問題。
參考文獻:
[1]陳相光.關于無直接利益沖突現象的社會心理分析[J].廣東行政學院學報,2007(03):78-81.
[2]王雅君.“無直接利益沖突”與社會心態調控[J].理論探討,2008(04):161-164.
[3]劉勇.“無直接利益沖突”群體心理分析及心理疏導機制構建[J].云南社會科學,2010(01):44-48.
[4]單光鼐.群體性事件背后的社會心態[J].中國黨政干部論壇,2015(05):20-22.
[5]孫德梅,王正沛,康偉.群體性事件管理的一個心理學視角——基于社會心態、社會行為理論的研究[J].華東經濟管理,2014,28(02):143-149.
[6]朱志玲,朱力.從“不公”到“怨恨”:社會怨恨情緒的形成邏輯[J].社會科學戰線,2014(02):172-177.
[7]龔志宏.論“無直接利益沖突”中群體心理的兩面性及其優化[J].求實,2015(04):39-46.
[8]劉孝云,郝宇青.論當前我國“無直接利益沖突”現象產生的原因[J].社會科學,2008(06):49-53+190.
[9]高傳勇.“無直接利益沖突”現象的體制性癥結及對策探析[J].學習與實踐,2009(07):90-94.
[10]陳世瑞,曾學龍.官民矛盾、群體性事件與化解之道[J].晉陽學刊,2015(01):103-110.
[11]周海生.地方政府應對群體性事件的三重缺失:理念誤區、體制障礙及現場失當[J].宿州教育學院學報,2009,12(06):64-67+137.
[12]冉光仙.非直接利益沖突視域下執政資源整合路徑探究[J].甘肅社會科學,2011(06):14-17.
[13]王巖,郝志鵬.“無直接利益沖突”矛盾的化解理念與路徑研究——基于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視角[J].中國行政管理,2014(12):82-85.
[14]李培林.加強群體性事件的研究和治理[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10-19(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