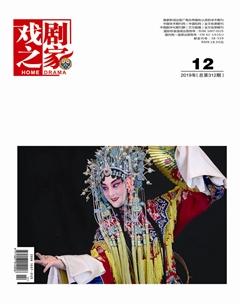論電子音樂作品《諾日朗》的音樂特征
張倩
【摘 要】張小夫教授是我國電子音樂的第一人,其代表作《諾日朗》是包含對電子音樂創作理念的成熟理解,結合中國創作元素創作出的具有東方特色的大型混合類電子音樂作品。其中,噪音與樂音、原始與現代、哲理與想象的交融碰撞使得傳統音樂借助現代電子音樂獲得新的詮釋,為作曲家提供了更加廣闊的創作空間和技術平臺。
【關鍵詞】張小夫;混合類電子音樂;《諾日朗》;LOOP
中圖分類號:J60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9)12-0053-01
一、體現民族特性的音樂元素
電子音樂作品的創作有賴于但不局限于電子技術的發展進步,經過近半個世紀的實踐階段,以張小夫教授為代表的中國作曲家們克服了早期一味追求對聲音素材堆砌的創作理念,探索出具有中國傳統文化氣質的現代電子音樂創作道路。諾日朗是位于四川阿壩州藏族自治區的一座雪山,在當地的藏族文化中,被當地藏胞奉為藏族男神的化身。《諾日朗》選取低沉的“喇嘛轉經”和縹緲“西藏民歌”兩種最能體現神秘的藏族宗教文化精神的聲音素材,反映出作曲家對具有民族特性音樂元素的向往。除在音樂語言的選擇中凸顯了藏民族文化特色外,在節奏、韻律、調值的處理方面也力求表達濃厚的民族氣息,通過打擊樂器的獨特音色實現了民族性的暗示和民族韻味的展現。整首電子樂曲中民族特性的音樂元素的融入令聽眾感受到藏域樂土的神圣,“嘛呢”聲中和“轉經”聲,讓人體會到轉經之人對自然的膜拜與對信仰的虔誠。樂曲的主題聚焦人與自然之神的溝通以及人內心深處對于“轉世” “輪回”等生命終極意義的追尋。
二、傳統管弦樂作品的作曲結構
整首作曲中復調思維的運用與樂曲“輪回”的主題非常貼切。通過對作品的波形頻譜圖的分析,可以看出《諾日朗》對傳統的管弦樂作曲技術的借鑒,具體體現為作品的引子和尾聲部分有明顯的呼應性。將全曲分為引子、第一到第四部分和尾聲,一部分與四部分,二部分與三部分均體現出對稱曲式的特點。電子音樂技術創新對傳統作曲技術的突破則體現在拼貼與多聲部 LOOP(循環)交響化制作手段的應用。原始聲音材料的聲高、音色、速度經過拼貼技術實現線條上的變形延伸,在與傳統器樂的聲部對比中獲得空間上的展開。LOOP電子音樂制作技術和磁盤的加速手段使聲音不斷重復,在不同的音區中相互交錯,使聲音材料流動起來,形成直接而巨大的聲場空間。樂曲中,207 秒“喇嘛念經”的原始素材經過音高、音區、密度、力度上的調整,結合傳統打擊樂器形成多層次復合的音樂語匯,充分體現了混合類電子音樂作品中整體與局部展現的復調思維[1]。
三、電子音響與打擊樂器的音色碰撞
《諾日朗》體現了作曲家對錄音技術、音響學、電聲學、調頻合成等數字技術的高超應用,最見其功力的當推貫穿整首作品的電子化聲響。經過分析,樂曲中并非充斥大量堆積的電子音響,而是著重強調原始音響材料微妙而豐富的變化。在作品表現上,利用不具有明確音高因而更加具備原始意義的木質、銅質、石質、皮質等傳統打擊樂器和磬、鑼、鈸、藏鈴等民族樂器,并利用混響、DELAY 等效果器實現了噪音樂音化,構建出空間“對話”。各類樂器不同材質相互摩擦、碰撞,拳頭和手掌拍打(分別代表陰、陽)創造出的原始樂聲與電子音樂產生出既融合又碰撞的聲場效果,營造出藏族文化的神圣意境[2]。
四、舞臺現場音響效果的實時處理
電子音樂的傳播方式和概念與傳統音樂的不同,演出是電子音樂制作環節中很重要的一個環節。現場演出是電子音樂呈現效果至關重要的一步,需要許多復雜的音響制作技術和實時效果處理手段的參與配合。《諾日朗》三個主要版本的創作中,對現場聲場的布局都各不相同,每場現場表演都體現了作曲家依照演出場地建筑結構和聲音能量發聲方式對音響空間設計方面的創意思考。例如,2006 年,《諾日朗》在北京國際電子音樂節開幕式上的演出,作曲家將打擊樂表演者安排在舞臺中心,8 組不同方位的揚聲器營造出打擊樂器、聲場效果相互呼應的空間“對話”效果[3]。這種錯落的復調思維與表現形式,使整首作品呈現出神圣感。每一樣或每一組打擊樂的旁邊都安置了拾音話筒,觀眾席兩旁也設有四組揚聲器與實時控音臺,按照聲音運動軌跡構成與舞臺中的中央聲場之間的呼應。
五、結語
《諾日朗》的成功促進了我國音樂作品題材、音響特征與組織方式的多樣性發展,給人們帶來了一種全新的視聽感受。傳統音樂藝術通過混合類電子作曲技術實現了音樂的動態化與真實化,讓聽眾身處其中,感受到生命大、中、小的循環審美和大時空的“輪回”文化,表現了音樂藝術的生命力。
參考文獻:
[1]張小夫.電子音樂的第一次浪潮”磁帶音樂”連載(三)[J].樂器,2001(04).
[2]王鉉.理念與技術的創新—電子音樂作品《諾日朗》的創作特點分析》[J].人民音樂,2010(09).
[3]徐璽寶.論張小夫的電子音樂創作特征[J].星海音樂學院學報,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