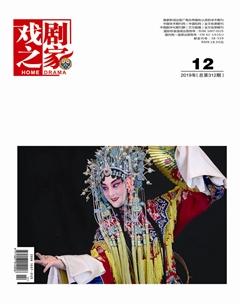使鹿鄂溫克民族電視媒介形象分析
常海齊
【摘 要】使鹿鄂溫克民族古老的傳統文明正面臨著變化的沖突,其生產生活方式及獨特民族文化的變遷受到多方關注。在不同媒介方式中,電視媒介是再現歷史文化與記錄現實的重要載體,對記錄與傳播民族傳統文化具有明顯而突出的優勢。基于此,本文通過對30多個相關的電視節目進行歸納,將使鹿鄂溫克民族電視媒介形象劃分為“表演性”形象、“體悟式”形象、“反思式 ”形象三種類型,深入分析其視聽與敘事的表達特征和呈現方式,并結合目前的創作現狀,總結電視媒介在傳播使鹿鄂溫克民族文化方面所出現的問題,思考其在傳播少數民族文化方面的價值和責任。
【關鍵字】使鹿鄂溫克民族;電視媒介形象
中圖分類號:G2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9)12-0072-03
鄂溫克民族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居住在大山林里的民族,只是由于歷史的發展,相當多的鄂溫克人已經走出森林,來到草原,還有一部分人生活在森林之中。[1]使鹿鄂溫克人是中國鄂溫克民族的一個組成部分,他們生活在大興安嶺西北部的林區,目前,是我國唯一飼養馴鹿的民族。由于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變遷較為明顯,很多電視節目對其進行了持續的關注和記錄,這為使傳播鹿鄂溫克民族民族文化產生了不同層面的意義。
一、使鹿鄂溫克民族電視媒介形象的基本類型
(一)“表演性”形象
對使鹿鄂溫克民族文化藝術進行表演性展示,主要突出表現使鹿鄂溫克民族文化的“奇”,即該民族中出奇而少見的事情,電視節目集中拍攝民族中奇特的自然風光和人文風情,來讓受眾直接感受使鹿鄂溫克民族的文化與生活狀態。有的是展示文化,比如湖南衛視《快樂大本營》中的“神馬都給力”這一期節目,通過使鹿鄂溫克民族中最后一位女酋長瑪利亞·索老人表現這個民族的古老傳統民歌和馴鹿文化。通過烏日娜老師和烏蘭牧騎的演員展示了該民族獨特歌舞文化,如模仿鹿哨、表演喉音等等;有的側重于展示生產生活方式,比如節目《鹿背上的原始部落》,介紹了布冬霞部落中鄂溫克族人制作樺皮用品、鹿皮衣、列巴、搭建撮羅子的方法等。
雖然同是對民族文化藝術進行表演性展示,但是有些節目則注重展示生活氣息,將人文、藝術、風俗、美食等民族“奇”特的事情和生活趣事巧妙融入,用體驗與互動的形式記錄發生在使鹿鄂溫克民族生活中的故事。例如少兒頻道《綠野尋蹤》由最野小勇士來到烏力庫瑪林場,深入原始森林尋訪神秘又陌生的馴鹿部落。節目的形式較為新穎,在體驗民族生活之余拍攝出自己眼中的鄂溫克族。節目的視點落在少年身上,無論是拍攝使鹿鄂溫克民族文化的演變,還是該民族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節目不僅展示了使鹿鄂溫克民族的生活狀況與文化,更突出了少年對待即將逝去的民族文化的真實看法。作為對民族文化藝術進行表演性展示,雖然很多節目的表現內容具有同質性,但是能夠發現各別節目也在創新節目的表現形式,試圖引起觀眾對該民族生活與文化發展的關注。
(二)“體悟”式形象
2003年根河市市委、市政府決定對鄂溫克民族鄉實施整體生態移民。這也是使鹿鄂溫克人的第三次定居。生態移民的政策對使鹿鄂溫克民族的物質和精神層面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為此,一些電視節目試圖通過影像的方式去觀察使鹿鄂溫克民族的生活狀況以及思想觀念的改變,進而讓更多的人關注該民族的發展。區別于第一類電視節目中展示民族的“奇”特,第二類電視節目則融入了對使鹿鄂溫克民族現狀與文化傳承困境的體悟,從“奇”到“悟”,電視節目多了對該民族文化發展的思考。
如吉林衛視《回家》欄目的“遲子建——靈魂上岸”這一期節目,作家遲子建談在節目中談到寫作《額爾古納河右岸》的背景與原因,表現出作家對于鄂溫克民族發展的擔憂,以及她對現代文明與傳統文化之間沖突的思考;鳳凰衛視《走讀大中華》的“呼喚遠去的敖魯古雅 ”這一節目,首先講述了獵民維佳對森林和馴鹿的無限依戀;其次通過探訪使鹿鄂溫克民族最后一位部落女酋長瑪利亞·索老人,了解她的生活經歷。2003年很多獵民都簽字搬入新敖鄉居住,而她卻拒絕簽字選擇在山上養馴鹿,節目深刻反映出她對傳統文化的堅守;最后主持人楊錦麟呼吁道:“雖然在走讀中并沒有找到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有效結合的圓滿答案,但是希望更多的人可以關注使鹿鄂溫克民族的發展。”從單一的介紹人文風情到關注使鹿鄂溫克人在現代文明進程中具體人物的心理感受和變化,節目開始思考從他們的生活狀態中體悟社會文化變遷為之帶來的影響。
(三)“反思”式形象
當下使鹿鄂溫克民族的生產生活方式已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有的人選擇繼續留在山林中喂養馴鹿,有的人則選擇下山生活。此時,電視媒體將鏡頭對準那些使鹿鄂溫克民族中的平凡人物,記錄他們的故事,感受他們的情感。如果說在內容表達方面,上述的電視內容側重“奇”與“悟”,那這一類節目則表達了對使鹿鄂溫克民族中平凡人物身上的“情”。節目內充分展現出使鹿鄂溫克人物的真情實感,以情動人,節目之外卻引發我們思考,反思現代化的生活方式是否可以給他們帶來幸福感,反思幸福的含義,遺憾的是這一方面的電視節目相對匱乏。
比如節目《鄂溫克族馴鹿習俗》,講述了吳旭升與妻子金雪峰在山林中以養馴鹿為生的生活。有個情節是正值馴鹿的交配期,吳旭升家丟失了四五頭馴鹿,雖然當時天色已晚,但是吳旭升仍然堅持進山尋找馴鹿,終于經過兩天一夜的徒步尋找,找到了馴鹿。在這過程中鏡頭記錄了吳旭升丟失馴鹿的緊張、妻子的擔心以及他們找到馴鹿后的喜悅,情感的變化讓我們深刻的體會到他們與馴鹿之間的感情,也可以感受到他們的幸福;央視中文國際《五彩呼倫貝爾·大山在呼喚》節目組到山上瑪利亞·索部落做探訪,在山下拍攝定居點和旅游景區的環境與人物,山上山下的反差折射出了使鹿鄂溫克民族生活變遷之中不同年齡人的心理變化。而兩種生活設施的對比更值得我們關注與反思,從節目來看,現代化的設施已走進使鹿鄂溫克人家,可我們也能夠發現一些傳統民族的器物,比如輕巧而實用、不需一釘一線制成的樺樹皮生活用品;沒有經過學習就可以畫出、剪出各種惟妙惟肖動物形象的使鹿鄂溫克族人,這些才是這個民族的智慧所在。生產、生活以及文化的變遷,也許改善了他們在物質層面的生活,但這些文化現象和技藝卻是使鹿鄂溫克民族在發展變遷中最為寶貴的精神產物,它們更值得去關注與保留。
文化延續和生存之間如何達成平衡,的確讓人深思,使鹿鄂溫克民族的發展不僅需要政府的幫助還需要民族自身的努力。電視媒體所要做的不僅是探索使鹿鄂溫克民族悠久的歷史文化,還應記錄該民族當下發生著的、極具時代感、現實感、貼近感的人物、事物與故事,將使鹿鄂溫克民族的現實狀況呈現在觀眾面前。從這三種類型分析中,可以看出它們之間并非涇渭分明,而是枝附葉連,彼此影響,對使鹿鄂溫克民族具有不同意義的傳播作用。
二、使鹿鄂溫克民族電視媒介形象的呈現方式
(一)視覺表達的多元化
通過梳理使鹿鄂溫克民族的電視節目,發現其視覺語言的呈現方式逐漸趨向于多元化,節目越來越重視畫面中人物與環境、細節等方面的結合,將視覺藝術盡情發揮,這樣的呈現方法極大的提升了節目的感染力。較為明顯的是節目中對鏡頭的靈活運用。首先是通過遠景、近景鏡頭的使用來敘述環境,環境是周圍的情況和條件,人或事物都有其特定的存在環境。[2]央視中文國際頻道《傳承·絕技》之《鄂溫克族馴鹿習俗》節目先使用遠景鏡頭交代了使鹿鄂溫克人生活的地方——內蒙古敖魯古雅阿龍山的環境背景,為觀眾提供了必要的信息,遠景鏡頭的后續畫面是具體場景的示現,節目采用航拍、推、移等鏡頭將一群馴鹿穿梭于山林的圖景與后面使鹿鄂溫克族人忙于放養馴鹿、尋找馴鹿等具體的事件相互聯系,逐漸渲染出使鹿鄂溫克民族與馴鹿之間的情感,表達出使鹿鄂溫克民族人對山林對馴鹿的依戀。這樣的畫面組合,既構建起故事發生的背景,也達到了營造氛圍的目的,加深了觀眾對節目的理解。
其次是運用特寫鏡頭刻畫細節。細節,即事物的細枝末節,是節目的重要因素。很多節目中都有對人或物的細節刻畫,央視科教頻道《百科探秘·馴鹿人家》講述了頒布生態移民政策后,一戶鄂溫克族獵民從山下定居點搬回山上生活的故事。母親瑪茹莎喜歡山上的生活,但是她28歲的兒子依蘇卻向往著山下的生活。為此,節目為了表現人物這種細微的心理變化,捕捉了很多依蘇迷茫的神情,比如他朝著山林大喊,瑟賓節排練里的低頭不語等,從中能夠感受到他渴望融入山下現代的生活,又無法融入的內心惆悵。這些鏡頭著力刻畫出了生態移民之后,生產生活的變遷對年輕人心理的一種微妙改變。另外,一些節目將鏡頭對準山林中的動物,比如節目《鄂溫克族馴鹿習俗》講到山林中靈性的動物馴鹿時,鏡頭里是馴鹿彌漫與山林之中的蚊煙中,配以音樂,表現出了馴鹿的神秘性。央視軍事·農業頻道的節目《美麗中國行·最后的馴鹿部落》也用很多鏡頭來表現野生動物,如松樹、鹿、狍子、小鳥等,它們活躍在山林中,又好似在與使鹿鄂溫克人公古革軍嬉戲玩耍,呈現了一幅人與自然和諧相生的美好圖景,讓人對使鹿鄂溫克民族生活的大地充滿著好奇。
(二)詩意的解說與靈動的音樂
解說詞的風格也發生著細微的變化。解說詞一般用于解釋說明一些畫面無法表達的地方,尤其對于展現少數民族生活的故事,考慮到觀眾可能對使鹿鄂溫克民族了解不夠,因此節目在表現畫面內容時會依賴于解說詞。但是隨著電視節目的不斷創新,解說詞更加注重趣味性、知識性和文學性,常常表達畫外之意,具有詩意,值得回味。節目《鄂溫克族馴鹿習俗》,主持人說道:“‘所謂絕技,就是因緣際會,鄂溫克族馴鹿絕技,就是山林中與鹿共生的因緣,是領命而去的召喚,也是適者生存的本能。”雄渾大氣的聲音,文學性濃厚的解說詞共同凸顯了鄂溫克族馴鹿這一民族傳統絕技。
托馬斯·斯金納認為,聲音與畫面的關系應該是“1+1=3”的關系,聲音與畫面在一起能夠創造出第三種意境,從而引發觀眾產生心理的聯想和感情的共鳴。[2]因此節目中對音樂的使用格外重要。例如節目中出現的人聲,即當地人演唱民族歌曲或演奏民族樂器,還有音樂的運用,每種表達方式都給觀眾帶來了不同的審美體驗。北京衛視的《傳承者》,在傳承項目敖魯古雅的文化展示時,年近94歲的瑪力亞·索唱起民歌《古佳耶》,感動人心;節目《馴鹿人家》作為背景音樂出現的民歌,歌詞大意是“我們是鄂溫克人,世世代代養馴鹿的森林人,我們領著馴鹿在大興安嶺里游走”,烘托出女主人對山林對馴鹿的熱愛之情。在節目中運用民族音樂不僅能夠激發觀眾的想象力,調動觀眾的情感,甚至可以引發觀眾思考,尤其是在民族題材的電視節目中,音樂不僅可以襯托某種情感,更能升華節目所表達的內容,是節目的點睛之筆。
(三)平民化的敘事表達
從相關主題的電視節目來看,除一些綜藝娛樂欄目,很多文藝類和文化類欄目、社教類欄目、以及真人秀欄目,大多采用新聞紀實的手法與平民化的敘事表達方式,一類是拍攝外景記者在當地使鹿鄂溫克族人家體驗的過程;一類是結合解說詞,發現和記錄關于使鹿鄂溫克族人的有趣的故事。前者一般是通過記者與當地居民的互動去感悟當地的自然與人文之美,在內蒙古衛視《蔚藍的故鄉》之《鄉土味道·敖魯古雅馴鹿》這一期節目,記者不再是旁觀者而是參與到他們的生活中,一起與當地人學習做鹿奶制作的列巴等;后者則重在紀錄被拍攝者的生活狀態,比如第一財經網拍攝的《鄂溫克使鹿部落之駝鈴漸息》、《鄂溫克使鹿部落之獵人回憶》、央視中文國際《傳承·絕技之鄂溫克馴鹿習俗》,節目行走在使鹿鄂溫克人家,給觀眾帶來更為真實的見聞和故事。兩者相比,后者既采取了紀錄片的表達方式也融入了故事化的情節和節奏的處理,增添了節目的趣味性。
三、使鹿鄂溫克民族電視媒介形象的價值
(一)展現使鹿鄂溫克民族的生活與文化發展狀況
梳理使鹿鄂溫克民族的電視節目資料發現,有一些還停留在民族文化的展示方面,只對民族的人文風情作導游式的介紹,詮釋的較為膚淺,而有一些則沒有拘泥于對民族中各種景與物的描述,側重強調人與景的故事,深入的表達了使鹿鄂溫克人的生活現狀和文化內涵。相比之下,后者表達的影響力較大。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走入觀眾內心的往往是具有真情實感的事物。雖然有所差異,但都是展現其民族生活、文化的重要方式,為傳播民族文化帶來了不同層面的意義。
(二)表達使鹿鄂溫克民族的生活觀念
使鹿鄂溫克民族是一個視自然為友的民族,他們居住在大興安嶺的叢山密林之中,雖然狩獵,但卻尊重動物的生命規律,從不獵殺幼小、懷孕的動物。就是這樣的生活方式決定了他們不會向自然過度索求,對生命的觀念也暗示他們不會對森林環境造成破壞。[3]電視節目《呼喚遠去的敖魯古雅》就曾講到使鹿鄂溫克獵民維佳的生活觀念,為保持森林的生態環境,他常在山林中撿一些別人留下的垃圾,而這樣的觀念也影響著他走出山林的生活習慣,比如在三亞他看到垃圾后仍然會隨手撿起來。節目將使鹿鄂溫克民族對事物的觀念進行呈現,有利于構建該民族形象進而傳播獨特傳統文化。
(三)傳播使鹿鄂溫克民族的獨特文化
使鹿鄂溫克民族是我國人數較少的民族之一,該民族只有語言沒有文字,想要保留使鹿鄂溫克民族獨特的文化,不能單單依靠建造博物館、民族村落這樣靜態的文化形式,還可以利用動態的形式去延續,例如通過電視媒體對使鹿鄂溫克民族獨特的文化進行傳播和保存。不同類型的電視媒介,在記錄著這個民族的發展與變化,它們是使鹿鄂溫克民族文化的相冊,每一頁都是一個開始、一段記憶,具有傳播價值和歷史意義。
四、思考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電視媒體的欄目訴求不同,因而對使鹿鄂溫克民族生產方式和文化變遷的呈現也有差異。同時也存在一些問題,首先有一些節目中的記者僅僅作為一名游客的心態去觀賞民族景觀文化等民俗文化,缺少一些思考性的觀點,如果記者在采訪之前未對民族進行基本的了解,那么節目中采訪問題的意義和節目的傳播效果也會大打折扣;其次,節目內容存在的同質化現象較為嚴重,為此節目應該注重對選題內容的挖掘和呈現形式的創新,比如當下很多人文類電視節目采用體驗和互動的形式弘揚文化,拍攝了很多感人的鄂溫克人的故事,這些故事體現在節目中能夠讓觀眾感受到使鹿鄂溫克人的喜怒哀樂、酸甜苦辣,從中表現使鹿鄂溫克民族中平凡人物的生活現狀與精神世界,這樣的創作方式值得借鑒。再次是節目應具有人文關懷,有尊重民族文化的態度。對待少數民族的文化我們需要用一種平視的角度去了解,慢慢地走入他們的生活和內心,只有這樣電視節目才會有溫度,有影響力、有傳播力,才能使得這個民族被人關注和理解。
參考文獻:
[1]鄂溫克族簡史[M].編寫組編著.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魏南江.優秀電視節目解析[M].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7年3月1日.
[3]色音,張繼.生態移民的環境社會學研究[M].民族出版社,2009年6月1日.
[4]郝時遠,張世和,納日畢力戈.“馴鹿之鄉”敖魯古雅鄂溫克族獵民研究現狀——34年后的追蹤調查1960-1994[M].1994年10月.
[5]貝拉·迪克斯.被展示的文化 當代“可參觀性”的生產[M].馮悅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