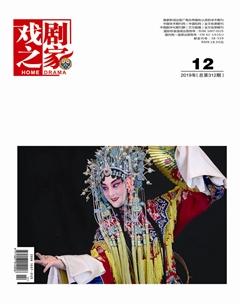性別政治視域下女性意識表達的理性審視
孫亞男
【摘 要】《嘉年華》作為一部聚焦“邊緣女性”“性別麻煩”等話題的女性獨立電影,講述的正是女性敘事最感興趣的議題:女性形象、女性意識、女性成長。本文將以性別政治為切入點,試圖在分析其敘事策略、符號客體借喻的基礎上,理性審視本片的女性意識表達訴求。
【關鍵詞】性別政治;女性意識;符號
中圖分類號:J90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9)12-0095-02
電影先在地存在著一種性別潛規則:男人看,女人被看;行動著的男人是主體,作為奇觀的女人是客體。[1]隨著中國女性的社會地位逐漸受到關注,電影創作者更傾向于關注女性情感和意識的表達。“女性意識”在電影的發展中分化出兩層含義:一是以女性眼光洞察自我,確定自身本質、生命意義及其在社會中的地位;二是從女性立場出發,審視外部世界并對其加以富于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2]這可歸結為女性的自我意識和女性的主體性意識,即對“性別潛規則”的反叛。《嘉年華》借女性身體和性別的符號客體“夢露雕塑”的命運變遷來完成小米“自我意識”的確認,用家庭內部秩序、社會外部關系以及女性主體的同構關聯等要素架構起敘事策略,張揚女性意識的發展困境,最終成全以小米為代表的邊緣女性的反抗與蛻變。從人性化的個體意識到典型化的社會境態,以個體的境遇影射整個社會的價值趨向,實現“性別麻煩”下的個體和外在現實世界的雙重觀照。
一、話語結構:意識形態的符號能指
后結構主義者從語言文化的規約性方面,將性別歸結成話語建構物,女性主義在性別政治下的“男/女”二元對立模式之外發出聲音,確立個體的自我意識。作為女性物化對象的夢露,一直以來是西方后工業時代的消費主義要求的“性感”與“美”等欲望的提喻,而在中國傳統道德觀念和意識形態機制的桎梏下,兩者長期被置于刻板的話語政治下賦以擠壓、打擊。《嘉年華》中的夢露雕塑被設定在海濱城市的“嘉年華”到來之前的松弛庸常背景下,其境遇的變遷映射以小米為代表的女性群像生命情感的嬗變,她們在現代文明所修訂的性別秩序等多重鏡像的圍困下,熟稔又禁圉“女人”、做女人、是女人的迷惑、痛楚與困窘。[3]
符號學肯定了主體與符號客體之間的意向性關系。“夢露”作為符號客體的自由形式,五次出現所指以小米、小文為代表的女性群像自我意識和主體性意識的流變。夢露首次出現在小米的“窺探”視角中,意指對女性身體和性別的探尋、對“自我”的發現與確認,也象征著“不自覺”與夢露相關聯的小米、小文、張新新將“自覺”地成為男性消費的對象。夢露的第二次出現被賦以母性守護神的意味,小文被性侵的次日,女性的生理疼痛只能靠藥片止忍,被男同學偷拍的經歷隱喻男權文化下對女性的視奸常態,女性的壓抑在小文出走尋父片段得到片刻的爆發,小文抱著魚缸蜷曲在雕塑下睡去的場景暗示女性和夢露的同構關系,女性的自我意識得以被守護。夢露第三次出現時腳踝已被貼滿了粘膩、突兀的小廣告,這隱喻著商業資本力量對女性意識的操控和蹂躪,小米與劉會長交易、莉莉半價修復處女膜、小文流連于象征女性下體的水上樂園管道、小文媽媽對女兒的“去性征”行為……這些是女性物化、男權至上的思維邏輯,“資本”和“夢露”成為主從的并存關系,女性群像的主體意識在此處短暫迷失。因夢露本身是作為男權文化語境中“凝視”和消費的客體存在,故雕像多是以紅腳趾、高跟鞋等局部的視覺符號呈現,以再現男性視野中對女性美的塑造。而夢露唯一以完整形態出現是在其被割據、吊起時,被玷污猥褻后的“迷失的夢露”實現了貝克《再見列寧》(Good Bye Lenin!,2003)式的重生。夢露的第五次出現是在極具力量和儀式感的運輸路上,同安哲羅普洛斯的《尤里西斯生命之旅》(UlyssesGaze,1995)中被運走的列寧像無意間形成某種關照,與其同步的女性小米“玩偶之家”式的出逃徹底砸碎了男性霸權主義的鎖鏈,完成了女性“自我意識”的復蘇、成長、蛻變,女性性別意識的主體性從重重符號中解放出來,裸露出生命的真實狀態。
二、敘事策略:女性意識的倫理性建構
選擇藝術片作為創作類型的《嘉年華》在敘事的策略上是“雷諾阿”式的,將一個龐大的群體整合為一個小眾群像,“女性群像”作為被擠壓的對象被整體編碼,呈現出來自性別的同構性特征。小文的離家出走暗示如果家庭秩序繼續壓榨女性自主意識,她將成為流連城市中尋找棲身之所的小米;小米任由自己沉淪于錢色交易將會成為下一個莉莉;從良的莉莉繼續服從男權社會的“性倫理”又會發展成另一個手足無措的小文媽媽。
同樣地,《嘉年華》選擇社會性議題,又偏離以“故事”“情感”撼動觀眾的傳統敘事軌跡,這顯然屬于當代中國電影硬核現實主義的“軟核化”——最大化地保持對中國現實的關懷,用敘事的或美學的策略謀求在電影管理體制中的安全落地。[4]即以歐洲藝術電影的美學素養加之知識分子式的思辨和社會關懷,展示在有限社會空間、單一性侵事件中,由家庭內部秩序、社會外部關系和女性的同構性關聯等倫理性話題共同搭建起的,籠罩在女性意識之上的“牢籠”。
在兩性之間,“性”是一種倫理禁忌的平衡,而打破平衡冠以年齡、身份、地位懸殊的“性侵害”恰恰是男性對禁忌的享受。由此可見,作為一種權力關系的性對女性意識的迫害并不僅僅以性別作為依托,還依賴于家庭(內部)和社會(外部)的分工。
在家庭內部,小文母女之間的“性禁忌”和“性羞恥”來源于男權社會對于“性倫理”的代際傳承。母親在女兒被性侵后做出的撕衣服、剪頭發等“去性征”的極端化處理,可認作是家庭內部關系的失序,這種失序所爆發出來的正是自甘卑弱、認同男性價值觀、“自覺”屈從客體地位的“性倫理”觀念,母親成為男權主義中得力的“女性”幫手,女性意識在家庭內部長期處于被泯滅、壓榨狀態。家庭內部對女性意識的分配往往秘而不宣,家庭之外的社會關系則旗幟鮮明地劃出了權力話語與女性意識的配比關系。整個社會在面對以劉會長為代表的“男權主義”對以小文為代表的女性做出的迫害時,所表現出來的是“利己主義”,即冷漠的眾生相——男性群像均是負面形象,女性群體則顯得疏離。眾人的冷漠一方面是以個人的觀念和集體的無意識構成的“看客”群像;另一方面是以男性為代表的強權欺掠常態——女性在以男性為主導的事件中被“先在地”置于弱勢、敗勢地位。
三、表達出路:性別批判與女性訴求
性別批判建立在男女二元對立的矛盾沖突之上,《嘉年華》將話題止于“性侵”本身,著重于對女性意識的表達,二元對立在其中表現為女性和社會的沖突,而非狹隘的男女利益獲取上的對立。這在影片中體現為三個層次,其一,以女性導演獨特的洞察力探討性侵事件背后女性的生命情感。導演文宴將議題錨定為“性別麻煩”,從女性意識出發,以女性視角審視現實世界,關注女性從心理情感到命運體驗的發展狀況,呈現出女性追求美和性自由權利所面臨的尷尬處境。其二,以女性群像反觀以無名海濱城市代表的有限社會空間下的性別機制。影片中與小米形成絕對參照的小文、媽媽、莉莉、新新、律師以及作為女性符號存在的夢露塑像,每個個體都是精致的、隱藏的性別運作機制上的一環[5],被置于社會這一放大鏡下剖析,看似都有個體的獨立意識,但在社會空間下還是要承擔運作的轉型之痛。其三,以女性和社會的二元模式引發更為廣遠的問題探討。《嘉年華》并不試圖規訓政治結構,而在于引發討論。在“夢露”的裙擺下,文宴更在乎的是“社會群像”對于自我意識的規訓以及對更深層面社會問題的思考。
參考文獻:
[1][英]勞拉·穆爾維.觀影快感與敘事性電影[G].周傳基譯,外國電影理論文選,2001.
[2]喬以鋼.中國女性與文學——喬以鋼自選集[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
[3]戴錦華.電影批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4]李洋.中國電影的硬核現實主義及其三種變形[J].文藝研究,2017(10).
[5]李銀河.性的問題·福柯與性[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