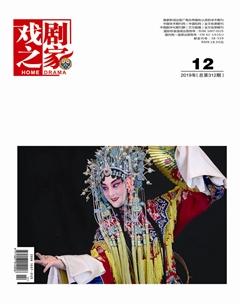《我不是藥神》的存在主義之思
楊霖 胡凡剛
【摘 要】電影《我不是藥神》自2018年上映以來,總票房突破30億,成為票房與口碑雙贏的國產(chǎn)現(xiàn)實主義影片。本文將用存在主義相關(guān)思想對影片進行分析及闡釋該影片給我們帶來的人文主義思考。
【關(guān)鍵詞】《我不是藥神》;存在主義
中圖分類號:J90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9)12-0102-01
《我不是藥神》是我國現(xiàn)實主義影片中少有的佳作,改編自2015年的陸勇事件,講述的是被社會忽視的白血病群體因消費不起高價藥,依靠程勇走私的價格低廉且藥效相同的印度仿制藥進行治療的故事。本片主人公程勇經(jīng)歷了從走私藥品發(fā)家到轉(zhuǎn)行開服裝廠再到良心發(fā)現(xiàn)虧本幫病人走私藥品的過程。此劇不僅從全新視角描述社會問題且無處不體現(xiàn)著存在主義哲學思想。
一、“此在”的本質(zhì)體現(xiàn)需要與他人“共在”
海德格爾主張:世界之中存在自我與他人,人與世界是不可分割的,人的存在與他人同樣不可分離,人在世界之中避免不了與他人的“共在”。在日常生活中,我們需要在與他人的“共在”過程中,感受他人對自我的反饋,在反饋中感受真正的自我,只有這樣才能確認自身的真實存在——“此在”。
彭浩因患白血病,不愿給家里添負擔,逃出了在農(nóng)村的家。出于自我保護,少言寡語并排斥與陌生人接觸,一頭黃色長發(fā)更是給人一種反叛青年的形象。隨著劇情的發(fā)展,我們得知其搶藥是給病友吃,這是在與病友“共在”的過程中體現(xiàn)出的自我“此在”的本質(zhì)。因此程勇決定留他在身邊工作,開始彭浩并看不起這個以賺錢為目的販賣走私藥的老板,始終少言寡語有著強烈的自我保護意識。程勇在轉(zhuǎn)行3年以后,打算繼續(xù)賣藥救人,彭浩一開始拒絕給他當幫手,但當?shù)弥逃聻榫炔∪速r本走私藥時,他又默默回到了程勇身邊工作。并在此后與程勇“共在”的過程中展現(xiàn)著自我“此在”的本質(zhì),同時程勇也在與彭浩“共在”的過程中,褪去自己商人的形象,展現(xiàn)自己“此在”的本質(zhì)。
人本身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與他人共同生活在世上,即與他人“共在”。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要把握自己,既不能對他人有過多的干擾和介入,同時也不能在共在的過程中迷失自我,失去自己的個性與原則。彭浩一直守著自己“此在”的本質(zhì),雖然看不起程勇靠販賣走私藥發(fā)家的行為,但卻將救人看得重于私人情感。
二、“本真”與“非本真”狀態(tài)下的“真實存在”
海德格爾在論述人存于世的狀態(tài)時,將人的狀態(tài)分為“本真”和“非本真”兩種。“本真”狀態(tài)是指人在作為個體不受外界的干擾時,本人最初始最純粹的心理狀態(tài)。而“非本真”狀態(tài)是指人與外界產(chǎn)生交流聯(lián)系后,受到外界的反饋與影響,失去了本身的固有狀態(tài),表現(xiàn)出迎合或逃避外在的心理,從而導(dǎo)致人產(chǎn)生一系列“非本真”的行為。
本劇主人公程勇先后兩次決定賣藥的心理狀態(tài)和人的存在狀態(tài)是完全不同的。最初是在得知患重病的父親暈倒,需要費用進行手術(shù)治療。在現(xiàn)實生活中,我們不可能離開日常生活來了解“本真”的自我,這意味著,有時我們可以通過“非本真”狀態(tài)探究“本真”狀態(tài)。程勇從事非法走私的“非本真”狀態(tài)背后,其實是渴望父親能健康活下去的“本真”狀態(tài)。
第二次是因患白血病的前合伙人呂益受因無錢服藥去世,觸動了他的內(nèi)心。他選擇再次開始走私印度藥,并且將成本2000元一瓶的藥虧本以500元一瓶的價格售出。這時的程勇選擇販賣藥品,完全是出自對白血病患者群體的同情,是發(fā)自內(nèi)心的行為。向我們展現(xiàn)了程勇心地善良以及愿意犧牲個人利益,幫助白血病患者群體的“本真“狀態(tài)。
三、個體“自由選擇”后的“責任承擔”
存在主義認為,人的自由就體現(xiàn)在自由的選擇上,人從出生就進行著各種選擇,人就是在不斷的選擇中實現(xiàn)自我的存在價值。關(guān)于“自由選擇”,人具有絕對的權(quán)力,這是不受他人或外界條件干擾的,主觀精神對這種選擇起決定作用。一旦做出了選擇,就必須進行“責任承擔”,選擇始終和承擔責任綁在一起。
程勇作為兒子的角色中,努力生活,盡心盡力照顧父親,特別是在得知父親重病暈倒后,無奈選擇幫人走私印度藥。再到作為父親角色的程勇,為了兒子未來更好的發(fā)展,忍痛同意了前妻提出的帶兒子移民的提議。這些選擇對于程勇來說雖牽扯著各種因素的推動以及條件的約束,但這也是綜合考慮后“自由選擇”的結(jié)果,因此他也要進行“責任承擔”。
一個人選擇一件事,盡管現(xiàn)實中存在各種牽制,但條件起的作用多大,仍取決于個人的選擇。事業(yè)有成后的程勇忽視個人利益的損失,心存病患者,再次鋌而走險走私藥品,是出自自己內(nèi)心的“自由選擇”。最終程勇也為自己的選擇付出了坐牢的代價,但同時也贏得了患者們的尊敬及全社會的理解,還推動了中國醫(yī)療體制的改革,這屬于“自由選擇”后的“責任承擔”。
《我不是藥神》這部影片能取得超高的票房和口碑是理所應(yīng)當?shù)模捌枋鲠t(yī)療體制問題的角度新穎。病患群體生活如此艱難,除了病痛的折磨和高價藥的壓迫,根本原因是我國醫(yī)療體制的不完善,這是多數(shù)人從未關(guān)注及思考的社會問題。影片還引發(fā)了觀眾對于存在主義的思考,為觀眾帶來了一場劇情跌宕起伏、內(nèi)涵豐富的人文主義視聽盛宴。
參考文獻:
[1]陳娟.《我不是藥神》:現(xiàn)實主義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擔當[J].視聽,2018(12):96-97.
[2]薛晉文.現(xiàn)實主義影視藝術(shù)的三重內(nèi)涵[N].文藝報,2018-11-14(004).
[3]張安華.從《我不是藥神》談現(xiàn)實主義電影的特征[J].電影文學,2018(19):8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