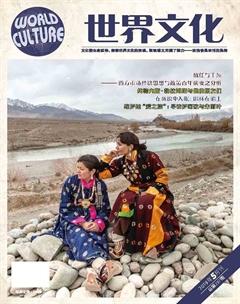莎士比亞《李爾王》的多重解讀
曾艷兵
一種理論或者方法能夠適用于任何研究客體或者分析對象,包括對它自身的分析和研究,那么,這種理論就是具有普遍效率的理論;一部作品能夠被各種理論和方法來分析研究,并且均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和發現,那么這部作品便絕非平庸之作,必定是一部深刻、復雜,甚至充滿矛盾的作品。這樣的作品在世界文學史上并不多見,這樣的理論則幾乎難以尋覓,若有這般理論,那就已經不是理論,而是真理了。理論可以成為真理,但真理不能成為理論,因為一旦變成理論,便不再有真理了。這里有關理論的問題我們姑且不論,還是談談作品吧。我以為,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之一《李爾王》就是這樣一部能夠適用于各種批評理論和方法的作品。
該劇根據古老的不列顛傳說改寫而成。李爾王年事已高,決定根據三個女兒對自己的愛將國土分給她們。大女兒高納里爾(Goneril)和二女兒里根(Regan)花言巧語哄騙父親:
高納里爾:父親,我對您的愛,不是言語所能表達的;我愛您勝過自己的眼睛、整個的空間和廣大的自由;超越一切可以估價的貴重稀有的事物;不亞于賦有淑德、健康、美貌和榮譽的生命;不曾有一個兒女這樣愛過他的父親,也不曾有一個父親這樣被他的兒女所愛……
里根:姐姐的話正是我愛您(李爾)的實際情形,可是還不能充分說明我的心理:我厭惡一切凡是敏銳的知覺所能感受到的快樂,只有愛您才是我無上的幸福。
于是,大女兒和二女兒平分了李爾王的國土和權力。小女兒考狄利婭(Cordelia)實話實說:“我愛您(父親)只是按照我的名分,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李爾王聽后頗為不悅,便剝奪了原本準備給考狄利婭的那一份國土。好在法蘭西王對考狄利婭一見傾心,喜歡她的誠實:“最美麗的考狄利婭!你因為貧窮,所以是最富有的;你因為被遺棄,所以是最可寶貴的;你因為遭人輕視,所以最蒙我的憐愛。”于是考狄利婭被遠嫁法國。李爾王在失去國土和權勢后,受到大女兒和二女兒的虐待,并被趕出家門,流落野外,在暴風雨中倍受折磨。考狄利婭聞訊后率軍回國討伐姐姐,不幸失敗而被害死。李爾王悲憤不已,最后發狂而死。考狄利婭的兩個姐姐爭奪權力,爭奪情人,最后互相殘殺,先后死去。

當然,許多人,包括托爾斯泰都認為李爾王分國土的情節不可信,“李爾沒有任何必要和原因而必須退位。同樣的,他跟女兒們活過一輩子,也沒有理由聽信兩個女兒的言辭而不聽信幼女的真情實話;然而他的境遇的全部悲劇性卻是由此造成的。”(托爾斯泰《論莎士比亞及其戲劇》,見楊周翰《莎士比亞評論匯編》上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502頁)李爾王對女兒厚薄不一,以這樣的條件放棄權力,如果放在一個幾內亞或者馬達加斯加的小親王身上,也許會更加可信。不過,托爾斯泰責備《李爾王》,“但這卻成了一個可悲的諷刺,因為托爾斯泰在人生的最后時刻不知不覺地變成了李爾王。”當然,“托爾斯泰很準確地看出作為戲劇家的莎士比亞既非基督徒也不是道德家。”弗洛伊德則這樣解釋《李爾王》,“兩個姐姐已克服了對父親與生俱來的愛戀,并萌發出敵意。具體地說,她們憎惡因早年的這種愛戀而招致的沮喪。考狄利婭對父親仍然一往情深;這是她心中圣潔的秘密。一旦被要求示之眾人,她只能緘口不語,公然抵抗。在很多病例中我都見到過類似的行為。”(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江寧康譯,譯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42、303頁)這種說法雖然別具一格,但恐怕很難讓人們心悅誠服。

李爾王在荒原中的一段呼喊,被認為是人文主義者的經典發聲:
衣不蔽體的不幸的人們,無論你們在什么地方,都得忍受著這樣無情的暴風雨的襲擊,你們的頭上沒有片瓦遮身,你們的腹中饑腸雷動,你們的衣服千瘡百孔,怎么抵擋得了這樣的氣候呢?啊!我一向太沒有想到這種事情了。安享榮華的人們啊,睜開你們的眼睛來,到外面來體會一下窮人所忍受的苦,分一些你們享用不了的福澤給他們,讓上天知道你們不是全無心肝的人吧!
荒野的暴風雨象征著李爾的內心風暴,促使他清醒地認識了外部世界。通過自己苦難的遭遇,李爾也清楚地認識了自我,并開始回歸人性,回歸自我。自身的苦難使他開始體悟到全體人民的苦難,開始想到那些“衣不蔽體的不幸的人們”。“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此時的李爾似乎與杜甫的情懷有些接近。這段臺詞洋溢著濃郁的仁愛思想,這也是人文主義者的主導思想之一。凡此種種,便可以看作是人文主義式的解讀了。
美國當代批評家邁克爾·萊恩(Michael Ryan)在認真研讀過《李爾王》后,決定對該作品進行多重解讀:一方面檢驗各式各樣的理論,另一方面則拓展并深化對《李爾王》的理解和認識。萊恩所采用的理論和方法包括:形式主義、結構主義、精神分析、馬克思主義、后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后現代主義)、女性主義、性別研究(酷兒理論、男/女同性戀研究)、歷史主義、族裔批評(后殖民主義和國際主義研究)。
邁克爾·萊恩首先對《李爾王》進行了形式主義的解讀。他認為,形式主義者可以從注意該劇對它的世界中的一些最重要的假定的陌生化開始。自然的等級制度受到了質疑,有了一種陌生化的效果。該劇第一場:李爾王宮大廳。肯特伯爵與葛羅斯特伯爵的對話:
肯特:大人,這位是您的令郎嗎?
葛羅斯特:他是在我手里長大的;我常常不好意思承認他,可是現在慣了,也就不以為意啦。
肯特:我不懂您的意思。
葛羅斯特:伯爵,這個小子的母親可心里明白,因此,不瞞您說,她還沒嫁人就大了肚子生下兒子來。您想這應該不應該?
肯特:能夠生下這樣一個好兒子來,即使一時錯誤,也是可以原諒的。
葛羅斯特:我還有一個合法的兒子,年紀比他大一歲,然而我還是喜歡他。這畜生雖然不等我的召喚,就自己莽莽撞撞來到這個世上,可是他的母親是個迷人的東西,我們在制造他的時候,曾經有過一場銷魂的游戲,這孽種我不能不承認他。
這孽種就是葛羅斯特的庶子艾德蒙(Edmund),葛羅斯特還有一個名正言順的兒子,名叫艾德加(Edgar)。最后庶子受到父親的青睞,嫡子卻被父親驅逐。由他們的關系混亂、僭越引出當時社會關系、人際關系的混亂、顛倒這一主題。“親愛的人互相疏遠,朋友變為陌路,兄弟化為仇敵;城市里有暴動,國家發生內亂,宮廷之內潛伏著逆謀,父不父,子不子,綱常倫紀完全破滅。”“最后,俄國形式主義也許會注意到,開場的對話這一動作偏離了處于劇本中心的主要事件。與后面緊跟著的李爾的宣言相比,偏離的性質就更明顯。而且,它的話題是一種發生在合法的社會行為場景背后的事件(通奸、非法的生養),和一種要避開公眾目光的隱蔽的意圖(‘看不出兩位公爵他更喜歡哪一個)。也許可以這樣說,開場對話的這種隱蔽的場景背后的性質使隱蔽的意圖(隱藏在阿諛奉承的場景之后)的問題戲劇化了,而這將導致李爾的垮臺……戲劇從離開中心情節的地方開始暗示在這些爭論中所持的立場:真實不是一種外在表演的東西,也不是由舞臺上的言詞構成的,而是不在他人視線之中的自然產生的真實情感——‘說我們感受的東西,而不是我們應該說的東西。真正的高貴或美德也將被證明是一種內在的高貴品質,而不是那種外在的公開的展示。戲劇本身在開場的背景對話中,說明了前臺是一個欺騙的場所。”(邁克爾·萊恩《文學作品的多重解讀》,趙炎秋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7、11-12頁)
該劇一開始并沒有直接描寫李爾,而是通過肯特和葛羅斯特之間的對話間接地講述了李爾的故事。從這一對話中我們得知,李爾是難以理解的,并且李爾也并不了解自己。葛羅斯特有兩個兒子,合法的艾德加和非法的艾德蒙,這正如詞語具有兩重意義一樣:既能表達意義,又能隱藏意義。“《李爾王》是一部多種話語模式并存的異質性文本。”李爾的語言具有命令話語的性質,他把這稱為父親的語言。它的意思是單一的、獨語的,沒有混雜其他的話語。李爾的突然發瘋預示著語言的崩潰。
在第一場,通過對考狄利婭姐姐們的側面評論,考狄利婭對姐姐們的阿諛奉承的做法進行了對答:“考狄利婭該說什么呢?默默地愛著吧。/……我確信我的愛比我的語言更富有。”在考狄利婭看來,真實在于感情而不是言詞。在這里,考狄利婭的言詞就是她的語言,并勝于語言。在浮夸的語言面前,沉默是一種更加有力的語言。
一個新批評主義者將會在劇本中尋找反諷和悖論,它們體現了矛盾的成功和解,普遍和特殊的融合。其中典型的例證是法蘭西王對考狄利婭說的那番話:“最美麗的考狄利婭!你因為貧窮,所以是最富有的;你因為被遺棄,所以是最可寶貴的; 你因為遭人輕視,所以最蒙我的憐愛。”李爾曾呼喚考狄利婭“my poor fool”,但這不是“我可憐的傻瓜”的意思,應譯為“我可憐的好閨女”(這里“fool”不是指傻瓜,而是表示愛憐的稱呼。該詞朱生豪譯為“傻瓜”,方平譯為“丫頭”,孫大雨譯為“小寶貝”)。這些修辭表達也是新批評主義者會特別關注和分析的。
一個結構主義批評家將會對《李爾王》具有雙重情節,而且這兩個情節既平行又同構這一事實產生興趣。第一個情節就是李爾王從掌權到失權;第二個情節是艾德加從無權到有權。艾德加推翻了那個非法的王位繼承者,也就是他的非法出生的弟弟艾德蒙。“通過結構的對應,戲劇的意義系統也被用來證明從血緣轉到高貴的合理。”
從精神分析角度看,李爾與他的女兒們的關系,使人想起男孩與他的母親的關系。批評家們注意到真正的母親在劇中是缺席的,她的缺席意味著什么?母親的缺席是否凸顯了俄狄浦斯情結呢?
依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李爾王》正處在老的封建形式與正在興起的資本主義社會形式之間的交界處。李爾是土地貴族的代表。“他的垮臺是當時 ‘貴族的危機的一個寓言。他的失去土地是一個土地正在失去其經濟上的力量并正在被貿易所取代的一個典型。”在這個時代,高貴與氣質或出身沒有什么關系,而與金錢有關。

下面我們看看后現代又是如何解讀的。萊恩說:“福柯也許會把劇本看成是描寫了從傳統的社會控制形式向更為現代的懲戒性的社會類型的轉變,這種轉變要求對那使得新的方法成為必然的危機進行描寫。德勒茲與加塔利也許會在其中發現它描寫了一個領土的平衡如何被一系列的潰敗和領土分割的運動所打破,而這種分割最終又自己重新整合起來,產生出一種新的秩序。德里達也許會對劇中由真理與表現、存在與模仿、言說與書寫之間的關系所形成的有序與無序的方式感興趣。克里斯蒂娃會注意發瘋一場怎樣展現了意涵在顛覆假定語言維持的真理秩序的理想方面的力量。利奧塔將會注意劇本怎樣為了真理的觀念或語義的內容而消除自己的形式,它更重視的是這些而不是物質性的意涵的運作。而鮑德里亞則會注意劇本是怎樣驅逐模仿肯定真實的,而那真實本身也僅僅是模仿。”
一個女性主義者也許會把李爾王看作一個濫用權力的家長,而不是一個有著悲劇性缺點的英雄。從性別理論或酷兒理論來看,“《李爾王》寫于一個同性戀——或者雞奸——被禁止的時代,然而它也是新登基的英格蘭國王詹姆斯一世使他的臣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他是一個同性戀的實行者的時代。”“人們甚至可以說,通過在開場的對話中將它引出來,莎士比亞暗示了同性戀亞文化生活的隱秘性質,而作為劇院中的一員,他可能也是屬于這種亞文化的……莎士比亞通過描寫一出充滿了同性戀暗示的戲中戲,映射了當時倫敦劇場本身存在的同性戀亞文化。”“正如我們所知道的,莎士比亞是個可能的同性戀者,然而卻結了婚,我們知道艾德加愛的是男人,然而與詹姆斯一世一樣,在悲劇結束時他不得不站在公眾場合,假裝服從強制性的異性戀的原則。然而這種服從命令的標志的明顯缺乏(艾德加一直沒有與任何一個女人有聯系),說明了這種接受是多么的猶豫與勉強。”總之,《李爾王》“也是同性戀男人的悲劇,因為他必須在強制性的異性戀形式下生活,同時卻體驗著那種必須保持沉默的感情”。
從歷史主義或新歷史主義的視角看,《李爾王》又具有另一種意義。《李爾王》1606年宮中上演,詹姆斯一世1603年登上王位。人們早已注意到了虛構的國王與真實的國王之間性格的相似性。但是,莎士比亞寫作此劇究竟是批判和譴責國王,還是警告與維護國王的權威?在這個問題上,歷史主義者與新歷史主義者的態度也許有著根本的不同。歷史主義者也許會寫作《李爾與詹姆斯》這類文章,主要持前一種觀點;而新歷史主義者則會寫作《莎士比亞與法官》這類論文,主要持后一種觀點。“詹姆斯以厭惡國事而著名,而李爾在劇中的第一個行動就是要把自己從‘國家事務中解脫出來,以便能夠去打獵,而這是詹姆斯最喜歡的一項消遣。”“劇中對于司法與審判的看上去是顛覆的批判是話語方面的一種策略。它通過警告王權的濫用以更好地為它的神圣天定的必然性辯護,從而試圖確立絕對君權的合法性。”
該劇還表現了酷刑,即挖出葛羅斯特的眼睛,這在公開行刑的制度化的暴力社會司空見慣,而在今日文明社會里就顯得難以為人們所接受了。這不由得使我們想起福柯那本影響深遠的著作《規訓與懲罰》。“在幾十年間,對肉體的酷刑和肢解、在面部和臂部打上象征性烙印、示眾和暴尸等現象消失了,將肉體作為刑罰主要對象的現象消失了。”(福柯《規訓與懲罰》,劉北成、楊遠嬰譯,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13頁)有人認為從宗教角度看,該劇可以改名為“李爾王的救贖”,李爾王代表的是受苦受難的普通人;考狄利婭則代表救贖人類的圣徒和殉難者;艾德加則是一位基督教紳士。也有人將該劇理解為一部當代的荒誕戲劇。已經瘋狂的李爾與已經失明的葛羅斯特在多佛懸崖上的一段對話可以理解為貝克特荒誕劇的先驅。
總之,該劇通過描寫一個絕對權威的封建君主變成普通人的過程表現了人文主義的思想。這部戲的概括意義最強,富有哲學意味。該劇探討了權威與社會正義、權力與智慧、真誠的愛與虛偽的愛、人性與大自然的善惡等問題。以權威強求愛反而會失去愛,助長了虛偽與邪惡;而真正的愛是無條件的,但真誠的愛又會損害權威的尊嚴。因此,權威與愛不可兼得。由此可以推及家長與子女、國王與臣民、上級與下級的關系。沒有權威便不可能統治平穩,但權威又會遏制愛與理解,失去民心,這樣統治仍不會平穩。光有權威或者愛都是不夠的,而二者只能擇一時,莎士比亞選擇了后者。另外,權利并不等于智慧,權力助長的往往是愚蠢。權力如果再加上愚蠢,悲劇就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