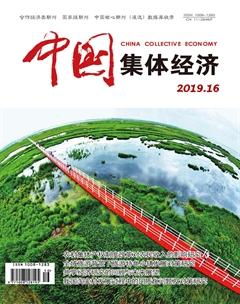上海市就業人員流動與重點行業發展關系研究
胡譯尹 郭卿 簡海蕓
摘要:在上海大力建設科技創新中心的背景之下,文章在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的理論基礎下,探究就業人員與上海重點行業發展之間的關系,為給針對性扶持政策研究或市場引導提供支持。文章以1997~2017年共21年的數據建立金融業發展與就業人員流動之間的回歸模型。研究表明,就業人員流動,以及就業規模的擴大有利于行業的發展。政府應適當擴大就業規模,同時加大人才培養力度,在就業人員流動性增強的同時,提高就業人員素養,能夠更好地促進行業發展。
關鍵詞:金融業發展;就業人員流動;多元回歸
一、問題的提出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重要場合發表了大量關于科技創新的重要講話,形成了寶貴的科技創新思想。黨的十八大也明確提出,“科技創新是提升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持,必須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據《解放日報》報道,韓正在2015年3月6日下午的回憶表示,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5月在上海考察工作時明確要求,上海要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在這一發展背景下,為了給針對性扶持政策研究或市場引導環境的培育提供數據支持,進而為上海科創中心建設的產業升級或布局提供一定的數據支持,本文將在就業與產業理論的基礎上,探究就業人員流動與上海重點行業發展之間的關系。
二、文獻綜述
上海作為中國的金融中心,必然離不開金融行業的發展。2016上海市企業員工流動率調查報告表示,金融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的就業人員流動率相對比較高,而制造業員工流動率趨于穩定。金融行業由于受到“互聯網”等因素的影響,非銀金融機構大量出現,以及政府管理部門對互聯網金融監管力度的不斷加強,一定程度上推高了金融行業的流動率。因此本文以上海市金融行業為例,對就業人員流動與上海重點行業發展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
從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的大方向來看,目前,上海市經過三次產業的發展,已經形成第三產業為主要推動力的經濟增長的基本格局,尤其第一產業的產值的比重已經下降到發達國家的水平,符合國際大都市的發展要求。然而,如今就業結構并不完全適應產業結構,就是說,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轉型變化趨勢一致,但卻滯后于產業結構變化,且第三產業就業彈性偏低,吸收勞動能力減弱,有些行業人才缺乏,有些行業勞動力過剩(朱象賢,2001;李林礬,2012;吳娜,欒貴勤,2014;景躍軍,張昀,2015)。
在探究產業、行業發展與就業人員流動聯系方面,Roberto Basile(2012)實證分析在專業化程度高的行業,行業的發展與就業動態之間存在負向影響。孫青芬(2012)在對中國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及影響因素研究中通過建立短期面板模型,發現生產性服務業的就業彈性在經濟發達地區為正,提高就業水平,擴大就業規模能夠促進行業的迅速發展。張杰(2013)對勞動力流動與第三產業發展的關系進行研究,通過建立聯立方程模型,發現在經濟發達地區,就業人員的凈流入份額提高會促進第三產業的發展,第三產業的蓬勃發展又會反過來吸引大量就業人員,在中西部地區卻出現了相反的現象。但人力資本在全國各地都能夠促進第三產業的發展,且影響系數較大。劉東閣(2016)在對勞動力流動與生產性服務業發展互動研究中,建立勞動力流動的靜態面板模型,以及兩者間的動態面板模型,也發現在一定時期內,勞動力要素流動促進了生產性服務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也會反過來加速行業內勞動力流動。
然而,國內外研究多是從經濟學,管理學等角度,以理論和定性分析為主,從宏觀上來解釋就業人員流動與產業行業發展之間的互動關系,對于某一地區的行業發展與就業結構改善不能起到良好的參考意義。所以,本文將單獨以上海市金融行業為例,從理論出發,用大數據進行定量分析,為針對性扶持政策某一行業,進而為上海科創中心建設的產業升級或布局提供一定的數據依據。
三、數據來源及指標確定
本文的數據主要來源于1997年至2017年的《上海統計年鑒》,本文的各項指標均是根據其中的相關統計數據計算得出,為了模型的顯著性,本文對所有指標進行了對數處理,具體見表1所述。
本文最重要的自變量是就業人員流動指標。本文所涉及的就業人員流動是從行業層面考慮的,通常包括就業人員在行業內的流入和流出,以及在行業內的職位變動。對于就業人員流動的界定,學者們通常根據其研究的方向、范圍及目的進行不同的界定。白麗娜(2013)使用某個群體中發生職業流動的總次數與該群體勞動力數量的比率來反映群體的職業流動的程度。Howard Pack and Christina Paxson (1999)把某一時期中從某一行業轉到另一行業的就業人員數的對數值作為就業人員流動指標。郭文杰(2009)使用勞動力流動增量指標,主要包括行業內就業人員數載不同年份的變化。張月友(2012)通過行業內就業人員數占全部就業人員數的百分比來表示就業人員流動。根據本文研究需要,以及可操作性,本文以上海金融業為研究對象,采用就業人員流動的百分比指標進行衡量。
四、模型建立與分析
在實際問題中,因為絕大多數情況下,我們無法預先判斷自變量與各個因變量之間是否真的存在線性關系,我們用回歸方程去擬合他們之間的關系,只是根據一定的分析所作出的假設,即無論是否真的有關系,總能擬合出一些數值,看似能夠滿足方程,我們稱之為“偽回歸”。所以我們要對擬合得到的回歸方程進行顯著性檢驗。其次,假設回歸方程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也還要對其中的回歸系數進行顯著性檢驗。因為回歸系數也是我們的假設之一,有可能出現總回歸方程顯著,而回歸系數不顯著情況。
第一,回歸方程顯著性檢驗-F檢驗
對多元回歸方程整體的顯著性檢驗就是要看自變量對于因變量是否具有顯著的影響。
y=β0+β1x1+…+βpxp+ε(1)
對回歸模型(公式1)提出原假設和備擇假設:H0:β1=β2=……βp=0,H1:β1(i=1,2…p)不全為0。在接受原假設的條件下,表示自變量和因變量之間的關系用單純的線性回歸模型來表示并不合適,構建F統計量
F=■(2)
其中SSR是回歸平方和,SSE是殘差平方和。此時的F統計量服從自由度為(p,n-p-1)的F分布。在給定的顯著性水平下查F的分布表,得出臨界值Fa。如果Fa 第二,回歸系數顯著性檢驗-t檢驗 回歸方程整體的顯著并不意味著每一個自變量對因變量都是顯著的,所以想要在回歸方程中,刪去那些無關緊要的變量,從而建立起更簡潔的回歸方程,對于我們能夠更好的可以看出自變量與因變量真正的聯系,因此我們就必須對單個回歸系數進行顯著性檢驗。可以容易得到,某一個自變量Xu對y不顯著,那么該回歸系數在方程里就等于0,所以我們可以得到原假設和備擇假設:H0:βu=0,H1:βu≠0,(u=1,2,…p)。由于參數分布的性質可以知道,回歸系數的估計量服從正態分布,那么就可以得到統計量服從自由度為(n-p-1)的t分布。 t=■~t(n-p-1)(3) 在給定的顯著性水平情況下,若自變量是不顯著的,應當考慮從方程中刪去該自變量再進行擬合。 利用最小二乘法建立多元回歸模型,初步得到以下模型: ln(fgdp)=-15.7471-0.0267ln(wage)-0.6343ln(loan)+0.4260ln(premium)-0.2779ln(saving)-0.2558ln(move)+2.9445ln(productivity)-0.4577ln(agdp) (4) 我們發現此模型的判定系數(R2)較高,達到了0.9951,說明模型解釋能力較強,同時D.W值為2.351,排除了自相關的干擾。但具體考察各個解釋變量的系數顯著性,發現職工平均工資、人均生產總值等變量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未通過檢驗,且個別變量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為了模型的可靠性,對模型進行優化,剔除了部分變量,得到如表2的結果。 模型如下: ln(fgdp)=-17.5501-0.4194ln(saving)-0.4004ln(move)+2.4567ln(productivity)(5) 剔除變量后,判定系數(R2)下降到0.9914,說明剔除的變量在統計上不顯著,D.W值為1.888,可以更好地排除自相關的干擾,且各變量均能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這說明這三個變量對我國金融業發展有顯著影響。 (一)居民儲蓄存款 根據回歸結果,我們可以發現居民儲蓄存款與金融業的發展是呈現負相關的。如圖1所示,近年來居民儲蓄存款出現下降或少增的趨勢,這有利于改善金融資產結構。我國是一個以銀行為代表的間接融資占絕對主體的國家,如今儲蓄存款流入股市等金融機構,雖然導致了儲蓄的少增現象,但提高以證券市場為代表的直接融資市場的比例,使得資金不會過分集中在銀行內,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金融結構,從而促進了金融業的不斷成熟。 (二)就業人員流動 在相關歷史文獻研究中勞動力的流動在某種程度上能夠促進產業的發展。本文中用金融行業從業人員數占全市從業人員數的百分比表示就業人員流動。由圖2我們可以看出這個指標近20年大致呈現逐年遞增的趨勢,同時由圖3我們也能看出全市從業人員除個別年份外也呈現上升趨勢,說明隨著金融業的發展,金融行業的從業人員逐年增加并且增加幅度超過全市從業人員數。然而,在本文的模型中,就業人員流動指標的系數卻為負,說明隨著第三產業的蓬勃發展,金融行業作為第三產業的代表行業吸納了許多高校優秀人才,但與此同時也吸引了越來越多來自第一、二產業的農村勞動力,然而這些勞動力資本和技術含量不高,不利于金融行業的健康發展。 (三)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 由于第三產業迅速發展,吸納了越來越多的勞動力使得其勞動生產率逐年上升,對金融行業的發展有著顯著的促進作用。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的目的在于探究行業發展與就業人員流動之間的關系,綜合就業與產業理論以及相關歷史文獻可以得出如下結論:擴大就業規模。在經濟發展達到一定水平的地區,就業規模的擴大,提高行業就業水平,在短期內可以促進行業的發展,且就業結構應適應產業結構。優化人力資本結構,使就業結構適應產業結構。雖然就業水平的提高有利于行業的發展,但是金融行業等生產性服務業作為知識密集型產業,對就業人員的技術水平與知識儲備有著較高的要求,如果只注重就業人員數量的增長,忽略對人才素養的要求,反而不利于行業的健康發展。所以,一方面需要注重本市人才培養,為本市重點行業的發展儲備人才,打下有力基礎,另一方面也要重視人才引進,特別是精通金融、技術等的復合型人才,同時也要對已從業人員進行繼續教育,定期進行員工培訓,使其適應行業發展要求。 參考文獻: [1]Pack, Howard.“Inter-industry labor mobility in Taiwan, China.”[M].The World Bank,1999. [2]Basile, Roberto, C. Donati, and R. Pittiglio.“Industry structure and employment growth: evidence from semiparametric geoadditive models.”[J].Mpra Paper 2013(38). [3]Franco, April M., and M. F. Mitchell.“Covenants not to Compete, Labor Mobility, and Industry Dynamics.”[J].Journa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trategy 2008(17). [4]中國統計出版社.上海統計年鑒[M].上海統計局,1997~2017. [5]張杰.勞動力流動與第三產業發展的關系研究[D].重慶大學,2013. [6]劉東閣.勞動力流動與生產性服務業發展互動研究[D].西南大學,2016. [7]吳娜,欒貴勤.上海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的協調發展研究[J].中國集體經濟,2014(04). [8]郭瑞東,周愛軍.區域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的協調發展研究[J].商業時代,2011(07). [9]朱象賢,宋建民,李和平.上海三次產業的發展與就業問題分析[J].上海綜合經濟,2001(11). [10]白利娜.我國勞動力職業流動的影響因素及其對收入的影響研究[D].山東大學,2013. [11]蔡禾,張東.中國城鎮勞動力市場中的職業流動及收益——基于CLDS2012年和CLDS2014年數據的實證研究[J].江海學刊,2016(03). [12]陳國亮.新經濟地理學視角下的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研究[D].浙江大學,2010. [13]孫青芬.中國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及影響因素研[D].東北財經大學,2012. [14]藍文妍,朱勝勇,李江帆.第三產業生產服務與第三產業生產率:理論與實證研究[J].產經評論,2014(05). [15]郭文杰,李澤紅.勞動力流動、服務業增長與經濟結構轉換——基于中國省際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9(11). [16]張月友,劉志彪.替代彈性、勞動力流動與我國服務業“天花板效應”——基于非均衡增長模型的分析[J].財貿經濟,2012(03). (作者單位:上海對外經貿大學統計與信息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