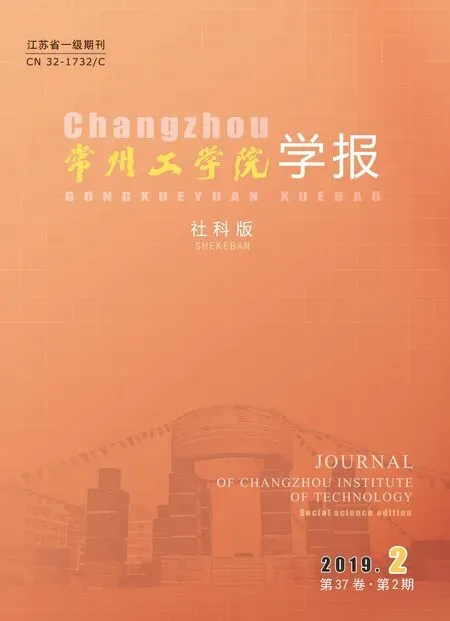遼寧省博物館藏《姑蘇繁華圖》建筑樣式考述
張新榮,秦媛,計玥玥,徐印,錢葉琳
(常州工學院藝術與設計學院,江蘇 常州 213022)
引言
《姑蘇繁華圖》,原名《盛世滋生圖》,是清代畫家徐揚描繪當時蘇州風物的一幅宏偉長卷,畫面紙本,設色,卷長1 241 cm,高36.5 cm。畫家徐揚,字云亭,蘇州吳縣人,常住蘇州府閶門城內專諸巷,擅長山水、花鳥、人物等。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皇帝南巡至蘇州,其繪畫才能得到乾隆賞識,遂被任命為畫院供奉,后被欽賜舉人,授內閣中書。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徐揚完成了《盛世滋生圖》,畫作獻皇帝后被藏于清宮廷御書房,清王朝覆滅時末代皇帝溥儀攜畫輾轉至長春,后該畫流散于民間。1948年,此畫由東北文物保管委員會收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由東北博物館即今天的遼寧省博物館所藏,為國家一級保護文物。至于此畫的真偽也有人曾提出異議,認為它是當時清末宮廷管事者與太監的調包偽作①,但在沒有出現其他真跡前,此畫應是唯一的真品。蘇州博物館原館長張英霖在《畫家徐揚傳記》里介紹有一幅《姑蘇城圖》出自徐揚之手,故此能理解為什么《盛世滋生圖》所繪蘇州山水、村鎮、城池和主要建筑物不僅形象逼真,而且其方位和相互間的距離都相當準確,這顯然是與徐揚在地圖方面的造詣和成就有著密切的關系②。
此畫可以再現250年前“乾隆盛世”時期江南蘇州府城的世俗風情。畫中山川、林木、城池、橋梁、碼頭、舟楫、寺觀、衙署、街巷、商鋪、民居一應俱全,還有學塾、會館、戲臺以及商鋪門面眾多的商幌、牌匾,另有婚娶、宴請、雅集、授業、科考、出巡、演藝、田作、買賣、造屋等生動場面,是當時江南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的真實寫照。“其圖自靈巖山起,由木瀆鎮東行,過橫山,渡石湖,歷上方山,從太湖北岸介獅、和兩山間入姑蘇郡城,自封、盤、胥三門出閶門外,轉山塘橋,至虎丘山止。”③作者自西向東,由鄉入城,穿城過街,重點描繪了一村(山前)、一鎮(木瀆)、一城(蘇州)、一街(山塘)的景物,畫筆所至,連綿數十里內湖光山色、水鄉田園、村鎮城池、社會風情躍然紙上。經粗略估算,全畫有市招、商幌的商鋪260余家,橋梁50余座,船只400余艘,人物4 000余人④。全畫非常細膩地刻畫了當年江南蘇州城的繁榮景象,具有極高的歷史、經濟、美術、藝術設計等研究價值。
關于《姑蘇繁華圖》的既往研究不是太多。縱觀國內外研究,大致有這幾方面:(1)從歷史學角度進行研究,一般都以圖版解說的方式,介紹這幅畫卷描繪內容考證后的研究結果;(2)從經濟學的視角進行研究,根據圖卷中所繪內容,涉及的各行各業場景,分析清代蘇州城的經濟繁榮情況;(3)從建筑學角度進行研究,通過詳細解讀這幅畫卷,以畫中內容為中心,考察江南地區親水城市空間的多樣性;(4)從美術學的視角進行研究,通過鑒賞優劣真偽、分析比較表現題材,研究繪畫的內容、表現對象、運用手法等;(5)從設計學的角度進行研究,圍繞繪畫中涉及的街路景觀,解讀傳統城市的景觀特征,論證該圖的資料性等⑤。
本文基于設計學的角度,著重對《姑蘇繁華圖》中的建筑圖像進行分析研究,并依據蘇州“香山幫”⑥姚承祖⑦《營造法原》⑧中提到的建筑營造立面樣式及屋頂樣式,進行考證、辨識及比對分析,揭示原有的歷史風物場景,明確畫中所描繪建筑圖像的真實樣式,使一幅歷史題材的風物畫兼具設計學和建筑學的借鑒意義,給當今的建筑遺產保護及建筑樣式傳承研究提供參考。從畫中所涉及的眾多建筑圖像來看,畫家描繪的是清乾隆時期蘇州地區較盛行的建筑樣式,大致可分為3類:第一類為普通民居、店鋪等;第二類為官衙、商行、宅院及樓閣、亭廊、水榭等;第三類為城樓、戲臺、寺觀等。按《營造法原》以房屋規模大小、使用性質劃分,將房屋建筑分為平房、廳堂、殿庭3種類型,由于房屋構架、屋面構造不同,其房屋外觀(其實質是屋頂外觀)又可分為硬山、懸山、歇山、四合舍(北方叫廡殿)、回頂(北方叫卷棚)、攢尖等樣式⑨(圖1—圖3⑩)。蘇州地區平房類硬山樣式較多,大量存在于普通民居及店鋪的外觀中。廳堂類(包括二層樓廳)外觀主要有硬山與歇山樣式,以及不筑屋脊的回頂,其規模、等級比平房要高,大量用于畫中的商行、衙府、宅院以及樓閣、亭廊、水榭等園林建筑的外觀中。由于殿庭類規模、屋面構造等級更高,其外觀式樣涵蓋了硬山、四合舍、歇山、懸山等多種樣式,但一般在民間較少使用,畫中偶爾會出現在城樓、戲臺、寺觀以及園林建筑中。另外,畫中民居、商鋪等建筑圖像外觀還常常出現3種山墻樣式,最普遍的有硬山墻和屏風墻,另有少量觀音兜墻。
根據《姑蘇繁華圖》畫卷自右往左的順序,另外也是按照畫幅描繪的村鎮、府城、街巷的三大主題內容,更是為了建筑圖像外觀樣式考證和辨識方便,把畫中的建筑圖像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為蘇州城外靈巖山前、木瀆、橫山、石湖、上方山以及獅、和二山之間的村鎮建筑圖像;第二部分為蘇州盤、胥、閶城門內外衙府、宅院、商肆等的府城建筑圖像;第三部分為蘇州山塘橋至虎丘山之間的街巷建筑圖像。

圖1 硬山樣式 圖2 懸山、歇山、四合舍樣式 圖3 攢尖樣式
一、蘇州城外村鎮建筑圖像外觀樣式考證和辨識
畫卷右起靈巖山前,主要描繪了一小村落及山林雅集景象。村落名山前村,主體建筑為一大戶人家,中落有五進進深,后進院子很大,院中兩名蘇地村婦正在與一名男工將一匹輕紗上漿、繃緊。邊落一側為各種工房,可能是用作織布的輔房,很顯然這是一家家庭式作坊。房屋外觀不乏硬山、硬山回頂等樣式。另一側為后花園,園中有圓形攢尖涼亭一座。中落由頭進三開間門屋起,二、三、四進均為三開間房,第五進較開闊,為五開間房。其中,二進廳應為接待賓朋應酬之大廳(或茶廳),畫中有匠人正在架梯上房鋪設瓦件。從新修建的房屋外觀來看,該二進廳外觀為硬山回頂(不設正脊而直接用黃瓜環瓦鋪設成黃瓜環脊的做法)樣式,三進房屋比其余都要高出許多,為二層樓廳,應是女眷起居之所,該大戶人家中落房屋外觀樣式除正在修建的二進廳為硬山回頂外,其余全部是普通硬山樣式。緊挨大戶人家為一書塾(或許屬大戶開設),有房屋四至五棟,除一棟敞開式為歇山回頂外,其余全部為硬山回頂樣式,敞開式建筑里能非常清楚地看到書塾老師正在授課、三位學童正在學習的情景。從這里也不難看出書塾房屋的外觀往往比較雅致,常采用回頂或歇山回頂作為房屋造型樣式,兩側歇山山墻都做弧形磚砌博風及線腳,與弧形回頂屋面相稱,順歇山面屋檐檐下再挑出涼棚,起到遮陽效果,畫家如此細膩寫實的筆墨,把書塾的外觀描繪到了極致。村落其他幾戶人家住房外觀卻基本都保持了嚴謹的硬山樣式。村口還繪有二進寺廟(應是靈巖寺下院)一座,其門屋和廳堂外觀均為歇山頂樣式(圖4)。另外,靈巖山游雅集除描繪蒼翠茂林外,也描繪了少量歇山頂、攢尖頂、硬山頂的園林建筑圖像,其中有兩亭據傳為乾隆十五年乾隆首次南巡時命名,后又恢復原名。古木蒼翠中有四面敞開之歇山式書樓,里面有一長者與一書生相向而坐,長者正伏案揮毫,這長者可能就是當時蘇州著名詩人沈德潛,該書樓應該是沈之別業書樓。書樓三面也都挑出遮陽棚,樣式雖然簡陋卻透著古雅,給畫面陡增了些許書香之氣。
畫卷再右起木瀆,主要描繪了山水間木瀆鎮的繁忙景象,而昔日的“斜橋分水”曾為木瀆十景之一,畫家對此處景色使用了非常飽滿的筆墨,涉及大小建筑百余棟。大部分建筑為臨水面街的一至二層商行,行業涉及酒樓、銀樓、綢莊、米行、糖果店、糕團店、雜貨鋪等,面闊二至三間不等,建筑外觀往往取雙坡硬山樣式,另有少量回頂。在西起山腳下的河流拐彎處,小院里有兩棟房屋不設屋脊,僅做回頂,院墻完全采用碎石拼砌,旁邊為雜貨行。對面臨河為開放式廳堂,屋檐下挑出遮陽棚,里面所繪人物似正在進行自娛自樂的三弦彈唱,斜對面臨河是米行,畫家將過往船只正在泊岸交易和裝卸貨物以及蘇州彈唱的情景表現得惟妙惟肖。畫中單孔拱橋即東安橋,今叫邾巷橋,過東安橋有一家規模很大且鋪面掛有“當”字店招的當鋪,為二層三進,頭進、二進均為二層,后進為一層,鋪面面闊五間半,留出半間可能是做通向內里的陪弄(蘇州許多民居邊上都設有陪弄),奇怪的是該當鋪樓廳前后兩進二層樓兩側山墻應全部為五山屏風墻樣式,但靠橋堍一側屏風墻懷疑是畫家筆誤,畫成了“七山屏風墻”,這在《營造法原》里未曾提及,蘇州傳統廳堂類建筑屏風墻一般為三山屏風和五山屏風兩種(圖5)。當鋪屏風山墻一側有通向后面一座寺廟的木柵門,一進木柵門是一座類似于觀音兜的屋頂(山墻圓尖稍比回頂山墻尖寬些,疑是早期觀音兜樣式)。后面寺廟規模不小,據了解是當時的木瀆城隍廟,共有五進建筑,除后院中央為一座二層重檐攢尖頂鐘樓,余下全部為歇山屋頂樣式。東安橋這一側大都為單層雙坡硬山造,其中只有一座臨河酒樓或茶樓為二層樓廳,左右不設山墻封砌,全部由木梁柱支撐,四面通透,造型別致,當屬廳堂類建筑中的四面廳,外觀為重檐歇山回頂樣式。另外,東安橋下則描繪了蘇州人家乘船嫁女兒的隆重場面,大小兩艘船上張燈結彩,高懸“狀元及第”“翰林院”字樣燈牌,據說能寓意將來子孫登科及第,“狀元橋”應由此出。西安橋邊主要是碼頭,建筑圖像大多為單層雙坡硬山樣式。
逐初園及周邊牽涉建筑圖像更多,除外圍臨水面街店鋪、會所、官衙等建筑圖像大量為硬山樣式外,少量夾在其中的寺廟、道觀則繪成了歇山樣式,河對面一群僧人魚貫而出,該寺觀可能就是后來的竹林庵所在,其建筑為歇山樣式。吳銓精心構筑的逐初園主體幾乎為兩面臨水,里面的亭廊、水榭、樓閣幾乎涵蓋了硬山、回頂、歇山、歇山回頂、攢尖等多種建筑外觀樣式,并給各色建筑起名“拂塵書屋”“聽雨蓬”“凝遠樓”“清曠亭”“補閑堂”等。建筑三開間居多,少有樓廳,園內主體三間廳堂緊聯一間軒廳,四面通透,該是蘇州人特別喜歡的“外坡屋或帶廊”樣式,內里絲竹悅耳,歌舞升平,高朋滿座,有青衣和童子扮相者位列中間,似正在進行一場家庭式堂會(圖6)。隔水相望有另一處規模很大的建筑群落是木瀆社倉,社倉幾乎三面臨水,交通便捷。逐初園東面是木瀆十景之一的法云庵所在地,建筑規整寬闊,寺邊有街肆,附近還有窯貨鋪,整個逐初園周圍建筑圖像豐富,亭廊、樓閣也不少,外觀有硬山、歇山、攢尖等樣式。
畫卷從石湖一路由西往東,到獅、和二山間所繪各色建筑圖像時疏時密,石湖主要以描繪山水風光為主,建筑顯得異常稀少,外觀樣式以雙坡硬山造為多。從獅、和二山到懷胥橋描繪的建筑圖像比較豐富,除普通硬山造外,又出現一棟五山屏風外觀樣式,圖像繪制非常工整。最顯眼的莫過于描繪了眾多人物圍在一棟建筑周圍看社戲的場面,依據此建筑開間和進深來判斷,應為殿庭一類建筑無疑。據說蘇州每年二、三月間有舉行春臺社戲的習俗,用杉木、竹子和彩綢在露天搭建戲臺進行表演。該建筑采用重檐結構,歇山頂樣式,三面通透,朱紅木柱或竹柱,矮檻墻上裝朱紅吳王靠,建筑看上去工藝精湛,等級極高。較為特別的是,在建筑前面高豎一面黃色幡旗,上書“恭謝皇恩”四字。畫家把該建筑屋頂全部畫成金黃色,其上張燈結彩,披紅掛綠,可以說畫家已極盡所能,把整個社戲場面描繪得非常熱鬧(圖7)。

圖4 靈巖山山前村 圖5 木瀆東安橋堍

圖6 木瀆逐初園 圖7 春臺社戲
二、蘇州城門內外府城建筑圖像外觀樣式考證和辨識
視線從畫卷獅、和二山山腳下的大量商鋪建筑往左移動則到了姑蘇城西南胥門城墻下,右邊稍遠處無疑就是封門和盤門,畫家筆下封門、盤門城墻自右至左途經胥門蜿蜒曲折,非常壯觀。城外河面寬敞,百舸爭流,水路運輸、碼頭停泊,喧鬧嘈雜。河道兩旁各色商店、貨棧、典當行等建筑繁多,整個畫幅用城墻把畫面分成城外和城內兩大部分,城內城外大小建筑共計幾百棟。胥門城外河道對面接官廳碼頭(過去俗稱),兩艘官船正在泊岸,碼頭上似匯集了許多官員,正備好轎子準備迎接朝廷達官貴人。城墻腳下則匯集了豬行、米行、典當行、棧房等各色自由貿易建筑群,建筑樣式基本為普通的單層雙坡硬山平房。河道邊懷胥橋畔、棗市街一帶卻分布了許多開間為二至三間、層高有一到二層的掛滿各色老字號招牌的商行,其中不乏雜貨行、餐館、戲樓、浴堂等,許多商行為兩層樓廳,雙坡硬山和硬山屏風墻的外觀樣式,有兩棟帶屏風墻建筑都為二層樓廳,其中規模稍大的三開間商行上下層除兩側五山屏風墻封砌外,屏風墻頂端還能清楚見到蓋有較小坡屋頂和屋脊,房子前后都很通透,鋪面商幌、招牌字跡清晰可辨。懷胥橋堍有家“香水浴堂”,進院門建筑為普通硬山屋頂,后進卻為一圓形穹頂,外形酷似饅頭狀,與古羅馬人的浴堂屋頂相似,而蘇州諺語里有“七搭、八幢、九饅頭”之說,這里的饅頭就指浴堂(圖8)。橋堍另一側有戶人家二樓為半露臺,似有名伶于露臺獻藝,畫家把露臺上硬山屋面的瓦楞、屋脊、挑出一半的涼棚、樓面朱漆護欄、紅地毯,甚至正在歌舞的名伶、兩旁的樂師等都描繪得非常清楚。過懷胥橋沿河也商肆林立,有糕點行、染坊等,屋前晾曬有布匹的染坊進深四進,高墻包繞,除前后幾進為硬山屋頂外,第三進為五山屏風墻造型,在此處顯得尤為獨特。旁邊是一家緊挨碼頭的木柵欄轅門,轅門內外正有人挑擔進進出出,疑是一家官府或貨行。城外遠處還繪有黃色八角攢尖頂的萬壽亭和開間寬闊連爿都為硬山造的姑蘇驛等建筑圖像。而作為遠景的城內建筑圖像卻比較規整,布局大多以圍合式院落沿著軸線展開,以硬山樣式居多,遠處還繪有許多等級較高的重檐歇山建筑圖像,其中和豐糧倉、蘇州文廟、瑞光塔等清晰可辨。

圖8 胥門懷胥橋堍
沿城墻再往左到了萬年橋堍城墻腳下的半截街,不長的街上有兩家店鋪特別有名,一家是售書的“大雅堂書坊”,另一家是銷售傳統樂器的“鳳鳴齋”,它們和其他商行并排在一起,均為兩層樓廳,開間三至五間不等,大的甚至達到七間,樣式大都為硬山墻,偶見硬山屏風墻。城內建筑圖像非常豐富,東西向的道前街(過去是衙前街的一段),掌管全省刑獄和官吏考核的江蘇按察司署(俗稱臬臺衙門)位于此。往東遠處的那座橋叫西貫橋,西貫橋北那座特別高聳的重檐歇山頂樓宇就是蘇州知府衙門的黃堂。城內靠著城墻并與城墻平行的南北向街叫學士街,沿學士街往北有一座很高的拱形橋就是黃鸝坊橋(古稱黃牛坊橋),黃鸝坊橋西堍有歇山式回頂過街樓一棟,橋西堍南通學士街,北接吳趨坊,橋西首還有黃鸝坊橋巷,附近環境清幽,是一些富商、歸田官宦及文人的居住地。整條學士街商業亦盛,掌管江蘇民政和財政的布政使司署(俗稱藩臺衙門)即位于學士街。
萬年橋兩側橋堍有四角攢尖小亭,與長方形涼廊相接,涼廊屋頂造型為典型的回頂樣式。萬年橋對面城內,畫家重點刻畫了正在蘇州臬臺衙門府進行“府試”的壯觀場面。衙前街上站滿各色接待和安保官員,似感戒備森嚴,大門前高掛紅底黑字“天開文運”牌匾,衙前橫街雙坡屋頂的白底牌樓上各書“吳中天府”和“春申舊跡”墨字。頭進大門為三開間大屋,對面建同樣三開間照壁一座,二進儀門完全是官式建制,中間三間高闊、深遠,屋檐前高后低(蘇州地區廳堂較之普通平房檐口更高,進深也更深,無論規模、結構、裝修要遠超平房),兩側有相對較矮小的耳房扶持,左右廂廊開間寬闊,布局對稱,里面考生座無虛席,三進大廳更加寬闊,其后還有四進、五進廳堂,建筑圖像大多規整有序,建筑沿軸線分布,開間寬敞。廳堂外觀除硬山外,兩側脊下還做磚砌博風,顯得等級極高,衙門的整體布局全然是清代鼎盛時期官式建筑的形制(圖9)。與衙前街平行的橫河兩側布有臨水或沿街商行,三、五開間較多,一層、二層常見,外觀絕大部分都繪成雙坡硬山屋頂,偶有歇山點綴。
學士街藩臺衙門府(原為王鏊別墅,名怡老園,后改建衙門)及東邊吳縣文廟等,建筑分布更加規整有序,各色建筑圖像繁多。藩臺衙府外高掛兩面黃色幡旗,上書“江蘇總藩”,旗下左右各有歇山式吹鼓亭,兩道木柵欄(舊時即轅門)和麒麟照壁頂端都做雙坡屋頂,轅門內外許多衙役正肩擔裝有銀兩的木桶過儀門送往庫房,儀門為雙坡硬山屋頂,兩側山墻做博風和勒腳,門口設有抱對,看上去等級更高,足以證明畫家觀察生活非常細致。進入庫房門廳后,后進廳堂為雙坡屋頂緊連軒廊的樣式,堂前站立一群人,似在驗收入庫銀兩,此建筑外觀較奇特,可謂“香山幫”經典樣式(圖10)。再往里是怡老園舊址,里面除大量的普通硬山房屋外,庭院還堆山疊石,古木蒼翠,充滿山野情趣。黃鸝坊橋堍過街樓西面,緊靠城墻的大戶人家正在舉行婚禮,建筑布局為四面圍合,因用途不同建筑高矮錯落,外觀都為硬山樣式。此處有少量建筑也作磚砌博風,山墻下還做勒腳,足以證明畫家對當時的建筑營造與裝飾有詳細的了解。
畫家筆下的閶門(春秋時期建造的吳國都城八門之一,明清時期商市特別繁榮)城樓畫得很雄偉,閶門城外吊橋(最早為無樁木橋,像彩虹故名虹橋,因可升吊后又改為吊橋)上的小商小販畫得生動有趣,橋兩邊為敞開式連廊,連廊屋面鋪成簡單的回頂,各路商販在忙著招呼自己的生意。右邊橋堍下各色鋪面井然有序,一層房屋、二層樓廳硬山、歇山高低錯落。往左北碼頭沿岸各路商船川流不息,從渡僧橋到山塘橋之間有“小磨麻油”“茶食糕點”“山東蘭綢”“南京板鴨”“云貴雜貨”等各色店鋪,其中外觀大都是普通硬山樣式。閶門城墻上坐落三開間兩層重檐歇山頂城樓一座,這應是此處最高的建筑了,登高遠眺,遠處南宋遺物重檐復宇八角北寺塔高高聳立,城內桃花塢、校場、唐寅晚年故居等景色一覽無余,遠處還有重檐歇山頂廟宇群落。畫家把閶門城內閶門大街的商行畫得高矮有序,大街一側大多為兩層樓廳,三至五間不等,排成直線,另一側則是自由松散的圍合布局,使橫平豎直略顯呆板的建筑仿佛活了起來,閶門城內至今仍保持這樣的布局,有各色商行,如絲綢店、藥材鋪、皮貨行等。另外,建筑外觀樣式也是硬山、硬山屏風、歇山等各種樣式交替穿插在一起,從而使整個畫面更加生動活潑(圖11)。

圖9 萬年橋堍和臬臺衙門 圖10 藩臺衙門 圖11 閶門內外
三、蘇州山塘街街巷建筑圖像外觀樣式考證和辨識
山塘街地處閶門城外,因山塘河形成街市,由于山塘河各支流水域縱橫交錯,故山塘街建筑分布基本都是面街背水。畫家筆下順著山塘橋往左,沿山塘河一直畫到虎丘山,把山塘街及其周邊沿河分布的建筑表現得淋漓盡致,總計大小高矮建筑有百余棟。山塘街地處城郊接合部,畫家筆下建筑圖像雖沒有那么規整,卻也不失整齊排列,山塘橋堍靠河一側為背水面街商行,建筑大都為單層有序排列,進深基本為一進,相鄰建筑間時有店鋪共用的小碼頭,為商船運送貨物停靠和生活用水提供方便(圖12)。橋堍對面為一層或二層商行間隔民宅,因不背水進深一般達到三進甚至四進,內設庭院并開院門,商行大都為前店后作坊。其中有一家面街住戶門口畫家描繪了前來道賀送禮的人群,廳堂里有一群老者正在雅會。相鄰還有一所義學(過去蘇州興盛辦義學,主要是為無力攻讀的清貧子弟提供學習機會),敞開的廳堂里有八九個學生圍著塾師讀書。過山塘橋自東往西到半塘橋,沿河描繪了許多布行、染坊、酒樓等建筑,規模大的二層商行大都為三開間鋪面,其間也夾雜著一些單純生活用住宅(圖13)。由半塘橋再到普濟橋沿河又出現花市,到斟酌橋就看到虎丘山了。此段建筑圖像外觀幾乎全部是雙坡硬山造,顯得非常單純。
沿山塘河往虎丘山方向的商行或住宅基本都退到堤岸后,空出堤岸方便行人流動或貨物運輸,建筑為一層或二層,外觀為雙坡硬山造,高低相錯。普濟橋下店鋪間還有園林和寺觀夾在其中,園林內堆山疊石,古樹蒼翠,亭廊高低分布,亭造型為八角攢尖,廊外觀為橫長方形前后敞開式回頂。靠園林一側坐落的寺觀規模很大,出入的山門建筑有四進,主殿五開間大小,左右對稱廂房也有三開間,畫家把里面建筑全部繪成觀音兜狀(也有點像回頂),主殿和廂房兩側弧線形山墻均高出屋面,沿屋面山墻還砌筑磚博風(圖14)。
畫卷最后是虎丘山及其寺廟,從正山門到三山門,大雄寶殿、千佛閣、珈藍殿、云巖塔,建筑順著山坡布局,建筑圖像大多數是歇山頂樣式,兩層高的重檐歇山也不少。

圖12 山塘橋堍 圖13 山塘街半塘橋 圖14 山塘街園林和寺觀
四、《姑蘇繁華圖》中建筑圖像外觀樣式分析綜述
縱觀《姑蘇繁華圖》所涉及的建筑圖像,基本能夠清楚辨識的,單層雙坡硬山樣式數量最多、最普遍,二層樓廳硬山樣式次之,硬山回頂也較常見。硬山回頂樣式約有27處,其中,山前村出現5處(包括正在施工的1處),山腳下河邊石砌院墻內1處,木瀆沿河3處,木瀆逐初園內園林廊廡及其他房屋共計6處,旁邊園林內1處,還有遠景1處,胥門城墻腳碼頭旁至少10處;硬山屏風墻(包括三山和五山)樣式大約出現12處,其中木瀆出現2處,懷胥橋堍有3處,萬年橋半截街2處,閶門城內至少5處;觀音兜(或者似觀音兜)樣式有9處,在木瀆東安橋堍木柵門內出現1處,山塘街沿河寺觀內廳堂加廂房約有8棟房屋;歇山回頂(包括重檐)約有20處,其中山前村有2處,石湖至少10處,木瀆四面開敞樓廳及河邊小亭共有2處,木瀆逐初園內連著外坡屋的1處,胥門萬年橋兩堍連著四角攢尖亭的4處長廊也為歇山回頂,黃鸝坊橋西堍過街樓也是1處歇山回頂;圓形(似饅頭狀)穹頂在懷胥橋堍的“香水浴堂”有1處。余下的歇山、重檐歇山以及四角、六角、八角、圓形攢尖等園林建筑樣式也都很普遍。
硬山樣式因其涵蓋了普通平房及廳堂類房屋,故在畫卷中出現頻率相當高,從單層民居到兩層樓廳甚至規模較大的宅院、官衙內的建筑,如山前村、木瀆鎮、胥門城外、萬年橋堍、城內藩臺衙門等都曾出現。據《營造法原》,其外形是在雙坡屋面兩側筑山墻與屋面完全接平。山墻頂端可做博風,落底還做勒腳,墻兩端側面也做垛頭(北方叫墀頭)。屋面一般鋪設大瓦(做底瓦)和小瓦(做蓋瓦,廳堂、殿庭類也有蓋瓦采用筒瓦的),屋檐下看面裝滴水瓦和花邊瓦,等級低的屋脊兩頭不做裝飾,做成游脊,普通的兩頭做甘蔗脊,等級稍高的做雌毛脊、紋頭脊,更高的做哺雞脊、哺龍脊。畫家描繪的各色房屋之硬山樣式幾乎都有上述做法出現。而另外一種懸山樣式,其外形與硬山之區別僅在于屋面兩端桁(北方稱檁)要挑出山墻,挑出屋面下做木博風或磚博風,不知是畫家對透視掌握得不好還是就沒有出現懸山樣式,在藩臺衙門府內廳堂似有懸山刻畫,但仔細觀察還是硬山屋面下山墻頂端加磚博風做法,其他幾處也是如此,很難分辨。
硬山回頂樣式在畫面出現27處,其外形與普通硬山相差無幾,唯一區別是無需做屋脊,一般可以直接用黃瓜環蓋瓦和黃瓜環底瓦鋪設成黃瓜環脊就行。在山前村、木瀆沿河、木瀆逐初園、胥門城墻腳下碼頭旁均有出現。而山前村那一例,畫家把正在上房施工的情形都非常生動地表現了出來。
硬山屏風墻樣式在畫面中出現12處,可以說畫家對此情有獨鐘。其樣式出現最多處主要集中在閶門城內那條熱鬧的商業街,由此可見,屏風墻在城內要比城外更常見。而木瀆東安橋堍的當鋪樓廳還出現了筆誤,五山屏風畫成了七山屏風。其外形特征是在硬山基礎上把兩側山墻加高,一般中間單屏高于和寬于兩旁其他單屏或雙屏,每屏頂端還做屋面和屋脊,有三山屏風和五山屏風兩種。
硬山觀音兜樣式(或者稱似觀音兜)雖然在畫卷上出現9處,但外形跟回頂非常接近,按《營造法原》解釋,兩側山墻由下檐起成曲線至脊,高起若觀音兜狀才是觀音兜,并且有半觀音兜和全觀音兜之分,半觀音兜做法是只在屋面金桁處起高,全觀音兜做法是在屋面廊桁處就起高,而且全觀音兜還分兩種。畫家描繪的木瀆東安橋堍木柵門入口處似乎高起部分也不明顯。山塘街寺觀內幾棟房屋也都為似觀音兜外形,幾棟房屋正面和側面起高也不明顯,而且又缺少實地考證資料,所以只能說是“似觀音兜”,或者說還是屬于“回頂”,又或者畫家徐揚生活的年代壓根還沒有出現觀音兜樣式。
歇山回頂樣式出現至少20處,由于畫面中式樣都很簡單,所以基本限于廳堂類建筑。其外形是在歇山頂基礎上演化而來,一般把歇山頂的正脊改做成黃瓜環脊。歇山樣式因在屋頂兩側多出兩個三角形山面,故裝飾時可作為重點,如山前村的書塾屋頂,山墻看上去是磚砌博風做法,給山面平添了許多有層次的線腳。木瀆逐初園內正在舉行堂會的開敞式廳堂亦是如此,歇山僅做回頂,山墻頂端圓弧形線腳疊級連著磚砌博風頓覺多出幾個層次,使建筑外觀看上去更具文人氣息。
歇山和重檐歇山樣式主要出現在寺觀、城樓、戲臺一類建筑圖像上,畫家幾乎都以遠景處理,廳堂和殿庭類都有涉獵。胥門城樓為重檐歇山頂,建筑開間和進深較大,檐下有牌科(北方叫斗拱),屋脊兩頭似為魚龍脊或龍吻脊,根據其規模判斷當屬殿庭類。閶門城樓為重檐歇山頂,面闊三開間,兩層重檐頂,戧脊八出并有脊獸,正脊兩頭似哺龍脊,從其規模來判斷還屬于廳堂類。還有一例“春臺社戲”的戲臺是作為近景重點刻畫的,戲臺雖然為臨時搭建,但其正脊、垂脊(豎帶)、戧脊和四個坡屋面以及兩側山墻可以說畫家用足了筆墨,而且畫成重檐歇山,與《營造法原》圖版之歇山樣式幾乎無異,只是做法上簡化了許多,它上面一層屋頂有9條屋脊和4個坡屋面構成,下面為重檐,整個建筑扎滿五顏六色彩帶、彩球,其實是把一個戲臺建成了重檐歇山樣式。
四合舍樣式在畫卷能辨識清楚的建筑圖像上尚沒有發現,遠景中可能存在。
攢尖頂樣式因其體量小,在畫卷中大都作為點綴形式出現在寺觀和園林里,其外形最有特點之處是只有一個尖頂,也可重檐,屋頂下檐有四角、六角、八角和圓形等。如畫卷中山前村大戶人家后院、木瀆鎮城隍廟內、胥門萬年橋堍等有該樣式。攢尖作為亭的外觀樣式還經常與樓閣、廊廡、水榭等園林建筑同時出現在宅院、寺觀及衙府后院內,外觀變化往往比較自由。
五、結語
上述,只是我們對《姑蘇繁華圖》考證、辨識及分析后的一點粗淺見解,可能還有許多遺漏,昔日場景和地名或許也有謬誤,雖然極力想從蘇州香山幫《營造法原》里找尋有力的支撐證據,然有關外觀、外形的單獨論述實在不多,近年有圖解、注釋《營造法原》的書出版,才有所補充。而中國傳統建筑向來將外觀造型建立在木作構架及瓦作工藝等之上,即先有木構架的樣式,才有硬山、懸山、歇山、四合舍等屋頂樣式。而《營造法原》里把房屋還分成平房、廳堂及殿庭三類,甚至還提出木構架的各種貼式,還有各種組合,園林建筑更可以自由變化和發揮,使外觀樣式既簡單又復雜,簡單的是單體建筑就幾種樣式,而組群或變化后就顯得異常復雜。
然而,時代永遠在不斷發展,西方建筑文明的沖擊使中國傳統木構架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鋼筋混凝土建筑,外觀樣式也被徹底顛覆。更有甚者,為了迎合老百姓崇洋媚外的一時興趣,否定傳統樣式,給許多城市的建筑都穿上了“洋外衣”。其實,繼承傳統并非一成不變,一定要采用傳統木結構,新材料、新工藝一樣能建造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傳統樣式,只是我們忽視了身邊的傳統,或者說對傳統缺乏了解。唐宋到明清的建筑中,作為承重結構的“斗拱”的功能由“承重”逐漸演變為“裝飾”,其外觀也在繼承傳統基礎上有所變化。
本文試圖從設計學的角度,對《姑蘇繁華圖》中曾經真實存在的傳統建筑外觀樣式進行分析研究,并與《營造法原》中涉及的外觀樣式圖版進行比對,從而進一步了解蘇南地區傳統建筑的真實情況,以期能給蘇南地區建筑遺產保護、城市風貌傳承,或是傳統建筑知識普及帶來一些啟迪。
注釋:
①張燁:《徐揚〈盛世滋生(姑蘇繁華)圖〉卷的真偽辨》,《美術觀察》,2009年第2期,第100-103頁。
②徐揚:《姑蘇繁華圖》,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8年,第7-8頁。其中,蘇州博物館原館長張英霖所撰的《畫家徐揚傳記》作了介紹。
③《姑蘇繁華圖》(原名《盛世滋生圖》)卷末自跋。
④徐揚:《姑蘇繁華圖》,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8年,第12頁。其中,蘇州博物館原館長張英霖撰寫的文章《姑蘇繁華的真實寫照——介紹歷史畫卷〈姑蘇繁華圖〉》作了介紹。
⑤王潔:《從建筑與景觀解讀〈盛世滋生圖〉的資料性》,《華中建筑》,2008年第4期,第21-24頁。
⑥據“360百科”,蘇州香山位于太湖之濱,自古出建筑工匠,擅長復雜精細的中國傳統建筑技術,人稱“香山幫匠人”,史書曾有“江南木工巧匠皆出于香山”的記載。明代生于香山的北京天安門城樓設計者蒯祥,因其建筑技藝高超而被尊為“香山幫”鼻祖。從匠心獨運的蘇州古典園林到氣勢恢弘的北京皇家宮殿,數百年來,蘇州香山幫匠人的精湛技藝代代相傳,香山幫匠人的杰作蘇州園林和明代帝陵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⑦據“360百科”,姚承祖(1866—1938),字漢亭,號補云,吳縣胥口墅里村人。同治五年(1866年)三月十八日生于木匠世家,祖父姚燦庭著有《梓業遺書》,承祖11歲隨叔父姚開盛學木作,終歲營建于鄉郡間,一生設計屋舍庭宇不下千幢。民國元年(1912年)成立蘇州魯班協會,被推為會長,曾任教于蘇州工業專科學校。代表作有木瀆嚴家花園、蘇州怡園藕香榭、光福吾家山梅花亭、木瀆靈巖寺大雄寶殿等。所著《營造法原》被譽為“中國南方建筑之寶典”。
⑧《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年,第1626頁。《營造法源》(現一般寫成《營造法原》),一部較完整的蘇南地區傳統建筑術書。姚承祖原著,此書系根據其祖傳建筑做法和其本人的實踐經驗編成,印本經張至剛增編,劉敦楨校閱,1959年出版。此書寫成于1929年,姚承祖原委托劉敦楨校閱,劉無暇,于1932年轉“營造學社”社長朱桂辛校閱,但由于書中術語與北京官式建筑不同等原因,時隔數載沒有付印。直到1935年秋,劉敦楨又將原稿轉交他在南京工學院的學生張至剛,張是蘇州人,人地相宜,立即將此書增編。
⑨姚承祖《營造法原》第二章,平房樓房大木總例及附表建筑結構部件名稱對照簡表八:屋頂。張至剛增編,劉敦楨校,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1986年,第4頁及附表。
⑩圖1至圖3來源為侯洪德、侯肖琪所著《圖解〈營造法原〉做法》,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14年,第219-222頁。
圖4至圖14均來源于徐揚繪的《姑蘇繁華圖》,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8年,第67-9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