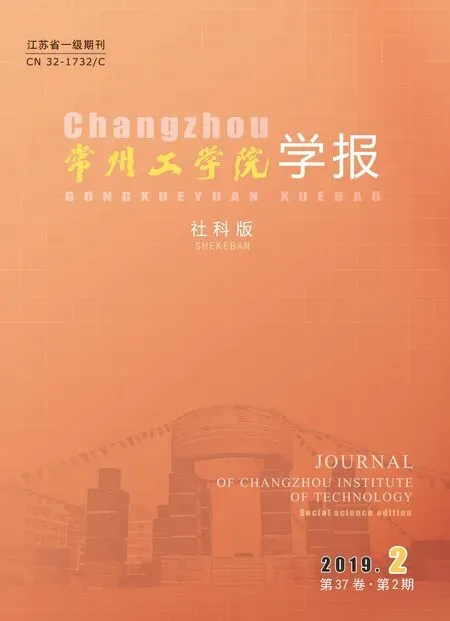李聞風通款太平天國時間考
施偉國
(常州工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江蘇 常州 213032)
在太平天國與上海小刀會(以下簡稱小刀會)的關系史上,與鎮江太平軍進行過書信聯絡的李聞風,無疑是一位頗具神秘色彩且又很難繞過去的關鍵人物。有關李聞風的身份問題,學界尚存在較大的爭議①。對李聞風上書太平天國的時間進行考察,或許對揭開其身份之謎有所裨益。
有關李聞風與鎮江太平軍進行書信聯系的情況,楊秀清在一封“交尚海李聞風弟等開拆”的信函中有所披露。知非子在《金陵雜記》中對此事有較為詳細的記載②:
股匪羅大綱偽冬官正丞相,盤踞鎮江……當上海另有別匪滋事之時,未久,羅賊即有稟至省中楊逆處云:探得上海另有一般人在彼已得城池,此一般人約有三四千人在彼云云。皆未敘出姓名。然羅處間日皆有信至省,隨后偽東王楊逆忽發出偽檄一函,曾有人密為私拆,其略云:“蓋聞識時務者為英雄,知進退者為俊杰,觀當今之大局,知真主為天王。三月間曾據欽差大臣羅大綱弟來稟:知弟等請攻蘇常,弟等在上海愿為內應,本軍師不勝欣慰,何以遷延至今?如果率眾來歸,必當奏請封加顯爵,何去何從希自諒之。”云云。……此偽檄系交付羅逆處,后不知羅逆處如何回復?偽檄是否私遞上海均不得悉。[1]625-626
就知非子引述的這封信函來看,楊秀清雖然沒有提到李聞風上書的具體時間,但卻特別指出,他是在“三月”(按:指天歷,公歷4月)間根據羅大綱的稟報而得知李聞風“請愿”情況的。這是一條重要的線索。按常理分析,從李聞風上書、羅大綱稟報,到消息為楊秀清所得,前后有十天至半個月時間似應足矣。因此,借諸信中所說的“三月”,完全可以推斷出李聞風上書的大致時間。而問題主要是,楊秀清在信中并沒有指出三月的具體年份,知非子在引述的時候也沒有加以特別說明。由于壬子二年(1852年)三月時,太平天國還在廣西境內轉戰,而到乙榮五年(1855年)三月時,小刀會起義已宣告失敗,故這里的三月,不可能出太平天國癸好三年(1853年)甲寅四年(1854年)的范圍。但究竟是癸好三年三月,還是甲寅四年三月,學界對此已做過一些解讀,盡管所據不盡相同,看法卻基本一致,認為這里的三月只能是甲寅四年三月③。但筆者認為,“甲寅四年三月說”值得商榷。
首先,從楊秀清寫信的時間看,“甲寅四年三月說”缺乏應有的邏輯依據。
由于資料所限,對“三月”進行正面釋讀還有諸多困難,以楊秀清寫信的時間來反推三月的具體年份,卻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方法。因為,楊秀清在信中之所以沒有對三月的年份進行具體說明,不可能是出于一時疏忽,最大的可能應該是,三月與他寫信的時間還處在同一個年份,沒有另加說明的必要。因此,“三月”與楊秀清寫信的時間之間存在著年份上的互證關系,如果楊秀清此信寫于甲寅四年的某一時候,則三月當為甲寅四年三月無疑;反之亦然。

其實,楊秀清在信函中使用的某些語氣措辭,也能夠反映出這方面的一些情況。其中的“何以遷延至今”句,很明顯是在小刀會起義之后,對當初李聞風等“在上海愿為內應”(即準備在上海舉行起義以響應太平軍)一事所作的回應,且不論這是否是楊秀清在故作姿態,按通常的行文習慣來看,這種具有較強即時性特征的反詰語氣,一般只會用于事后不久的某一時候。如果信中所說三月指甲寅四年三月,那么楊秀清此信必定寫于甲寅四年四月或四月之后,此時距小刀會起義至少已有8個月之久,若繼續使用這種語氣措辭,不僅已顯得沒有多少意義,還難免給人一種刻意刁難的小家子氣感覺,這與楊秀清在信函中所要表達的期望李聞風等“率眾來歸”的本意顯然是不相符的,斷不會為其所用。
其次,從羅大綱在鎮江的活動時間來看,“甲寅四年三月說”也與史實不相吻合。
據知非子記載,楊秀清不僅在得到羅大綱有關小刀會起義的報告后寫了這封信函,而且這封“交尚海李聞風弟等開拆”的信函也是交由鎮江的羅大綱轉遞的。因此,對“三月”的釋讀,除了要具體考察楊秀清此信有可能寫于何時之外,還必須進一步查證羅大綱是如何進行轉遞的。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都不能偏廢。按甲寅四年三月的說法,楊秀清此信最早得寫于甲寅四年四月,但作為信函轉遞者的羅大綱,最晚在甲寅四年四月的時候還得在鎮江任上。但這根本不可能。
據張汝南《金陵癸甲紀事略·粵逆名目略》“羅大綱”條記:“至金陵后,東賊使陷鎮江,即留守,嗣調守安慶等處。”[1]674張德堅《賊情匯纂》卷二“偽冬官正丞相羅大綱”條則明確記載:“甲寅二月調回江寧,令與胡以晃等上犯和、廬,三月據守安慶省,遂擾建德、東流等處。十月官兵收復田家鎮,群賊下竄,楊賊又令大綱據守湖口縣,以遏我師。”[4]61另外,曾經隨美國專使麥蓮等一起訪問鎮江,并與當時城內最高軍事長官吳汝孝有過接觸的裨治文,在1854年7月初給《北華捷報》的一封信中也證實:羅大綱大約是在“3個月前”被調離鎮江的[5]149。考諸史實,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早在甲寅四年二月(至晚到是年三月)的時候,羅大綱就已經從鎮江奉調回京,并很快奔赴了天京上游戰場。如果三月指的是甲寅四年三月的話,楊秀清又怎么能把這封最早應寫于甲寅四年四月的信函,交由甲寅四年二月就已經離開了鎮江的羅大綱進行轉遞?!
總之,不論是從楊秀清寫信的時間來看,還是從羅大綱離開鎮江的時間來分析,“三月”都不可能是指甲寅四年三月。筆者認為,這里的“三月”,只能是癸好三年三月。也就是說,楊秀清是在癸好三年三月而不是甲寅四年三月得知李聞風上書情況的。由于稟報李聞風“請愿”的羅大綱是在癸好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才率太平軍進駐鎮江,故可以斷定,李聞風與鎮江太平軍進行書信聯絡,時間當在癸好三年二月下旬到三月之間。
需要指出的是,李聞風在1853年春與鎮江太平軍進行書信聯系,與當時太平天國運動快速發展所引起的社會輿情的巨大變遷是相一致的。眾所周知,隨著太平軍攻克寧鎮揚三鎮,尤其是定都天京,清朝政府在江南地區的統治迅速陷入了混亂之中,而且,太平天國作為一支新興的政治力量,也很快引起了社會各方的密切關注。這場運動在展示自己對舊秩序強大的沖擊力和破壞力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在心理上給社會各界,尤其是下層民眾帶來了強烈的震撼與感召,一些不滿現狀、心懷異志的人士在各地紛起呼應④。以當時上海附近的情況看,更是呈現出了輿情洶洶、人心思動的多變局面,所謂“三年癸丑春,粵匪陷江寧、鎮江等郡,蘇省戒嚴,群不逞之徒,咸蠢然思動”[3]1087。作為小刀會主體的客居在上海的閩、粵人等,“皆是同情于太平軍者。人們預料如太平軍一到,他們都要加入其軍”,坊間甚至還傳出“閩、粵人將起事響應,先占上海以俟太平軍之來,然后獻城于天王為太平天國之一部”的說法[6]926。可以說,上海的李聞風等人向太平軍“請愿”,正是江南地區這種特定社會輿情的一種反映和結果。
若以李聞風通款太平軍的時間來看,李聞風為太平天國派駐上海的聯絡人員的說法非常值得懷疑。因為,當李聞風與鎮江太平軍進行書信聯系的時候,太平軍才剛剛進入天京和鎮江不久,要說這時太平天國就成功地向上海派出了自己的聯絡干部,未免過于牽強,其可能性實在微乎其微。李聞風不可能是天京方面派出的信使,而應該是小刀會方面的人物;且從其上書“請愿”來看,又不會僅是個一般性人物,很可能是其中的某位首領。當然,在現有小刀會首領的名單中尚找不到有叫“李聞風”的,筆者認為,這很可能是其中某位李姓首領使用的化名,尤其以福建幫首領李咸池,即李庭幗的可能性為大。
按:小刀會起事前,李咸池即在聯絡策劃、結會樹黨等方面用力頗多,為諸首領中最活躍的人物,“系首先倡亂者”[3]987,不僅名字久為地方“風聞”,還成為上海官府緝拿究辦的“首犯”[3]190。小刀會占領上海縣城時,李咸池“是重要首領之一,后來才勢力日減”[3]796;進攻太倉失利后出走福建,坐船由海道前往廈門,“尋見股首黃位,求撥鳥槍手二千名”[7]347。清軍攻克廈門后潛回龍溪老家,不久被官兵捕獲,遭凌遲處死。
注釋:
①羅爾綱、郭豫明等認為:李聞風為太平天國派在上海與小刀會做聯絡工作的干部(羅爾綱:《太平天國與天地會關系考實》,《羅爾綱文選》,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02頁;郭豫明:《上海小刀會起義史》,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上海分社,1993年,第116-117頁)。王慶成、朱從兵等則認為:李聞風是小刀會中人,但并非著名領袖,或為小刀會方面具體負責與太平天國聯系的專門人員(王慶成:《從劍橋大學收藏的劉麗川告示論太平天國與上海小刀會起義軍的關系》,《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第8頁;朱從兵:《上海小刀會起義與太平天國關系重考》,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07頁)。
②太平天國攻克南京之后,知非子曾在天京城內居住了一年多時間,以其親歷目睹匯集成《金陵雜記》,書中引述的楊秀清這封信函也歷來為史學界所重視和利用。
③王慶成認為:由于楊秀清是在得到了羅大綱有關小刀會起義的探報后才發出這封信函的,故此信至早應寫于甲寅四年四月,信中所說的三月也只能是甲寅四年三月(王慶成文,第7頁)。郭豫明則認為:知非子在上文說,楊秀清是在得到了羅大綱有關小刀會起義的探報后才發出這篇檄文的;下文說,“又夷人去歲(指1854年)至省數次”,可知三月的年份是咸豐四年即1854年(郭豫明文,第116頁)。學界有關太平天國與小刀會關系的其他論作,也基本上持甲寅四年三月說,不一一贅列。
④京城海甸的劉氏兄弟等也暗中串聯,向揚州太平軍投書,表示“愿為內應”“愿效犬馬之勞”(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檔案史料》第九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6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