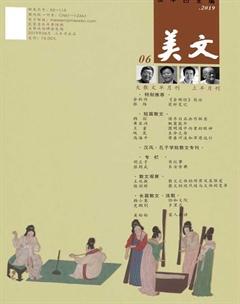楚辭筆記
張煒
戰國的激蕩
戰國時代,戰亂頻仍,民不聊生,整個社會動蕩不安。當時除了“戰國七雄”,還有其他諸侯及地域強人攻城掠地,爭奪不息,那是一個充斥著暴力血腥的世界。無數生命消失在混戰、饑餓和瘟疫中,人類為生存付出的代價之大超乎想象。處于這樣的歷史時期,生活簡直就等于掙扎,一切幸福似乎都談不上了。物質的生產與積累困難重重,那么進一步考察精神層面,又會是何等狀況?
這大概要進入一個非常復雜的話題。
人處于動蕩不寧的時代,就意味著更多的奔波,要飽受折磨,因為在一個需要不斷規避和抗爭、犧牲頻頻發生的時世,個體并沒有太多的選擇。可也就在這樣險峻艱難的客觀環境中,在拼博與砥礪中,人的能量又往往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激發和釋放。一些極端時刻,人性會變得較少遮掩和偽飾,似乎可以從不同的方向表現出一種極致:殘酷和憐憫、暴虐和仁慈、貪婪和慷慨。人類為戰勝悲劇掙脫絕境所投入的奮爭,與黑暗對峙所投射出的生命之光,將會格外地強烈和熾熱。這成為人類一些特殊的生命時段,這期間各種元素的交織,無數力量的糾纏,將時代活劇上演得淋漓盡致。戰國正是這樣的一個時代,它是人類歷史上鮮有比擬的一個特異時期:一方面荒涼凋敝,民不聊生生靈涂炭;另一方面又表現了罕有的思想飛躍和靈感激揚。
精神和藝術的奇跡在這個紛亂的時代里孕育誕生:繼絢麗的《詩經》之后,《楚辭》出世;諸子百家,星漢燦爛;被嘆為千古奇觀的“稷下學宮”誕生于齊國都城臨淄稷門,成為一場歷時百余年的思想與學術的盛宴。學宮集天下卓異,辯理說難,縱橫捭闔。當年連權傾一時的重臣和權力蓋世的君主,都投入了這場曠百世而一遇的思想大辯論。稷下文氣之盛,辭鋒之利,可謂曠百世而一遇。
戰國是一個苦難深重、血淚交織的群雄割據之期,也可以說是一個精神之域群星璀璨、藝術空前繁榮的偉大時代。大思想家孔子東行齊國,在首都臨淄聽了盛大的《韶樂》演奏,竟然陶醉至“三月不知肉味”(《論語·述而》)。那是怎樣一場華麗的視聽盛宴,今天也只有想象了。確定無疑的是,它出現在齊國都城臨淄,就發生在那個劇烈涌蕩的戰國。
我們不禁要問:與苦難并行的還有什么?與殘酷的七國爭雄同時呈現的還有什么?是遍地餓殍,四野哀號,一場接一場征戰;聲名狼藉的機會主義者和大陰謀家生逢其時,張儀蘇秦,搖舌鼓唇,各色人物層出不窮,他們在大地上穿梭往來,翻云覆雨,合縱連橫。這既是少見的大亂世,又是歷史的大舞臺。在一個充分“激活”與“激蕩”的時代里,生命中的各種能量都被呼喚和調動出來,呈一時之雄健奇偉。
我們或許找到了一個恰當的詞匯,從某個側面和角度來為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段命名,這就是“激蕩(激活)的時代”。
戰亂與紛爭必然導致群雄追逐,蒼茫大地上有可能出現許多相對獨立的板塊。這可以是一些稍稍封閉的空間,成為一些自治狀態下的較少互擾的分立的單元,在最小的局部甚至會有一潭靜水。類似的狀態即便保持很短一段時間,也將顯現特殊的意義。這里會有一些人與事的特例或個案發生,比如時代的窺視者和蓄養者、棄世遺世者、個體的思悟和修煉等等。因為生活再也無法在不同的角落里整齊劃一,縱橫交織的混雜格局中,有一些潮流無法席卷和滌蕩的邊緣地帶,這里,呈現壓倒之勢的強力一時未必悉數抵達。偷安和喘息時有發生,而這一切正是得益于戰亂,借助于分割。
在一些偏遠和封閉的角落里,一部分思想與精神的特立獨行者一旦得到休養生息的機會,就有可能煥發出驚人的創造力。他們作為個體的力量,這里主要指心靈的能量,會在這個空間里得到一次驚人的揮發。縱觀歷史,這種情形似乎是常常發生的。反過來,當整個世界安定下來為之一統,族群和地域的壁壘全部消融之后,一些獨立的空間也就不復存在。地理意義上的整齊劃一可以是“盛世”,是繁榮的基礎和機遇,但在許多時候也意味著精神與思想的集中和同質。如此一來也會妨礙千姿百態的呈現。藝術和思想的完成必須強化個體的意義,必須預留相應的空間,而這些條件的逐一達成,有時的確需要尋覓一些特別的歷史機緣。
在波詭云譎的戰國時代,有一些膽大包天、狂放激切的縱情想象,比如大九州學說的創立,比如縱橫家們日服千人的曠世辯才。這樣的奇才異能也唯有那個時代才能出現。我們只能說,在一個紛爭急遽、沖突四起的時空中,在一種危機四合的環境里,生命只有做出一次次極端化的拼爭才能實現突圍,甚至將生死置之度外才能謀求發展。也就在這樣的一個過程里,人類竟然譜寫出一些最為壯麗的篇章。
展讀整部人類史,我們還很少看到與戰國時期相類的精神格局,大致接近的,也許還有魏晉和清末民初。這都是一些極其混亂動蕩的社會,是時代將要發生巨變或正在巨變的過渡期。在這樣的境域下,大多數人都面臨了生之危境,都要被迫投入激烈的競爭,非如此而不能維系生存所需,失去延續生命的唯一機會。許多時候,人們除了掙扎反抗再無其他選擇,振作和奮起成為一種必須。從大的方面看,安逸不再,不安和恐懼頻頻襲擾,人們不得不對嚴酷的周邊環境做出迅速反應。也正因為如此,它催生出的思想與精神之果會是十分驚人的,甚至與另一些時代大異其趣:深邃、昂揚和特異,極度地哀傷或沉醉、陰郁或沉湎,逼人的絢麗和完美。
屈原和他的千古絕唱《楚辭》,便是這樣的經典范例。
《楚辭》是中國歷史上出現的第一部瑰麗的個人創造,其誕生的時空通常被稱之為“戰國”。屈原是這段歷史的深度參與者,既是一個被傷害者,又是最大的呈現者。他是這個時代的產兒,是滔滔洪流中的一滴。他的詩篇記錄了這樣一滴水怎樣飛濺,怎樣匯入激流,怎樣與時代巨涌一起激蕩而下。這些記錄就是他的動人的吟哦。《楚辭》同諸子百家的璀璨思想一起得到了保留,成為中國文明史上的“雙璧”。
后世人面對一部《楚辭》,發現它源于心靈的想象是如此奇異,驚心動魄,絢爛斑斕,以至于不可思議。無論是當時還是后來,在這樣的創造面前,都將無任何藝術能與之混淆,更無法取代。這是空前絕后的精神與藝術的奇跡,可以說含納了一個時代的全部隱秘和激情,這一切皆匯集于一個特殊的生命。
時代將人逼到了絕境,而絕境又驅使生命走向巔峰,無論是呼號尖叫,還是心底之吟,都會逼近前所未有的強度與高度。就精神和藝術而言,時代確有大小之分。詩人不得不在一個混亂而嚴酷的時代里奮力突圍,這是不可懈怠的。這種生命的沖決與奔突付出了慘烈代價,這一路燃燒滴落的燦燦金粒,足以為整個民族鑲上一道金邊。這正是詩人的光榮與宿命。
后來者期待獲得一個超脫的視角,以冷靜地評判鑒定過去的時代。他們想從中找出得與失、哀與幸,區別出個人和集體、潮流與水滴。這是一個大碰撞、大選擇和大融合的時代,人生如此,思想和藝術也是如此。在各種交織沖擊和糾纏搏斗之間,生命最終爆發出驚人的亮度,把歷史的長空照得通明。
瑰麗的南國
《詩經》誕生的時間稍早于《楚辭》,它形成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從這部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中,我們較少看到有關南國的描述。“詩三百”中只有少量詩篇屬于當時的長江流域,更多的則是北國的民歌,就一部藝術記錄的特質而言,它的氣息基本上是屬于北方的。我們或許想從中更多地窺見南國的瑰麗,以滿足對南國的某些神秘感的想象。實際上當時的南方,比如楚地,同樣有一場藝術繁密茂長,其溫潤的氣候、遼闊的土地,也蘊藏了激動人心的吟唱。這些歌聲的質地與干冷粗獷的北方大為不同。在今天看來,《詩經》所記錄的世界似乎呈現出一種相對封閉的北方性格;而楚地的歌唱也有強烈的地域性。在那個當時尚未知曉的南方地區,絢爛逼人的藝術之花在濃烈地盛開。當歷史的幕布被一點點拉開,人們終于聽到了楚地的聲音,看到了另一場生命的壯麗演繹。
在巫術盛行的沅湘兩岸,那些野性而粗悍的吟唱振聾發聵,充滿了旺盛蓬勃的生命力。戰國七雄之中楚國疆域最大,廣袤的土地上江河蜿蜒縱橫,高山連綿起伏,在丘壑水畔,在大自然的無數褶縫里,生活著一個剛烈勇武的族群。他們操著北人聽來有些費解的“南音”,以忘我的歌唱邀請神鬼共舞,傾訴衷腸,虔敬地仰望祈禱,渴盼在現實生活中能夠得到挽救和幫助。在與命運抗爭的過程中,他們借助于這種特殊的儀式,讓另一個世界的力量加入進來。后來,這似乎成為一種日常生活中十分依賴的方法,以追求神奇之力。
人鬼神三者相互交織的精神世界,是楚地所特有的一種共生狀態,這在《詩經》里并不多見。在楚人巫氣彌漫的吟唱中,我們感受的是另一種文化,它撲朔迷離,籠罩著濕潤渾茫的霧氣,閃爍在崇山峻嶺的陰影之下。由于南部地區陰濕溫熱,水汽淋漓,所以植物得到更多的灌溉和滋潤,往往有更加茂盛的生長,于是很快綠色攀爬蔓延,給大地蒙上了一層厚厚的植被。在這種自然環境中產生的歌吟,其風貌以至于內容當然會有不同。它陰氣濃盛,怪異而野性,一切皆與北方有異。水汽和陰郁,茂長和放肆,在這些方面可能要超過“詩三百”。總之,它們的審美特征差異顯著。
屈原是這些吟唱者當中最杰出的人物,也是一個集大成者。他吸取了楚地豐沃的滋養,伴隨了一場深沉而放縱的生長,最終走向了個人開闊而獨異的音域,成為一位輝映千秋的偉大歌者。
如同宿命一般,當年周王朝的采詩官沒有抵達南部,或者說涉足尚淺,也就把那片未曾采擷的幽深土地留給了后來,留待另一場驚心動魄的演示。打開《楚辭》,好比大幕開啟,人們馬上看到了一個耳目一新的國度,它遠不同于黃河流域,從現實物質到精神氣質,一切都呈現出迥然有異的面貌。他們的吟哦時常發出“兮”和“些”的聲音,那是不同于北方人的拖長的尾音,也許相當于“啊”和“嘿”。當一陣陣“兮”“些”之聲從濃濃的霧氣、從崇山峻嶺之間傳出的時候,會形成一種由遠到近的震蕩,一種聲音的誘惑。那些置身于大山深處的呼號者令我們好奇:他們有著怎樣的生活,怎樣的故事,怎樣的勞苦奔波,詠嘆竟如此渾厚悠長。
這些聲音伴隨著楚人的生活,化成動人的旋律一層層回蕩開來。開闊的音波將我們囊括籠罩,強大的磁性隨之將我們穿透擊中。我們迎著聲音走去,帶著一縷惶惑、迷離,懷著費解的心情一點點接近它。蒼蒼山水迎面而來,霧氣退向兩側。我們看到了具體的人,看到了一些清晰的神色。他們就是南國的生命,是黃河之南的長江淮河流域,是一個陌生的世界。楚地不同的精神和文化,需要北方人重新適應,就像需要慢慢化解他們的方言一樣。在這片土地上,人們要生存,也須奮力勞作,迎接和抗爭無測的命運。他們在追逐物質的同時,也會收獲一份精神的享受,獲取閑暇和愉悅,發出各種各樣的歌吟。
楚國民歌與巫術結合一體,顯現出另一種顏色,有特別的詭異和靈動。那些費解的詞語、地域的隱秘,還要等待我們去進一步破解。鐵馬秋風塞北,杏花春雨江南,大自然的神奇饋贈是如此豐富,在干燥寒冷的北國表現為肅穆,而到了南國卻是另一番風貌韻致。這里的生命接受大地的孕育,自然山水賦予他們獨有的靈性,讓其煥發出不可替代的創造力。
我們不禁設問:楚地之神從何而來?巫術從何而來?它們又如何接受人間的邀約?這一切實在難解。在這片霧氣繚繞的土地上,無數神奇都仿佛自然而然地發生,以至于成為生活的常態,化為人們精神的呼吸。在北方人看來,南方即便遠離了宮廷的肅穆莊嚴,也會尋覓到另一種強大的依賴: 接受靈異的襄助。這需要通過一場超越世俗權力的接洽儀式,從而進到另一個時空維度。在那個遙遠而又切近的神鬼世界里,有著不同的法則,正是通過對這種法則的尋找、求助以至于依傍,南國才獲得了信心。他們通過時而婉轉、時而狂放的嚎唱,讓一場場邀約成功,讓一種信心凸顯。就在這群聲呼號放歌之中,無可比擬的、令人震悚的威力一點點釋放出來,極大地強化了這片土地上生存的力量。正是在一種神秘外力的支援之下,南國才得以世代繁衍、發展和壯大。
詩與思的保育中心
人類常常有一個幻想,就是使杰出的思想和藝術能夠在最美好的社會環境中生長,而且自始至終得到小心翼翼的關愛和護佑。這是許多人夢寐以求的。多少人渴望這樣的盛世:人類享受普遍的寬容與恩慈,可以專注而深入地思索和創造,從而誕生出最為甜美的思想和藝術的果實。雖然這種一廂情愿的期待總是破滅,卻也仍舊綿綿不絕,因為這種盼念既合理又美好,絕沒有理由讓人們放棄。這當然是一種理想主義情結,而任何理想主義都有可能在現實中撞得粉碎:那樣的一個時代似乎是不存在的,“詩與思”的保育中心是不可能存在的。歷史上固然曾經出現了一些權高位重的廟堂人物,他們運用手中的權力去維護“詩與思”,甚至真的動手籌建一座座“保育中心”,如戰國時期名動四海的“稷下學宮”就是這樣的范例。有人要讓創造者獲得優良的物質條件,讓他們幸福安逸地運思和歌唱。那些擁有極大權力的人,愿意看到受其保護的人盡情發揮絢爛的才情,衣食無憂且不受傷害,表現出無窮無盡的創造力。當這個心愿稍稍得到實現時,這些得意的廟堂人物就有一種空前的欣喜和興奮,甚至還要親自加入“詩與思”的隊伍,同歌共舞。
只可惜這個過程往往極為短暫,生活漸漸還是要露出它殘酷的真容,接下去可能是更大的痛苦與跌宕。而在這之前,那些所謂的安逸的角落,“詩與思”已經在不同程度地發生蛻變。它們未經風雨,稚嫩而細弱,經受不住大自然的摧殘,隨時都可能凋落,變成一地殘枝敗葉。在廟堂權力者筑起的籬笆中,最終他們也很難隨心所欲地放縱自己,不能自由而野性地生長,無法枝壯葉茂、粗悍和強盛。說到這里,人們自然會想到一些典型的例子,除了齊國的稷下學宮,還有盛極一時的“養士”之風。齊國的孟嘗君、趙國的平原君、魏國的信陵君、楚國的春申君,都以“養士”著稱。這些諸侯權貴們邀集文人策士,筑壇興學,莫不嘆為觀止,可惜最終無一例外落個慘淡結局。權貴們或與吐放大言的學士們說不到一塊兒去,甚至引起了強烈的沖突;或者因為其他變故,總之好景不長,大家不得不作鳥獸散。
權力蔭庇之下的環境盡管平安溫煦,可是置身其中的人仍要警醒,吟哦的聲音還是要放低一點,最好不要驚動另一些人的安眠,不要打擾他們。這隱隱的擔心,事實證明是十分必要的。“詩與思”的稚綠小心翼翼,縮手縮腳,在沒有光色的午夜稍稍地伸展一片葉芽,又極可能在黎明之后的強光下很快枯萎。幸免者隨著時間的延續,會漸漸松弛下來,但仍然還會有意想不到的摧折,會發生劇烈的沖撞。他們這時要無所顧忌地呼號,激烈爭辯,撞擊之聲驚動四野。一些好奇的傾聽者匯集過來,這種圍觀一定會引起不安。無論是觀望者還是呼號者,終究還是要被驅散。整個過程提醒所有的人:王國需要安靜,尖音是不能持久的。
回望(春秋)戰國,人們不禁會想到孔子這位大思想家,他多么需要一個與其精神相匹配的王國。魯國不是這樣的地方,于是他離開了,去了周邊許多國家。那些地方大都和魯國差不多,所以孔子和他的弟子才有漫長的跋涉和顛沛流離,直到晚年都沒有找到一個理想之所。最終孔子還是回到了魯國。返回魯國后,行將老去的孔子開始修訂《詩》《樂》和《易》,這成為他晚年最有價值的勞作。死亡之前他做了一個夢,吟道:“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禮記·檀弓上》)孔子夢見屋梁要坍塌,泰山要崩毀,發出了最后的絕唱。
齊國曾是戰國時期的群雄之首,物質繁榮豐饒,藝術燦爛輝煌,擁有天下最好的戰車和宮殿。在這樣的鼎盛之期,齊國君王心有余裕,想起來要修建一座“詩與思”的“保育中心”,這就是流傳千古的學術和藝術的佳話,即創建“稷下學宮”的壯舉。當時天下第一流的思想者全都匯集稷下,在此雄辯滔滔,豪情萬丈。大學者享受第一等待遇:荀子曾擔任過學宮祭酒,配有豪車華屋,宮中學人也生活優渥,如孟子“受上大夫之祿”,擁有相當高的爵位和俸養。他們可以吐放大言,無所禁忌。狂言與志向,言過其實和虛幻想象,一切兼容并蓄。這是那個大時代一頁驕人的記載,是斑斕閃爍的歷史之章。可就是這座歷時一百五十多年、驚艷天下的著名學宮,其結局又是如何?整個故事仍舊是概念化和老套化的,那就是權力者與思想者的對立,是孟子離去,荀子沮喪。
原來廟堂權勢人物不過是葉公好龍,是一些玩文化者。是的,在他們眼里,文化是鳥雀一類的東西,也可以豢養和玩耍。他們沒有預料到的是,真正的詩與思一定是各具鋒芒的,會直抵生命的深處,與廟堂的轄制格格不入。那曾經令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韶樂》之美,也不過是禮儀所需,屬于廟堂之樂。
在廟堂所圈定的籬笆中,真正深刻的“詩與思”仍然不被兼容,無處藏身。讓我們的思緒從春秋戰國蕩開,進入所謂的盛唐,感受唐詩的際遇。那些最著名的詩人命運各異,但可以說其中最卓越者,仍被先后放逐到大唐廣闊的土地上,成為一群四處奔波的游蕩者。李白和杜甫,幾乎一生都在旅途之上,他們絕少安逸:“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李白《行路難》)“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就在這風雨摧殘、烈日暴曬之下,他們吟哦和記錄,留下了深刻的生命痕跡。和李杜類似的一些人物,他們或行進在逃亡的隊伍中,或輾轉在饑餓的大地上,在貧瘠艱困的生存中書寫個人的文字,幾乎沒有什么例外。那些有過廟堂生活經歷的人,偶爾也沉醉和幻想那一段日子,甚至有點戀戀不舍,但躋身宮殿與廳堂的生活,卻讓他們的心靈時常處于一種煎熬的狀態。流離而出,奔向遠方之后,他們才能大口呼吸,煥發出勇氣,獲得身與心的自由;面對美麗的大自然,那種放縱的想象和浪漫才顯得無比動人。即便是艱辛拼掙之下的呻吟,也那樣哀慟肺腑,其吟哦和歌唱都達到了一種極致。就“詩與思”的生長來看,一個人是這樣,一個群體也是這樣。我們真的找不到精神的保育中心,而且不可以存有這種幻想。
安逸、和平、豐厚的物質與社會環境,各種強有力的庇護,既不會憑空降臨,也不會天長日久。對于思想者和詩人來說這只是一份過分的奢望,最好不要期待;事實上只有擺脫了現實物欲的羈絆,才能夠讓心靈安頓下來,對置身的這個世界獲得相對客觀與超越的判斷。真正撼動心魄的“詩與思”往往誕生于艱苦困窘的境域中,這樣的世界固然令人痛苦不安,卻能催生出豐碩而深邃的精神成果。“國家不幸詩家幸”(趙翼《題遺山詩》),這似乎成為一個常理,寫在了復雜的歷史和經驗之中。那樣的時代讓我們避之唯恐不及,但那個時空中真的出現過另一道風景。也許這個結論太悲涼了,可它是真實的,是并不突兀的鑒定。
讓我們再次回到當時的楚國,看看大詩人屈原生活的環境。如果沒有楚懷王和頃襄王的昏庸與腐敗,沒有那些令人憎惡的宮廷爭斗,沒有兩次流放,沒有那些令詩人絕望的掙扎和奔波,又何來《離騷》,何來《天問》,何來《九章》和《九歌》?就在這人人恐懼的現實境遇中,出人預料地結出了最為迷人的“詩與思”的果實。作為后來者,我們心中矛盾重重,不無哀傷,究竟是希望還詩人一個安寧與欣悅的生存之境,還是于現實苦難中擷取瑰麗芬芳的藝術之果?我們無法回答,既怕傷害了我們的詩人,又實在不能割舍千古絕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