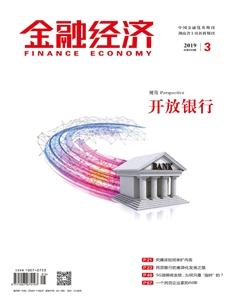開放銀行風起了
車寧

已有30余年行齡的胡總是一家上市銀行的“老前輩”,從辦公室打字員干起,一步步升遷至這家銀行科技部門總經理。可以說,商業銀行信息化進程的每一個歷史節點,對于胡總來說幾乎無役不予。面對打造開放銀行的歷史機遇和內外壓力,胡總和他的同事們依舊莫衷一是,幾許期待,幾許猶疑,真是“進亦憂、退亦憂”。
對于長期幕后工作的銀行科技人來說,幾乎是跑步走向舞臺中央。行內各項會議、各種戰略中“開放銀行”的口號固然不絕于耳;行外也與網絡大佬、實業巨頭在頻頻閃爍的鎂光燈下做出“合作賦能”的承諾。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我們也會看到:產品開發不順,是“不夠開放”;業務增長乏力,是“不夠開放”;就連制度流程、風險防控等等工作的現實困難也需要“不夠開放”來背鍋。
從上到下,從業務到科技,被脫媒、轉型、互金折磨許久的銀行人終于在開放銀行的概念中看到了自身向平臺經濟進化,成為生態整合新物種的希望,也同樣深知服務底層化、場景化、去中心化對自身獨立價值的消解。徘徊在十字路口,銀行人普遍想知道:什么是開放銀行的正確打開姿勢?
物有本末
開放銀行(Open Bank),或稱銀行開放式金融服務平臺,是銀行以用戶需求為導向,以場景服務為載體,以整合生態、搭建平臺為目標,以API/SDK(主要是API)為手段,在一系列網絡、信息、智能技術支撐下,通過內部整合和對外開放,使銀行服務更聚焦、更敏捷、更智能、更開放。
那么,這種開放銀行對之前的商業銀行經營模式究竟在哪些方面做出變革?
第一,變客戶服務為用戶服務。從客戶到用戶,一字之差,所折射的是跑馬圈地的增量發展到精耕細作的存量經營的深刻變遷。銀行與用戶需要在各種場景反復使用中締結更多維度、更深層次的連接,這就要求銀行更多地從用戶而非自身出發,將服務開放提供至用戶需求的各個場景。
第二,變銀行業務為場景服務。過去,不管是網點抑或程序,銀行服務都講究“領地意識”,千方百計把用戶拉到“我的”網點、“我的”程序,在增加用戶“皮鞋成本”之外,甚至內部業績和利潤分成也有齟齬。未來,銀行要更加主動走出去,潤物細無聲地貼身滿足用戶需求,以服務能力而非拉客能力作為真正的護城河,在滿足客戶不同場景需求的基礎上整合生態、建構平臺。
第三,變單打獨斗為平臺經濟。作為“中介”,銀行天然有“脫媒”的焦慮,看著網絡時代愈演愈烈的脫媒趨向,摸著自身還算豐厚的家底,從融資租賃到投資理財,從電商經營到內容生產,銀行在多個領域大干快上,盡管不能直接創造價值又極大消耗成本。抱團取暖、合作共贏的平臺經濟已是時勢使然,而其實現方式就著落在API及其小伙伴上。
第四,變App運營為API輸出。開放銀行的實質是銀行服務能力的開放,而其現階段的實現方式就是在服務標準化、產品化的基礎上,將其與應用場景聯通,在這一過程中銀行服務固然更加廣泛,但也更加底層。在當下和未來相當長時間內,App作為銀行服務主要渠道和“引進來”基本載體的地位不會發生改變,開放API與經營App并行不悖。形象地說,就是撤掉城墻,架構橋梁,不當紅花,甘為綠葉。這種謙卑的手段與高遠的目標間顯然存在著一種巨大的張力,而保證手段能服從和服務于目標的就是銀行基于前期網絡、信息和智能技術所鍛造的專業能力。
理解開放銀行的運行邏輯,自然不能缺少同業的比較分析。事實上,根據麻省理工學院Sloan商學院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將核心服務通過API方式分享給合作伙伴的能力定義了當下信息技術領先者和跟隨者的格局。落實到銀行業,包括BBVA銀行、花旗銀行、星展銀行等,它們在全球范圍內風起云涌的開放銀行發展中,展現出銀行開放的幅度、形式和進程,這既是先行者的成績,也是后來者的借鑒。
事有終始
理解開放平臺對于銀行的戰略意義,還需要有自身的獨立思考,需要結合自身情況并將其納入內外部的宏觀背景下考量。
從外部情況來看,打造開放銀行本質上是價值鏈的重構。在過去數年中,信息化、去產能(去杠桿也可以理解為金融領域的去產能)已經實質上重塑了整個國家經濟生態面貌。一方面,信息技術無論在商業場景抑或公共服務的廣度和深度應用上都有突破式進展,這不僅是連接方式的改變,更可以由量變到質變,產生了新的連接內容,銀行不僅是多了服務的承載方式,更是有了深度挖掘業務,開展精細經營的有力抓手;另一方面,去產能既促成了企業間在產業鏈上的錯位發展,也由此使得消費者的消費需求更趨理性和個性,這自然令銀行傳統上粗放的資金—資產經營能力難以為繼。可以說,是上述技術—產業—消費三位一體的顛覆式變革,而非互聯網金融在商業模式上的“小打小鬧”促成了銀行開放的壓力和動力。這次,不僅僅是服務渠道的微調,更是經營模式的改變,是對實體經濟價值體系調整的呼應和介入。
從內部情況來看,打造開放銀行是數字化工作的歷史延續。與“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相適應,銀行也一直在推進自身業務的現代化,而其一以貫之的呈現方式就是不斷升級的數字化轉型。從電算化到電子渠道分流,從IT建設到“大智云移”,從網上銀行到手機銀行,歷史清晰地說明打造開放銀行固然是外部形勢的要求,但更是自身數字化工作發展到新階段的自然延續。銀行前期的數字化工作成就,既是其開放銀行繼續推進的基礎,也造就了其發展差異的先天稟賦。其實,開放銀行本來就是一個“接著說”的故事,切不可為眼前的浮躁遮掩初心。
從更深層次解構,開放銀行口號的提出本來也是帶節奏的過程。一方面,在金融強監管的大氣候下,互聯網企業自營金融的努力遭到巨大挫折,需要重講故事以滿足資本期待和發掘新的業務增長領域,開放銀行、尤其是借道地方中小銀行是其當下的最優解。另一方面,銀行雖在經營和技術上多有改進,但管理體制中條塊分割的部門銀行痼疾仍然存在,與之相應,必須采用一個個口號引領的運動式手段,才能短期內凝聚共識、調動資源。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正確打開開放銀行的關鍵還需要看透伙伴目的,明確自身需求。
知所先后
開放銀行戰略推進的探討,邏輯、形勢是一個側面,真正實施起來還要具體分析銀行在這一生態格局搭建中的優缺點,評估項目啟動的各種制約要素。
首先,不宜妄自菲薄,不管是前期數字化工作的自然延續,還是對互金公司挑戰的被動應對,銀行在信息技術及與其適應的商業模式上已有了長足的進步,可謂是“信息企業中最懂金融,金融企業中最懂信息”。
還原銀行業務的本質,就是利用信息不對稱對風險進行定價,進而再促成資源跨時空的配置,銀行作為信用中介的前提就是作為信息中介。而與林林總總的互聯網企業相比,銀行又可以提供支付結算、存貸款等資金融通方面的服務,這是一種更深刻、更牢固的連接。更不用說,時下監管重回準入管理的舊途,國家許可的、能夠提供信用服務的信息中介舍我其誰。
不僅如此,站在互聯網沖擊的最前沿,銀行的信息化能力已不可同日而語。事實上,現在能夠代表金融來與互聯網、與實業談“開放”的恰恰只有銀行。更為重要的是,在金融產品中,銀行存貸付是一種更廣覆蓋、更常發生的業務,能夠常態、高頻且高質量地生產金融數據資源,這在被稱之為數據時代的當下和未來都具有重要戰略意義。
然而,開放銀行的紅地毯上并非滿是鮮花和掌聲,同樣還布滿著荊棘和坎坷。作為基礎的數字化工作固然成就巨大,但仍存在不少問題,特別是在開放銀行新的語境中,舊日傷疤更以扎眼的形式展現出來,這便是“聚合而非整合,站臺而非平臺”。
回顧銀行數字化工作乃至經營轉型工作歷史,不難發現其更多是增量創新而非存量改革,一方面未觸動部門銀行的利益格局和運行模式,另一方面作為創新成果,更多部門、更多利益被創造出來,這就反向強化了舊有體制力量。當開放銀行戰略實施之后,不難想見這又是牽頭部門的一場孤獨長跑,很難大破大立地真正實現以開放為導向的經營格局重整。
與之相應,還有銀行在產品化能力上的滯后。當服務能力以API的形式輸出,其前提首先是脫離本部門管理的藩籬,按照全行統一標準進行標準化改造。產品化工作的要點是在全行形成產品工廠,各部門根據業務需求再進行拼裝而非各起爐灶。這項工作粗看是技術層面,事實上則是風控能力、運營能力等等的綜合表現。
另外,打造開放銀行的外部風險也應該有清醒評估。首先是條件是否真正成熟,合作伙伴是否真正給力,前期備受熱捧的產業互聯網金融之所以高開低走,和外部基礎條件的乏力有很大關系,可謂殷鑒不遠。另外,開放銀行的另一面也是風險開放,在這里,合作伙伴或許提供了場景合作,但風控作為核心能力卻少有輸出,銀行自身面對輸入風險、共振效應以及內外部風險疊加形成新的暫時不可預測的風險是否已有應對策略,是否建立充分的緩釋和隔離機制,這些都需要提前予以考慮。
則近道矣
分析開放銀行的實施策略,我們不難發現:適應形勢、尋求發展是道,階段目標是術;開放銀行是道,API是術。
現實中,不同銀行的開放銀行戰略有不同的訴求,因而也具有不同的方式,比如大型銀行更強調建構生態,力圖以API為抓手玩轉平臺經濟,但可能遭遇曲高和寡、自說自話的窘境;中小銀行身段足夠靈活,但因議價能力相對較低而可能被邊緣化,反成為其它生態的衛星。不過從共性來看,筆者建議可從以下三點著手準備:
首先是筑基。前文已說,開放銀行終將是銀行綜合實力的全面比拼,而在獲客、運營、風控、科技等等能力的提升上,已有不少方法面世,本文也不再一一贅述。結合實際,從效率最大的角度看,值得關注的有兩點:一是要壓實牽頭部門職責,從內部看,人人負責就是人人免責;從外部看,開放合作也應由專業部門有序組織推進,做到規劃統一、需求統一、實施統一;二則要完善敏捷開發機制,不僅是總行層面,更是對分行層面,開放銀行的實現場景許多是本地化服務,對接當地運營商,需要在制度設計中予以重點考慮。
其次是借勢。對合作伙伴開放API是手段,服務企業及個人用戶才是目的本身。其實,提升服務質量本來就該是開放銀行的應有之義。一方面,需要在合作伙伴場景中,借助合作伙伴的能力、數據和分析工具更迅速、更準確、更人性化地滿足客戶金融需求;另一方面,還有部分客戶對金融需求不是迫切需要或僅作為從屬需要,反而更看重銀行作為連接器對各種資源的整合,考慮到金融脫媒的不可逆轉,中間收入的增收壓力,需要對此予以特別重視,這里可能成為銀行收入轉型的新突破口。
最后是賦能。在市場經營早期,開放數個乃至數十上百個API接口固然可以造成眼球效應,但真正的銀行平臺經濟的形成還有賴于對伙伴和用戶的賦能。幸運的是,相對于從零做起而又志在平臺的許多行業相比,銀行先天就具有廣泛的客戶基礎,豐富的服務渠道以及國家認可的低廉吸儲能力,這是其進行賦能的基礎。在此之上,銀行還可以輸出自身專業的金融產品設計能力和風險控制能力,在合理分潤的前提下形成用戶—平臺—產品—風控多位一體的生態格局。未來,在依法合規的基礎上,銀行甚至可以嘗試輸出和交換數據能力,這乃是開放平臺可持續運營的動力和最高價值。
互金企業暫時黯然退出舞臺中央,銀行反而由于對本業的堅持終于“守得云開見月明”。時下更現實的是,提高以銀行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體系的效率,而非重構一套體系。正是在此意義上,開放銀行也有了其值得期待的社會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