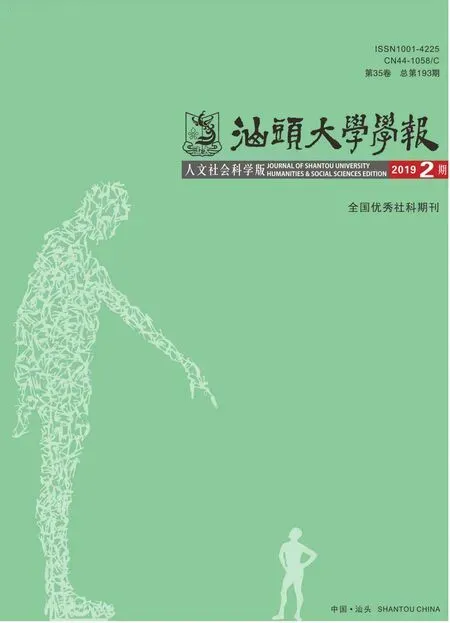民間信仰的“社會性”內涵與神圣關系建構
——基于粵東“夏底古村”的信仰關系研究
彭尚青,黃 敏,李 薇,趙 敏
(汕頭大學文學院,廣東 汕頭 515063)
關于中國民間信仰與地方社會關系的研究,既有宗教社會學關于“制度-彌散”的經典討論[1],又有民俗學、人類學“華北模式”與“華南模式”等不同視角[2]。從宏觀以至微觀,這些研究在豐富的經驗觀察與獨到的解釋性理解的基礎上,對中國民間信仰的儀式、組織等內容有著不同的方法與側重。然而,關于信仰關系或社會關系的討論似乎又通過不同地區的案例觀察,詮釋著中國民間信仰之于民間社會的相似意義。舊時,在粵東惠州鹽洲島,祭祀神靈的“集體儀式”[3]將圍繞廟宇的多個村莊整合為一個信仰集體;而如今,在河北省井陘縣青橫莊,社會秩序的變遷正推動著“社區公共儀式的重建”[4]。
可以說,中國民間信仰的儀式變遷無分南北,俱是顯而易見的,也很容易將之與社會秩序的變遷相聯系。那么,這種普遍性的儀式變遷引發以下思考:為何民間信仰在呈現儀式的時候,大多并不像制度宗教,所有儀式圍繞固守的教義而成規矩,而是因時而變、因事而變?儀式的改變是否意味著信仰核心的變遷?或者在變遷的過程中,居于民間信仰中心的是什么?民間信仰對神圣與世俗的模糊界限,會因此而明顯,又或更加糾葛不清?新的儀式出現是否意味著新的神圣關系的建構?社會秩序對于信仰儀式,是約束,是動力,或者更是其根本?
要厘清中國民間的社會秩序與民間信仰的神圣關系建構問題,可能需要大量的田野調研、民間信仰研究的經典案例、乃至不同學科的交流合作,方能步步為營,進而水落石出。當然,也最好以當下的、現實的實踐材料為基礎,而不是以過早假定的統一理論為依據,使得民間信仰的“儀式歸于信仰領域,秩序歸于社會領域”,貌合神離。在神圣關系建構的問題中,以民間信仰的社會實踐方式來看,各個廟宇的實踐邏輯應當是考察民間信仰的社會根基、民間信仰在變遷的社會環境中自我建構等問題的重要角度。因此,本文將以粵東夏底古村為例,通過對村落與廟宇的社會關系的梳理,來探討民間信仰的“社會性”內涵與神圣關系建構的問題。
一、玄天古廟:宗族文化的附庸抑或制度宗教的注腳
“夏底古村”(以下簡稱夏底村)位于汕頭市潮陽區關埠鎮,是一個有著700多年歷史的“黃氏”單姓古村落。據清光緒《潮陽縣志》記載,夏底黃氏一世祖黃經德:“字騰茂,莆田人也。宋時以鄉舉知程鄉縣事。性慈祥,多善政。后調潮陽縣,未蒞任,以病解組,因家于直浦都之夏林。”[5]夏林黃氏后分三支(堂后、埔上、夏底),其中夏底村為黃經德四子黃東春所建。其后,夏底村黃氏的家譜和祠堂碑記中,均以黃經德為夏底村一世祖,黃東春為二世祖,沿用至今。
如今,夏底村居住有黃氏族人8 500余人,村域面積約3.27平方公里。村落中現存有宗祠四座,另有佛教居士林、玄帝古廟、雙忠古廟等宗教信仰場所。圍繞這些宗祠與廟宇,夏底村村民每年要參加20多次相關的祭祀活動(見表1)。在這些祭祀活動中,有關“黃氏”祖先的崇拜儀式,其組織由宗族統領而最為統一,其儀式由族老主持而最為嚴肅。與這種嚴肅而統一的祖先崇拜儀式相區分,潮汕地區的民間信仰儀式規模崇尚宏大,形式也極其多彩。“賽大豬、賽大鵝、斗戲、斗彩棚等風俗”從前便有,現今又“加進了喜慶娛樂的內容”,娛神娛人,熱鬧非凡。[6]那么與嚴肅而統一的祖先崇拜相比,這種喧囂的慶典是否只是地方社會(以潮汕而論,更多是宗族組織)的文化附庸,其運行組織與社會結構之間也僅僅是“主客二元”(信仰組織-社會結構)的鑲嵌關系?

表1 夏底村民“拜老公”與“拜老爺”活動周年列表①注:深色底紋為民間信仰相關活動,其余為祖先崇拜活動。
二、以宗族組織為中心的“拜老公”與“拜老爺”信俗
潮汕地區圍繞宗族血緣關系而形成的祭祖傳統在當地被俗稱為“拜老公”。夏底黃氏的“拜老公”習俗以村民參與的規模和形式來看,可以略分為三類:其一是單戶家庭祭拜近親的家祭,其二是各房派祭拜各支的祖先,其三是整個夏底乃至夏林黃氏集中祭拜遠祖。第一種以家庭為單位的祭拜家祖規模最小,祭拜的通常是在五代以內逝世的家人,且僅以家為單位在各自家中或墓地進行。第二種各房派祭拜各支的祖先,在夏底主要是三房子孫在每年農歷二月十一祭拜三房七世祖黃無為、四房子孫在每年農歷二月初九祭拜四房十四世祖黃廷玉。①夏底創村之初,村內還住有黃氏以外的其他姓氏的居民,包括林、許、馬、蕭、謝、王等。而至現今,經過村內流傳的“十姓歸黃”等歷史進程,夏底村現已成為一單姓村落,為黃經德四子黃東春后裔。其中又以七世祖黃無為所傳的三房派、七世祖黃博叟所傳的四房派為多,長房派為次。現今夏底村人口則主要由三房與四房構成。第三種則是遠祖祭,由夏底村“老年人協會”(由在村中有威望的黃氏男性族老組成)組織夏底黃氏代表參與,祭拜的對象為夏底村較早期的祖先——太始祖、一世祖、二世祖、六世祖。參與祭拜的村民代表人數通常約50人,主要由夏底黃氏60歲以上的族老組成。
夏底村“老年人協會”除去統籌“拜老公”的祭祀祖先儀式外,同時還負責主持夏底村祭祀村落民間神祇的“拜老爺”慶典。這些民間信仰儀式本是脫胎自傳統的宗教信仰,只是因為潮汕地區廟堂眾多(據《潮汕廟堂》所述,潮汕地區現存的各種大小廟、祠、堂、宮,可能還有數以萬計之多,祀神已知逾170種。)[7],制度性宗教在潮汕社會的歷史進程中逐漸式微,又或者從未嚴格意義上掌控到地方廟宇,使得這些民間廟宇的儀式更多地成為地方村落的集體活動。黃挺先生認為,地方村落的祭祀儀式中,社祭與廟祭逐漸融合,形成“拜老爺”的傳統,“開始有了增進鄰里團結、加強鄉村治理的社會功能”。[8]
那么,潮汕地區村落的社祭與廟祭從前是否分明,又或者從一開始就是同一主體關于不同主題的活動?這一問題需要大量的歷史研究,此處暫且存疑,這里先將焦點放在現今的儀式活動中,觀察兩種祭祀活動是否今天已然合而為一,又或者于哪種程度上相合,在哪些方面仍舊是相分的。
三、以“玄天上帝廟”為中心的民間信仰
夏底村每年相對重要的“拜老爺”節日有三個,即年初的“神落天”(迎接諸神下凡),年底的“神上天”(答謝神恩,即“謝神”,送諸神上天述職),以及“大老爺(玄天上帝)生”(農歷三月初三誕辰之日,也被當地人稱為“佛誕日”)。除此之外,村民們在農歷每月的初一、十五都會祭拜伯公、天公等神祇。甚至在黃氏家庭的家祭日,這些神靈也會同時在家中享用香火。另外,玄帝古廟中還供奉有慈悲娘娘、太子爺、黃公(黃一龍)、八卦爺、王公(王鑾)、隴尾爺等,這些“老爺”的誕辰之日也會有部分村民前往玄帝古廟祭拜。
在夏底村,對諸神信仰的祭祀活動以“玄天上帝廟”(俗稱“玄天古廟”“老爺宮”)為核心,玄天上帝誕辰之日的慶典也最為隆重,方便回家的夏底黃氏村民都會在當天回家拜神。這類拜神活動也給黃氏族人提供了和朋友親人重聚、增進感情的機會。玄天上帝即真武帝,在夏底村被稱為“大老爺”,或稱“佛祖”。據《夏底廟宇史略》碑記記載:玄帝宮始建于明景泰年間(1456),由夏底黃氏六世祖黃應進出任江西泰和縣主簿后倡建。玄帝宮內正殿供奉玄天上帝……左祀是慈悲娘,右是花公媽,案幾上小亭閣里太子爺作為串巷保平安之神。清康熙三年(1633)遭遇“斥地遷界”②康熙元年(1662),清廷為斷絕大陸人民與鄭成功物資貿易,企圖以“斥地”來孤立鄭氏,并消滅之。正月二十九日發遷民告示,著令沿海居民,內遷50里。潮汕沿海地區許多宗祠、廟宇因之被毀。,夏底廟宇遭盜毀;康熙八年(1668)展復后,人民復荒,連年豐收,康熙十八年(1678-1959)廟宇重修。1968年經歷文化大革命,宮殿之杉木被拆做改革工具之用,僅存遺址。改革開放后,1992年由夏底老年人協會主辦重建,1993年8月落成。建成后,廟宇建筑初總面積282平方米,廟前廣場490平方米,耗資50多萬元。
玄帝古廟也是夏底村正月“上燈”的地點。正月初五到初七的晚上,夏底村的村民都會以家庭為單位,帶著燈籠和香,到玄帝古廟祭拜,在那里點上燈籠帶回家,同時點上香帶回家以插在家里的香爐。一般家中有幾個男性就帶幾個燈籠,“上燈”的起源也與父權社會息息相關,如今則更多是一個祈求平安的儀式。
夏底玄天古廟之左還有一雙忠古廟。只是對于村民而言,雖然它同由老年人協會管理、與玄天古廟同出一處且建筑相仿,但其重要性遠不如玄天古廟。雙忠公指的是張巡、許遠。據傳,唐至德二年(757),安祿山叛軍進攻戰略重鎮——睢陽。在兵力懸殊、糧草斷絕的情況下,時任河南節度副使的張巡與睢陽太守許遠依然堅守,為平息叛亂爭取了十個月的寶貴時間。雙忠公精忠報國,其傳奇事跡在潮汕地區代代相傳,久而久之也成為了夏底村民敬仰的對象。在每年正月的營老爺慶典中,雙忠公也作為“老爺”而游村受拜。陳春聲認為,雙忠公在潮汕地區的廣受祭祀,與地方宗族組織對地方勢力的影響不斷加強相輔相成。[9]
四、居士林的民間神靈與玄天古廟的佛光
除去民間信仰的玄天古廟、雙忠古廟,夏底村另有一處重要的制度性宗教信仰場所——佛教“居士林”(全稱為“汕頭市潮陽區佛教居士林”)。在夏底,玄天古廟、雙忠古廟等民間信仰可以說已經由宗族組織所主持,而居士林則由佛教信徒所管理。然而,居于同一村落的兩種信仰之間并非涇渭分明,而是彼此聯系緊密。現今的居士林內,仍留有一座民間信仰的“古樹娘娘廟”。而在玄天古廟的門楣上,別致地掛上了“佛光永照”的字樣,似乎這座衍生于道教的民間廟宇,由宗族文化的附庸,轉而成為制度宗教的注腳。
佛教自南朝劉宋大明年間(457-465)傳入潮汕[10],潮汕地區佛寺眾多,較為有名的有潮州開元寺、潮陽靈山寺和揭陽雙峰寺。夏底村附近還建有宋時的三峰寺、摩藏寺,明時的梅峰寺、經山古寺等。佛教在潮汕信眾廣泛,只是直至上世紀60年代,夏底村才有了第一個念佛場所——凈心精舍。在儀式與活動規模方面,夏底黃氏圍繞民間諸神與祖先的祭拜活動十分大型而豐富,其中“營老爺”“無為公祭日”等更是全村參與,并且家家供奉花公媽、灶君等。相較之下,佛教在村中稍顯沉寂,沒有以村落為單位的大型佛事活動,也非全村信奉。那為何佛光又照到了玄天古廟?這與居士林的最先合法化息息相關。
居士林的前身靜心精舍系夏底村遠近四鎮(關埠鎮、金玉鎮、灶浦鎮、西臚鎮)第一所由居士團體成立的自由學佛的場所,由夏底黃鴻金(法號:釋寬金)居士建立。1990年,時任廣東省佛教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的夏底村鄉賢黃禮烈為黃鴻金居士和當地禮佛之人合法信仰場所的考慮,向廣東省宗教局申請設立一個佛教“居士林”。該居士林于1995年主體建成,隨后成為關埠鎮文物保護單位。居士林的建立時,為尊重村民們的自然神信仰,其內的“古樹娘娘廟”仍舊保留,佛教信仰并沒有排斥民間信仰的古樹娘娘。
此外,居士林的居士們甚至會“入鄉隨俗”,在夏底正月營老爺活動時,參加相關的慶典儀式。并且,每年七月初七的民間信仰“送香船”儀式中,正月十五、二月初一佛教消災祈福的日子,居士林的居士們會被請到玄帝古廟誦經。正如前文所言,玄天大帝在這里被稱為一尊同受佛教居士所敬奉的“佛祖”。
玄天上帝究竟為道教神靈,抑或是佛教菩薩,本文并不打算辨析。需要注意的是,從《夏底廟宇史略》可見,明清時期,潮汕佛、道教開始受民間信仰神靈香火的沖擊而漸趨式微。此時,玄天上帝等被黃應進引入夏底村,是作為一個民間信仰的廟宇而存在,廟內同時祭祀的慈悲娘、花公媽、太子爺都是潮汕地區廣受香火的民間神靈。而在廟宇復建后,這所廟宇打上“佛光永照”的印記。1990年夏底村籌建居士林,1995年建成,成為關埠鎮文物保護單位。1992年玄天古廟與雙忠古廟重建,1993年玄天古廟建成。在時間以及關系的兩相契合之下,似乎民間廟宇鑲嵌“佛光永照”也是水到渠成之事。
五、民間信仰與祖先崇拜混合收支的香火
在夏底村,玄天古廟內的玄天上帝被稱為“佛祖”,廟內供奉“慈悲娘”(觀音化身),佛教居士林內供奉“古樹娘娘”。正月圍繞玄天古廟的“營老爺”活動由夏底村老年人協會主持,基本整個夏底黃氏村民都會動員起來,連居士們也會參加。宗族、民間信仰、佛教幾種在學理上區分明顯的信仰形式,在夏底村彼此交錯,其背后則是夏底村老年人協會的統籌運作。祖先崇拜、制度宗教與民間信仰相互接納,同時宗族權力主導及容納所有信仰形式的情況,更凸顯在夏底村有關祭祀祖先與神靈的香火錢的管理中。
夏底村玄帝古廟中設有“添油箱”,所獲得的香火錢由夏底村老年人協會管理,為老年人協會的主要收入。這筆錢除了用于玄天古廟的相關活動,還會用于夏底黃氏族祭,以及支持村中教育、文化建設工作等等。“拜老爺”“拜老公”活動是夏底最盛大的崇拜活動,在每年農歷年底和年初達到最盛。活動的舉行涉及到大額的金錢收支,為公平透明起見,老年人協會每年均在兩個時間節點公布收支明細,一次是在年底公布于玄帝古廟旁,另一次是在年初各種拜神、拜祖活動之后公布于列世祖祠。
2017年3月至2018年3月,夏底村老年人協會通過“佛祖生”(玄天上帝誕辰)、“迎神”(正月營老爺)等活動獲得29萬余香火錢,加上協會歷年積蓄,當前擁有共約71.5萬資金,其中38.68萬作為重修列世祖祠的啟動資金定期存寄。而這筆錢在支出方面,主要包含“宗族”“廟宇”“教育文化”三項。其中“宗族”包括各種拜祖活動的組織和準備、宗親村落的往來、祠堂的管理、族老的慰問款、救助金等;“廟宇”包括各種祭拜神明活動的組織和準備、廟宇的管理等;“教育文化”則包括資助黃武賢紀念館、夏底村小學教師慰問金等相關文化建設支出(見表2)。

表2 夏底村老年人協會2017年3月-2018年3月支出簡表①資料來源:夏底村老年人協會2017年年底收付公布表、夏底村老年人協會2018年1-3月收付公布表。
從民間信仰與祖先崇拜在儀式形式上的各自崇拜,到不同崇拜活動其實踐的主體或主持的團體皆由宗族組織主持,再至所有活動的香火收入兼顧村莊的“神圣”與“世俗”兩個領域,夏底村民間信仰組織的社會關系或信仰關系,已經不再僅僅是“主客二元”(信仰組織-社會結構)的關系。民間信仰的“社會性”內涵由此也應當更進一步,超出信仰領域對它的局限。本文以為有韋伯與涂爾干兩種不同的對宗教的社會學研究路徑。韋伯認為宗教作為一種社會事實,對它的研究更多是在形態上進行分析和解釋;而在涂爾干的分析中,宗教其本質便是“社會”。本文以涂爾干的理解來分析民間信仰的“社會性”內涵及其與神圣關系建構的問題。
六、民間信仰的“社會性”是外在特征還是內在本質
1899年,涂爾干出版了《宗教現象的界說》一書,書中第一次使用“宗教社會學”這一術語。之后,他在1912年出版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將宗教定義為“一種與既與眾不同、又不可冒犯的神圣事物有關的信仰與儀軌所組成的統一體系,這些信仰與儀軌將所有信奉它們的人結合在一個被稱為‘教會’的道德共同體之內。”[11]54但是,神圣事物是什么呢?涂爾干認為神圣的東西是被實體化、人格化了的團體力量,實際上就是社會本身。換句話來說,“宗教是社會的象征”。[11]552
與涂爾干不同,韋伯擱置了對于宗教本質的探討,將其宗教社會學的研究重心從本源問題轉向宗教實踐行為的研究。①韋伯在《宗教社會學》一書開篇即表現其對于“特殊的共同體行動(Gemein-schaftshandeln)類型的條件與效應”的重視。韋伯:《宗教社會學》,康樂、簡惠美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1頁。韋伯認為宗教行為是此世的、理性的,它所遵循的是經驗法則。韋伯認為原始人并不能像現代人一樣區分事物,他們的經驗所分辨的是尋常與超凡。在超凡的基礎上,原始經驗形成了精靈信仰(Geisterglaube),它是巫師克里斯瑪(Charisma)的來源。在此基礎上,超凡的“存在者”被象征化、人格化為部落的神祇。之后,祖先崇拜、家父長祭祀制、政治團體、地方神、一神信仰等被現代人熟知的宗教形式逐漸形成。基于這種歸因于原始人思維差異的起源論觀點,韋伯懸置了宗教信仰本質的討論。隨后在《宗教社會學》一書中,他將論述重點放到了先知、祭祀、宗教倫理、禁忌、教團等內容上。
涂爾干和韋伯對于宗教的研究代表了宗教社會學研究的兩種進路,前者將宗教等同于社會,追溯宗教起源和宗教神圣性的社會本質等問題,后者則是將宗教信仰視為一種行為方式,作為一個社會事實,分析其各個要素與社會之間的關系。這種將宗教作為社會事實的研究方式,影響了后來社會學功能論、沖突論、補償論等對宗教的研究。在帕森斯、莫頓等人的功能論中,宗教成為社會系統中具有整合功能的一部分。沖突論中,宗教組織被視為社會系統中的利益集團之一。補償論中,宗教成為致力于一般性補償的人類組織。[12]這些理論有一個統一的特征,即將宗教視為從社會關系中異化而出的文化實體,從而分析其對于社會整體的功用,同時也將宗教從社會這個整體的關系中獨立出來。
那么夏底村的民間信仰“異化”成為一個獨立的實體而單獨運行了嗎?從前文的實例來看,夏底村“玄天上帝”民間信仰的實踐主體實為村落的宗族組織,其管理一直由村里的老年人協會主持。甚至當佛教居士林進入夏底村,從老年人協會分裂出去之后,它仍然要受到這一宗族組織的影響。民間信仰組織與宗族組織在社會關系上的這種同一主體性特征,導致了夏底村祭祀祖先、祭祀神靈這兩種學理上涇渭分明的不同信仰,雖然在儀式上有著明顯分別,卻能夠在香火收入與分配上得到融合。宗族、廟宇、教育文化三個方面的支出,意味著這些來自夏底黃氏的香火錢最終又回到了黃氏家族的集體之中。夏底村的民間信仰有它異化出來的節日和儀式,然而從它的“社會性”內涵來看,似乎這種異化并未出離涂爾干所言“社會的象征”范圍。
七、民間信仰基于“人的法則”的神圣關系建構
貝格爾在《神圣的帷幕——宗教社會學理論之要素》一書中,將宗教的研究劃分為兩個部分,一個部分是宗教的體系、另一個部分則是歷史的宗教。貝格爾認為宗教體系的核心是其神正論的部分,它提供的看似有理結構(plausibility structure),使人的關系秩序化。他在書中指出:“宗教使人建立神圣宇宙的活動。換一種說法,宗教使用神圣的方式來進行秩序化的。”[13]因而,宗教信仰的神圣關系建構背后其實是“人的法則”在演繹。
夏底村的信仰關系如上所述,似乎恰好說明了“人的法則”在“神靈關系”上的延伸。潮汕地區一直以來是中國宗族文化保留相對完整的地方,這種強勢的文化傳統(實質上的社會秩序)亦影響到了玄天大帝信仰的重要儀式——“營老爺”活動。2017年夏底村正月初五“營老爺”,隊伍從玄帝古廟出發,沿村繞行一周,經過夏底村市場、夏底村小學、黃金福總兵府等村內重要公共場所,以“列世祖祠”為終點。正月初七,“營老爺”的隊伍又從“列世祖祠”出發,行至隔壁的埔上村大祠堂(熾昌堂,供奉夏底黃氏一世祖),最后才回到玄天古廟。
從廟宇的管理與香火錢的分配,到信仰儀式的實踐與象征,有著世俗社會秩序的全程參與及演繹,夏底村的實例折射出來的是一種基于社會關系建構起來的神圣秩序。這種建構模式,一如涂爾干對宗教信仰的社會性起源的論述,神圣關系的建構因之也圍繞“群體意識”“族群的生存目標”而形成,宗教信仰在根底上是一種對群體“關系的信仰”。人際關系決定了人神關系,社會秩序直接影響神圣關系的建構。[14]民間信仰的“社會性”內涵因而在此處并不僅僅是一種組織上的關系特征,也并非限于“主客二元”(信仰組織-社會結構)的鑲嵌關系,而是民間信仰的核心,能夠融于社會的根本。民間信仰因此建構出區別與制度性宗教的、跨越神圣與世俗的獨特神圣關系。在其表面看似世俗與功利,在其內部其實有著本身便具有神圣性、合法性的社會秩序與集體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