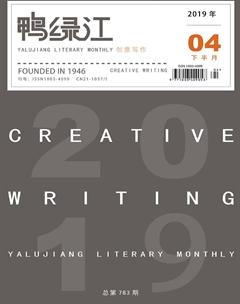刻墨冰川


冷冰川曾受邀為張愛玲的遺作繪制插圖,張愛玲身攜舊上海的華麗煙火終老洛杉磯,絢爛歸于冷寂。而冷冰川的作品亦是富麗而冷艷的,有時甚至顯得不近人情。張愛玲的文,冷冰川的畫,策劃者實是慧眼獨具。
刻墨是冷冰川獨創的技法,不知是先有美學的追求后有技法的創造,還是相反,總之,冷冰川的刻墨不僅是一種新的技術語言,也創造出一個屬于他自己的美學天地:慵懶裸身的女子,百葉窗斑駁的光影,凌亂擺放的書籍,身形偉岸的冷冰川居然如此細膩入骨的營構出少女的春意草草。大塊的黑白對比如琉璃般影射光暈,胴體的線條如水般游走,牽引著觀者的思緒。繁復的鋪排與優雅的勾勒,像寫意與工筆的融合,像繁復的交響樂弦管中一聲悠遠寂寥的古琴音……這份略帶頹廢的華麗,讓人聯想到古代春宮畫、洛可可、楚辭、宋人花卉。此樣情愫,當今已如雪泥鴻爪。
溫和而清逸,華麗而冷寂,冷冰川的藝術世界似乎與當下時代無關,他全身心徜徉在一個屬于自己的不辨東西,無古無今的美的世界里。正如深山里的花,正是拒絕,賦予它那份清雅秀逸;正是遠離喧囂,成全了那份淡淡的自足。
冷冰川的藝術是世界藝術史在中國文化中的際遇的典型個案,他既不是一個傳統主義畫家,又不是一個西方學院主義畫家,而且疏離于中國當代主義藝術運動之外,完全依賴其極為奇特的才能,在他溫厚的為人處世之間,將骨子里面異于同輩的對視覺感覺的特別敏感,與不動聲色的反叛結合起來。這種敏感是一種天賦,確實很少見,幸運的是他在人生少年時就用這個天賦進入了一個正確的行業,去做一種畫,這種畫就是刻墨。
他的刻畫慢慢形成了自己的風格,這種風格是他的獨創,也是歷史的機遇,也有傳統的淵源,或者稱為藝術史的淵源。因此,他自己將這種作品稱為“刻墨”,這個稱謂很準確。
每次看到他的畫都被他畫中的一種形象吸引,因為他刻畫得優美而妖嬈,有時過于“漂亮”,這種“漂亮”引發一種人和色相之間的幻想,是看者沉迷于感官的愉悅,猶如似是而非將到而未至之曖昧,因為這個色相并不是一味的情欲,而是經由刻畫出來的細致堅挺的細線鋪排而成的,以及這些細線之間被挑撥、殘壞和折磨而構成的一種圖像的關系形成的視覺盛宴,這種關系形成一種魅惑,只有在他的圖畫出現在眼前的時候,平面上才會制造出一個既是空間,又是圖畫,既是想象,又是夢幻的結果,但是盯著畫幅,形象又好像不在畫里面,離開畫面,形象雖在心頭,又無從憶起,大概他畫中的那種吸引人的形象發生在觀看當場時人與畫的相遇之中。線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有點像詩歌里的韻律,每一條線都在對形象的依附和超越之間,就像韻律在對物象的依附和超越之間,確實畫出了具體的對象,或美人花草,或風簾云霞,而超過線表達對象的,卻是出自他的特殊手段,被他表現的對象永遠在線的交織、排列、分叉、動蕩和糾纏中顯示出自我的形象,形象似乎時刻躲閃、隱藏到了線自身的組合和結構里面,盯住了看似乎又化在一根根線里面,不盯著看,形象從線里逃脫了出來,這種造型的特殊能力就是畫中的詩意,詩意超過了形象到達境界,卻或有或無地在面前閃現,而終于消失,而當面對畫面的時候,它又再度動蕩、流變開來,這樣一來一回就使得每一次的重新觀看都非常有趣,這種觀看就成為不間斷的觀看,對一幅圖畫的欣賞也就變成永無止境的欣賞。這就是我覺得冷冰川特殊的才能留給藝術的貢獻。
我們從事當代藝術研究時,首先是在考察一個人能對藝術到底做出什么樣的根本貢獻,以評論和看待一個藝術家的作品的價值。特殊才能營造的畫面效果這樣的問題經常被有意識地忽視和懸置,因為研究者警惕自己在面對一件美好的作品或者一個藝術家杰出的才能時,被藝術家的能力、情性所吸引從而出現了一種沉迷的狀態。所以我覺得這位溫厚的冷冰川卻在其冰冷的表面之下涌現出一種川流,而這種川流中間是一種巖漿,這種巖漿的溫度是在表面凝固不動中蘊含著爆發的力量,因此,當冷冰川把這種力量冷冷地用黑的底子和細膩的線條來表達的時候,這種力量就會變得尖刻而深沉,并且撥動人的心弦,讓人一觸則忘記戒備,任其誘惑驅使。也許他的線條就是一種從不同人的肉身里拈出來的“心弦”吧。
冷冰川的手法,除了其圖畫本身的超越于技藝的意蘊之外,他在技術上還有一種藝術史上的特殊貢獻,即刻墨。關于刻墨,它分為墨和刻兩個方面。
墨如何承載質和光,成為一種奇特的襯托?冷冰川的墨,上面有一種光,這種光本來是中國的墨的緣起,經過千年的等待和觀望以對應天地間精華的吸收,油煙和松煙燃燒的是在深山里成長的樹木,經過燃燒,收集煙塵,在寒砧上伴著風雨錘打千萬次,產生為一種特殊的顏色。墨之黑呈現出來不是煤黑,不是炭黑,不是油黑,而是一種輕盈而收斂的煙黑。似乎帶上了在山中煙霞具有的輕盈之光亮,將天地流動吸納于其中。每個藝術家用墨的原由不同,信念不同,墨的質量因而獲得不同的呈現。如同我們看到德加的畫,如果不是通過一種monotype單色油墨的技術,一種發自中世紀天主教圣像作坊的淵源,不可能出現那種偶然的、指間印痕的效果,德加用這種油墨的效果帶出了他作品的一種迷茫以及或有或無的松懈、松泛的感覺。由此不同的墨帶起的是一個文化的記憶。冷冰川的墨的記憶有綿遠流長的淵源,從墨寫在竹簡絹帛上的痕跡,一直到成為碑銘、成為歷史、成為永恒的象征,然后再進一步地被人錘拓點染下來,把這種文化的記憶反復地吟誦,反復地傳播,最后成為對人的本性和人的作為的一種超越,以及對生死的超脫。人意識到自我的生死必將到來,但只有用永恒才能把這種局限放大為無限的可能。所以在墨里面,在其幽暗的光里,實際上已形成了對無限的永恒的追索,而這種追索因為其幽暗而變得無窮無盡。
再說刻。在冷冰川的刻墨圖畫上,刻同樣是痕跡。這條痕跡在墨底上呈現為白色的紋路,遠紹中國過去的拓本,漢代的繪畫,其實就是浮雕和線刻的拓本,以至于人們忘卻了這些作品原來是門闕宮墻陵墓上的石頭雕塑,而將之認作墨底白線的圖畫,史稱漢畫。更進一步把漢畫當做漢代藝術的代表,所謂渾厚,所謂博大,本來并不是漢代藝術的特征,僅是因為石雕變為漢畫,一如刻墨,造成千古誤解,竟把墨與線的印象,錯作漢代原本。再到后來,碑刻大興,留下法帖,帶動中國藝術的核心審美價值流芳千古,曾經用來記錄歷史,也記錄了圖像文明的道路。近代以來,在西方文明的影響之下,中國藝術家,包括冷冰川本人,都是長期地在西方的繪畫方法的教育之下,把mimesis (模仿造型)當作是藝術的重要來源,這在任何一個經歷了新文化運動的中國現代的藝術家身上都不可能避免。但是,藝術家可以避免的是受其局限,在探索的過程中重新把一根線看成是一個獨一無二的存在,并且在線里面找到人的存在的意義的寄托,那么這根線就脫離了其形體和形態,具有了本身的力量,這種力量會發展為一種痕跡,這根痕跡正是一種“刻”,一刻,直達秦漢,深得漢畫之三昧。刻,因為其深刻,因為其摹刻,因為其刻琢的方法,線條遲疑和平滑,從而使得我們很多無盡的、永恒的追求變成個性的顯現,由此與碑刻傳統勾連。刻墨,墨上再刻,這條刻線又是什么呢?這條刻線實際上就是碑刻的來源。碑刻實際上是刻在墨底上出現的白線,這種白線把黑白顛倒,在顛倒過程中,這條線就有了一種執著的力量,它就遲疑起來,它就不再僅是一個線條,而是一條線條在耕作、在遲疑、在腐蝕的過程中產生的感覺。一旦這種感覺再被流動化,這種流動的遲疑就變成了冷冰川刻墨的品質。
刻墨作為一種方法由此而建立起來,我們看到了這一點,看到的就不僅僅是一個藝術家的杰出的動人的作品,而是一個對文化的創造和建設。
朱青生:北京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