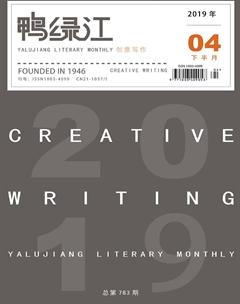我的朋友冷冰川
在這個寒冷的北京冬夜,忽然想到遠在西班牙的冷冰川,心里突地熱了一下。
冷冰川,不像他的名字:冷,冰,川,這個高大的南通人渾身洋溢著巨大的熱情和溫暖。第一次看到這個名字,以為是藝名,見到本尊后,跟想像中的奇崛精細完全是兩個樣子,這個雕刻出那么精美絕倫線條的人竟然這么一個“龐然大物也”,他看出我的驚訝,笑著說:“我就是冷冰川,我要有力量才能握住刻刀一刀一刀刻出來。”同時揮舞他那茁壯有力的手。
他的口音里有濃重的南通味,每個字極柔和地被重重吐出,他長的高如鐵塔,形如羅漢,聲音卻柔中帶剛,是一個具有反差和張力的人,這也是藝術家跟常人不一樣的地方吧,當然,他長成這么的反差,大概還是“天生麗質”吧。
怎么描述這個別具個性的藝術家呢?真有點難度,他在大俗大雅中獲得了最大限度地平衡,他是我見過的藝術家里最有平常心和藝術味的人。很多藝術家,凡是沾上藝術的邊,就變得不像人了,成了一個叫藝術家的物種。冰川卻是最懂得世道人心的藝術家,他跟人交往都是隨性隨心,不亢不卑,愛憎分明卻不張揚,察言觀色卻不道破,好惡善惡心中有數,到頭來往往順水推舟成人之美,所以,冰川能打通藝術家和其他各界的聯系,他是當代“我的朋友胡適之”,能成為冰川的朋友是天大的福氣。
我認識冰川是著名設計師張志偉老師介紹的,當時張老師給我設計一個詩集,說用冷冰川的畫很合適,我當時就小心翼翼地問:“我不認識冷冰川呀,藝術家都很各色,他會同意嗎?”張老師很有把握地說:“冰川,夠朋友,我跟他打個招呼,你們一見面就會成為好朋友的!”張志偉老師談論人向來謹慎,幾乎不用這么肯定的語氣,他這么來表達冰川,自然有特殊的感情和信任。等我見到冰川后,才徹底懂得一個人的好,他用心去對待每一個朋友,他的用心還呈現在他“左右逢源”,互不搭界的“冰友”成為朋友,百川到東海,他的胸懷如同太平洋了。他是出版界的寵兒,是藝術屆的詩人,是設計界的插畫師,他跟各界大咖都是好友,果然如志偉所言,我跟冰川一見如故,仿佛前世好友,不分彼此,沒有性別,這樣的境界需要錘煉幾世才能擁有呢?
冰川的藝術世界是黑白分明,刻墨即墨刻,用刻刀在被墨浸透的卡紙上刻出他的欲望與夢想,極單純又極繁復,極情色又極空無,極細膩又極曠遠,極寂寥又極歡愉。我難以想象冰川用冰冷的刻刀一刀刀刻在墨紙上的感覺,每一刀都是他雕刻世界的敘述視角,刀刀溫情,刀刀見性,刀刀直逼人心,驚心動魄,嘆為觀止。在夜色溫柔寂寥中,我仿佛看到一個入定的高僧摒棄人間煙火氣,氣定神閑地用刀刻著這個世界和理想世界的圖景,山川風月、女子與貓、妖冶花草、鮮活生命,下刀實在,刀外虛空,虛實相間,我經常陶醉于冰川的黑白世界,欲望如此茁壯純粹,春情蕩漾,愛欲純潔,生命力如此旺盛浩蕩,天地萬物順乎自然而美好,在某個瞬間,我甚至以為自己是刻刀下的那個寂寞無望的女子。冰川把冰冷有力的刀鋒化作對世界的柔情,手起刀落,梅花綻放,冷艷火熱,愛他就愛他的刀,那是冰川的大器和觸角,是他伸向黑暗的火炬,如他自己所說:“畫得黑,是為了亮”。
這個在黑白世界里尋找亮的男人喜歡穿黑色衣服,一絲不茍地認真,一絲不茍地幽默,他的幽默因為認真顯得冷峭,經常是我們笑完了,他才說出自己的看法,我們愣了一下又大笑起來,他思考慢,行動慢,說話也慢了半拍,這個慢讓冰川冷靜地觀察人,他的冷幽默里全是智慧和真摯,像孩子一樣充滿了童真,這也是藝術家跟常人不一樣的地方吧。冰川是嗜好真的,他說“情癡近乎真”,他對藝術是情癡,對藝術和朋友真摯,我們的一見如故大多是因為都是真人。
我的詩集出版后冰川開志偉玩笑,說志偉把他畫里下半身都截去了,那恰恰是他畫里最迷人的地方。現實中的冰川認真甚至拘謹,藝術中的冰川隨性隨意,一個單純的人在藝術中平衡了各種矛盾,他在藝術中完成了自己審美觀的統一:
我很相信創作時情色的麻煩氛圍。情色也始于虛無,我模仿它絕望的好處。
要畫的單純,單純到給人以復雜、深厚、豐富的“涉世”感覺。
純潔的表達恰恰是春藥的方式。純潔的完美,在于它沒有任何動機。
這是他的文字,他的文字跟他的刻刀一樣鋒芒畢露,字字見血,毫不含糊,他對藝術的理解接近于詩,是最高貴的質樸,單純的情色,帶來冰川藝術純粹的美,那是一個火與冰的世界,黑白極處見到無限可能的地帶。
高秀芹:北京大學中國詩歌研究院副院長,北大培文總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