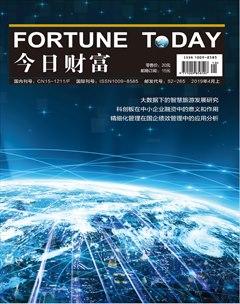中外合作辦學中外方涉稅問題研究與對策
趙娟娟
2003年《中外合作辦學條例》頒布以來,教育政策展現出空前的開放局面,嗅覺敏銳的外方教育機構蜂擁而至,中外合作辦學走上了繁榮之路。經歷了十多年的摸索與實踐,中外合作辦學已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道,并成為越來越多人的選擇。其在培養世界公民和全人教育上功不可沒,對國內的傳統教育也是很好的補充。但相關稅收問題還有很多值得探討的地方,本文以外方涉稅問題等為切入點,探討了如何規范和強化合作辦學的稅收征管。
近十多年來,全球教育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便是國際化,培養“世界公民”成為了大多數國際化學校的響亮口號。國內教育政策的空前的開放與民眾對世界文化的包容之心,推動了各國教育、多遠文化的交融和碰撞,因此中外合作辦學走上了繁榮之路。與此同時居民可支配收入逐步增加,中外合作辦學已被越來越多的人認知、認可,形成了龐大的教育消費市場,外方教育機構嘗到了甜頭,發現了中外合作辦學的巨大的利潤空間。本文結合作者自身工作經驗,分析合作辦學的組織形式、針對外方涉稅事項等各項細節,闡明了外方收入的征管的現狀,提出了存在的問題,及征管的依據和解決策略。
一 、中外合作辦學類型
中方和外方的教育機構可以再成立一個新的機構專門開展合作,這種類型就是中外合作辦學機構;也可以依托中方教育機構實施項目合作,此類型稱之為中外合作辦學項目。
(一)中外合作辦學機構
《中外合作辦學條例》第二章第九條規定:中外合作辦學機構應當具有獨立法人資格。因此其特點可以歸納為:1.獨立法人;2.由中外教育機構共同舉辦;3.在中國境內;4.主要招生對象是中國公民。中外合作雙方可以用資產作價作為辦學投入,獲得辦學許可證后,依法辦理注冊登記。例如筆者所在的城市,重慶巴蜀常春藤學校即為中外合作辦學機構。
(二)中外合作辦學項目
中外合作辦學項目則不具備獨立法人資格,也不單獨設立合作辦學的教育機構,而是在班級,課程等方面,合作開展合作,其舉辦形式非常靈活,通常是附屬在具備相關資質的中方教育機構中,例如成都七中嘉祥外國語學校,與國外教育機構簽訂合作協議,在獲得教育主管部門核準即可開設相應課程并招收學員。
二、涉稅收入現狀分析
(一)教育機構的收入
無論是中外合作辦學“機構”,還是“項目”,在合作模式和收入分配方面大同小異,通常由中方教育機構負責運營和招生,外方教育機構負責外籍師資和教學。由于《中外合作辦學條例》中第一章第三條明確規定, 中外合作辦學應為非盈利性質,因此中外合作辦學項目不得分配辦學結余。但并未限制外方直接向中方教育機構或學生收取費用作為回報。因此外方往往會設置名目繁多的項目進行收費,不僅費用高昂,且名目繁多例如:項目合作費、教材費、升學指導費、在線課程費、注冊費、學籍軟件使用費、外教費用、游學費等。費用收取途徑有兩種。
其一,通常情況下,費用由中方教育機構收取,外方教育機構根據協議約定按比例(或保底)收取項目合作費。學費往往是采取此種方式。
其二,由外方教育機構直接向學生收取,通常除學費外的衍生費用是采用此種方式。這種情況下,中方教育機構可能又會從外方教育機構中分配一定的份額,也可能全部由外方教育機構收取,中方教育機構不參與其中。
(二)外籍教師的薪酬收入
作為中外合作辦學的關鍵因素,外籍教師往往承擔外方教育機構履行合約的使命,外籍教師的相關支出同時也是教育機構成本支出的重要成本組成部分。主要包括:薪酬、保險費、差旅費、培訓費、房租費用等,其支付途徑分為三種情況。其一,由中方教育機構在境內支付。其二,由外方教育機構在境內,或境外支付,甚至目前比較流行的做法是境內境外組合支付。外籍教師的薪酬往往較高,而在中國境內使用的部分并不多,剩余部分匯回教師本國就會產生匯款成本和時間成本,而且很多外籍教師在其本國每月有固定的貸款需要歸還,因此目前比較流行的做法是由外籍教師自由選擇薪酬的境內外支付比例。例如中國境內支付40%,境外支付60%。其三,由中方教育機構和外方教育機構聯合支付。關于外籍教師的相關費用,在中外合作辦學的協議中一般會有明確規定,中外雙方分別根據協議約定承擔其責任部分。例如,外籍教師的薪酬、保險、境外簽證費用等由外方教育機構支付,房租費用、差旅費、境內簽證費用由境內教育機構承擔。
三、外方的涉稅問題與對策
(一)免稅與非免稅收入難以界定
根據財稅[2014]13號文《關于非營利組織免稅資格認定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的規定,學歷教育享受免稅政策。雖然中方教育機構與外方簽訂和合作協議,共同合作辦學,但其收入卻又有本質區別。開展學歷教育的中方教育機構僅是聯合了外方教育機構,其本身不對結余進行分配,故收入符合免稅政策。但深入研究中外合作辦學其稅收實質,不難發現,外方教育機構為我國非居民納稅人,且收取的費用利潤巨大,是以營利為目的商業活動,因此不可享受免稅政策。
所以無論合作辦學收入采取何種名目,何種途徑收取,均可按其最終取得方一分為二處理:一是中方教育機構提供學歷教育取得的收入符合免稅政策;二是外方教育機構取得的部分,不符合免稅政策。
(二)納稅義務人難以確定
如上所述,既然中方教育機構收入部分免稅,外方教育機構收入部分不免稅,那是否應就各自收入分別申報納稅?財稅[2016}36號文第一章第六條對增值稅的納稅義務人做出了明確規定, 境外機構在境內發生增值稅應稅行為,且在境內未設有經營機構的,以購買方為增值稅扣繳義務人。再來從企業所得稅的角度分析,《企業所得稅法》第三十七條規定對非居民企業取得的應稅所得,實行源泉扣繳,以支付人為扣繳義務人。以中方教育機構收取學費,再向外方教育機構支付項目合作費為例,中方教育機構才是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的扣繳義務人。
根據筆者的實際經驗,很多外方教育機構在簽署合同時,列明“在中國境內發生的所有稅費由中方承擔”。而中方合作者往往認為自己符合免稅政策,忽略此條款實際代表的是應該代扣代繳的外方教育機構的相關稅費。
(三)外籍教師薪酬是否免稅難以界定
在中國境內教育機構任教的外籍教師,存在以下兩種情況。
1.一是外籍教師其籍所在國家,與我國簽訂了稅收協定,且外籍教師本人符合免稅條件,這些外籍教師取得的教學收入在稅務機關批準本案后免征個人所得稅。以美國為例:《中美關于對所得避免雙重征稅和防止偷漏稅的協定》第19條規定,任何個人是、或者在直接前往締約國一方之前曾是締約國另一方居民,主要由于在該締約國一方的大學、學院、學校或其他公認的教育機構和科研機構從事教學、講學或研究的目的暫時停留在該締約國一方,其停留時間累計不超過三年的,該締約國一方應對其由于教學、講學或研究取得的報酬,免予征稅。
2.二是外籍教師國籍所在國家,未與我國簽訂了稅收協定,或是雖有稅收協定,外籍教師本人不具備免稅條件,這些外籍教師取得的教學收入應根據稅法有關居民納稅人與非居民納稅人的判定標準,確定其納稅義務范圍。
根據筆者的實務經驗,如果外籍教師來自協定國,且與中方教育機構簽訂勞動合同,由中方教育機構支付薪酬,同時具備其本國稅務機關開具的完稅證明則符合個人所得稅免稅政策。但如果與外方教育機構簽訂勞動合同,則不能享受此項免稅政策。
對于不能享受稅收雙邊協定免稅政策的外籍教師,又存在一些免予征收個人所得稅的抵扣項目。此時又要對外籍教師的居民和非居民屬性進行區分。
根據財稅〔2018〕164號文第七條規定 目前外籍居民納稅個人可以同中國居民一樣,選擇享受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也可以選擇按照享受住房補貼、伙食補貼、洗衣費、搬遷費、出差補貼、探親費,以及外籍個人發生的語言訓練費、子女教育費等津補貼免稅優惠政策。而非居民納稅個人只能選擇后者。
(四)稅務機關信息有所局限
對于外方教育機構直接收取,中方教育機構不參與其中的收費項目,稅務機關沒有有有效的信息獲取途徑,導致這部分稅源很容易流失。例如游學費、在線課程費等衍生收費項目,往往不是全體學生的必須選擇,其具有單筆金額小,費集體行為等特點,總金額不容小覷,而且外方教育機構通常會要求學生直接匯款至境外的外方教育機構。款項出境涉及外匯問題,目前國家的外匯管制也日趨嚴格,企業在向境外付匯時,需要向銀行提交完稅證明、對外支付備案、合同備案等證明材料,似乎能夠防止出境稅款的流失,但卻沒有對個人的外匯要求同等的備案材料。個人對境外教育公司的小額匯款并不需要提供完稅材料,尤其是對境外學校的匯款,即使金額較大也不需要完稅證明。一些狡猾的境外教育公司還會與境外的學校進行合作,由境外學校向學生收款后再分配部分給境外教育公司。如此一來,這些外方直接收取的費用就逃避了管制。對此,稅務機關、外管局、銀行等部門應加強溝通,在加強企業外匯管制的同時,也要著眼于個人外匯政策的完善。無論是公司還是個人向境外付匯時,都需向銀行提交盡量完備的材料,諸如:完稅證明或免稅文件、稅務審核過的合同備案材料等。目前稅務局已在推行電子稅務局,涉稅事物已有很多可以直接在電子稅務局上完成,那么外匯的合同審核完全可以通過電子稅務局提交,并完成審核。稅務局亦應積極開發手機端的電子稅務局APP,并由專人在后臺對此事項進行在線審核,那么付款人即使事先不知道合同需通過稅務局審核,到達銀行后,也可以在銀行工作人員的指導下,通過手機APP實現材料備案,審核結果立等可取。這樣一來,一方面并不會加重付款人的負擔,另一方面稅務機關就由稅后監督變為稅前監督,對外方教育機構直接收取的付匯收入積極的監控起來。(作者單位:重慶諾林教育信息咨詢服務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