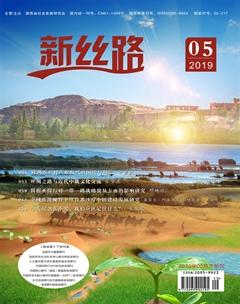關于手機應用侵犯著作權時手機應用平臺運營商法律責任的分析
摘 要: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手機應用軟件越來越多,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和應用發生了日新月異的變化,隨之而來的手機應用侵權現象日趨嚴重,法院受理的侵權糾紛案也越來越多。因此,對手機應用軟件和互聯網內容服務來說,建立嚴格的規范機制和科學的監管制度,明確相應的法律責任就顯得尤為重要。
關鍵詞:手機應用;運營商;法律責任
一、自營手機APP侵權時手機應用平臺運營商的法律責任
《著作權法》第四十八條規定:“有下列侵權行為的,應當根據情況,承擔停止侵害、消除影響、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等民事責任……:未經著作權人許可,復制、發行、表演、放映、廣播、匯編、通過信息網絡向公眾傳播其作品的,本法另有規定的除外……”。若APP是手機應用平臺運營商(以下簡稱運營商)自行開發(通常情況為由手機應用平臺運營商聘用的程序員所開發),后放在應用平臺上,其開發的軟件侵犯了他人的著作權,則運營商構成直接侵犯網絡信息傳播權,承擔直接侵權責任。
注意在無法確認侵權APP的直接開發者的情況下,法院傾向于推定侵權作品是運營商自行開發并上傳其手機應用平臺的,此時運營商也構成直接侵權。
二、第三方開發者開發的APP侵權時運營商的法律責任
1.若運營商直接參與APP利潤分配,則運營商承擔共同侵權責任
《關于審理侵害信息網絡傳播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信息網絡傳播權司法解釋》”)第四條規定:“有證據證明網絡服務提供者與他人以分工合作等方式共同提供作品、表演、錄音錄像制品,構成共同侵權行為的,人民法院應當判令其承擔連帶責任。”第十一條規定:“網絡服務提供者從網絡用戶提供的作品、表演、錄音錄像制品中直接獲得經濟利益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其對該網絡用戶侵害信息網絡傳播權的行為負有較高的注意義務。”
在(2015)民申字第2198號民事裁定書中最高人民法院認為:蘋果公司通過Appstore獲取利益和承擔義務應具有對等性和一致性,由于蘋果公司在與開發商的協議中,約定了固定比例的收益,因此蘋果公司負有較高的注意義務。蘋果公司在可以明顯感知涉案應用程序為應用程序開發商未經許可提供的情況下,仍未采取合理措施,故可以認定蘋果公司并未盡到上述注意義務,具有主觀過錯,其涉案行為構成侵權。
據此,若運營商直接參與了APP利潤分配,意味著其承擔嚴格的審查義務,也意味著運營商與開發者之間簽訂有相關利潤分配協議。一方面,運營商未盡到嚴格審查的義務。另一方面,運營商與開發者之間簽訂有相關利潤分配協議可能被作為以分工合作等方式共同提供侵權APP的證據,可以認為平臺運營商對侵權人提供了實質性的幫助,所以負共同侵權責任。再者,《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第二十二條規定的“避風港原則”要求網絡服務提供者未從直接獲得經濟利益,因此,直接獲得經濟利益的運營商不能適用“避風港原則”通過刪除、斷開連接避免承擔侵權責任。本所認為若運營商直接參與了APP的利潤分配,那么運營商將承擔與開發者的共同侵權責任。
2.若運營商雖未直接參與APP利潤分配,但明知或應知APP侵權,則運營商承擔共同侵權責任
《信息網絡傳播權司法解釋》第八條第一款規定:“人民法院應當根據網絡服務提供者的過錯,確定其是否承擔教唆、幫助侵權責任。網絡服務提供者的過錯包括對于網絡用戶侵害信息網絡傳播權行為的明知或者應知。”對于“應知”的判斷,該司法解釋第九條規定了認定網絡服務提供者是否構成應知的要素包括:網絡服務提供者提供服務的性質、方式及其引發侵權的可能性大小,應當具備的管理信息的能力,網絡服務提供者是否積極采取了預防侵權的合理措施等等。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在(2016)京民終247號北京中青文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等與侵害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糾紛二審民事判決書中認為:運營商百度公司未分享侵權APP利潤,因此適用一般理性人的標準。百度公司只要施以普通的注意義務,即可發現涉案APP取得授權的可能性極低,具有相當大的侵權可能性,但卻沒有盡到合理的注意義務,也沒有建立起足夠有效的著作權保護機制,對于涉案侵權行為具有應知的過錯,其行為構成幫助侵權。
著作權人如果能夠證明運營商雖未參與APP利潤分配但沒有盡到合理的注意義務、沒有采取積極預防侵權的合理措施、APP侵權可能性極大等要素,則能夠證明運營商具有明知或者應知的過錯。若運營商雖未直接參與APP利潤分配,但具有明知或應的過錯,則運營商與開發者承擔共同侵權的法律責任。
3.若運營商未直接參與APP利潤分配,且不構成明知或應知APP侵權,則適用“通知-移除”規則
若運營商未直接參與APP利潤分配且不構成明知或應知APP侵權,在司法實踐中適用“通知-移除”規則。《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第二十二條對“通知-移除”規則做了詳細規定:“網絡服務提供者為服務對象提供信息存儲空間,供服務對象通過信息網絡向公眾提供作品、表演、錄音錄像制品,并具備下列條件的,不承擔賠償責任:明確標示該信息存儲空間是為服務對象所提供,并公開網絡服務提供者的名稱、聯系人、網絡地址;未改變服務對象所提供的作品、表演、錄音錄像制品;不知道也沒有合理的理由應當知道服務對象提供的作品、表演、錄音錄像制品侵權;未從服務對象提供作品、表演、錄音錄像制品中直接獲得經濟利益;在接到權利人的通知書后,根據本條例規定刪除權利人認為侵權的作品、表演、錄音錄像制品。”此外,《侵權責任法》第三十六條也做出相應規定:“…網絡用戶利用網絡服務實施侵權行為的,被侵權人有權通知網絡服務提供者采取刪除、屏蔽、斷開鏈接等必要措施。網絡服務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時采取必要措施的,對損害的擴大部分與該網絡用戶承擔連帶責任。網絡服務提供者知道網絡用戶利用其網絡服務侵害他人民事權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與該網絡用戶承擔連帶責任”。
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審理黃曉陽與北京京東叁佰陸拾度電子商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京東公司”)著作權權屬、侵權糾紛案((2014)三中民終字第11615號)適用了以上“通知-移除”規則。法院認為被告京東公司僅提供信息存儲空間和技術服務、未通過涉案侵權手機應用軟件的傳播直接獲得經濟利益、原告發送的通知京東公司并未實際收到不算有效通知,判定京東公司符合網絡服務提供者免于承擔賠償責任的條件。
綜上所述,未從開發者提供的APP中直接獲得經濟利益的運營商,不知道也沒有合理的理由應當知道APP侵權,只要其收到侵權通知后及時刪除相關APP,則不承擔侵權責任。
三、手機應用平臺轉載第三方APP開發者侵權APP下載鏈接時運營商的法律責任
1.若手機應用平臺轉載的是普通鏈接,則運營商不承擔侵權責任
網絡連接分為普通鏈接和深度鏈接,二者有以下區別:第一,技術屬性上,普通鏈接的對象是被鏈網站的主頁,點擊跳轉后顯示的仍是其完整頁面,本身并沒有經過特殊的技術處理,深度鏈接不發生頁面跳轉,可在設鏈網站上直接呈現被鏈內容或可以通過設鏈網站直接下載相關文件;第二,鏈接目上,普通鏈接出于中立地位,目的在于為用戶在海量信息中快速尋找相關信息,提供搜索結果或者是鏈接網址,深度鏈接是以直接提供被鏈網站的作品為目的,并形成了設鏈網站內容的深層次對應關系;第三,控制管理能力上,普通鏈接只是實施一個直接跳轉的行為,其對被鏈網站的域名無控制力,深度鏈接將第三方網站作品通過鏈接方式變成自己的一部分,具有較強控制能力。
若手機應用平臺轉載的是普通鏈接,運營商通常不承擔侵權責任。依據的是《信息網絡傳播權司法解釋》第四條“…網絡服務提供者能夠證明其僅提供自動接入、自動傳輸、信息存儲空間、搜索、鏈接、文件分享技術等網絡服務,主張其不構成共同侵權行為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以及第六條“原告有初步證據證明網絡服務提供者提供了相關作品、表演、錄音錄像制品,但網絡服務提供者能夠證明其僅提供網絡服務,且無過錯的,人民法院不應認定為構成侵權。”此外,可以參考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網絡環境下著作權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一)》第三條“網絡服務提供者為服務對象提供自動接入、自動傳輸、信息存儲空間、搜索、鏈接、P2P(點對點)等服務的,屬于為服務對象傳播的信息在網絡上傳播提供技術、設施支持的幫助行為,不構成直接的信息網絡傳播行為。”
由此可見,若運營商轉載的是普通鏈接,且無過錯的,不構成直接的信息網絡傳播行為,也不構成侵犯信息網絡傳播權。
2.若手機應用平臺轉載的是深度鏈接,但不構成明知或應知APP侵權,則適用“通知-移除”規則
深度鏈接指不發生頁面跳轉,在設鏈網站上直接呈現被鏈內容或可以通過設鏈網站直接下載相關文件的技術手段。深度鏈接在法律上構成信息網絡傳播行為。依據的是《信息網絡傳播權司法解釋》第三條規定:“……通過上傳到網絡服務器、設置共享文件或者利用文件分享軟件等方式,將作品、表演、錄音錄像制品置于信息網絡中,使公眾能夠在個人選定的時間和地點以下載、瀏覽或者其他方式獲得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其實施了前款規定的提供行為。”同時,參考北京市高院《關于審理涉及網絡環境下著作權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一)》第二條“……將作品、表演、錄音錄像制品上傳至或以其他方式置于向公眾開放的網絡服務器中,使作品、表演、錄音錄像制品處于公眾可以在選定的時間和地點下載、瀏覽或以其他方式在線獲得,即構成信息網絡傳播行為,無需當事人舉證證明實際進行過下載、瀏覽或以其他方式在線獲得的事實。”據此,運營商轉載了深度鏈接,使APP處于公眾可以在選定的時間和地點下載、瀏覽或以其他方式在線獲得,構成信息網絡傳播行為。
司法實踐中,若手機應用平臺轉載的是深度鏈接,但不構成明知或應知APP侵權,適用《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第二十二條“通知-移除”規則,以及《侵權責任法》第三十六條。運營商在收到被侵權人通知后,及時采取刪除、屏蔽、斷開鏈接等必要措施,就可以避免承擔侵犯信息網絡傳播權的法律責任。
3.若手機應用平臺轉載的是深度鏈接,且明知或應知APP侵權,則運營商承擔共同侵權責任
如上文所述,轉載可獲得侵權APP深度鏈接的行為和將侵權APP在應用平臺上上線的行為一樣,構成信息網絡傳播行為。依據《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第二十三條“網絡服務提供者為服務對象提供搜索或者鏈接服務……但是,明知或者應知所鏈接的作品、表演、錄音錄像制品侵權的,應當承擔共同侵權責任”,加之《信息網絡傳播權司法解釋》第八條、第九條規定,若手機應用平臺轉載的是深度鏈接,且明知或應知APP侵權,則運營商與開發者承擔共同侵權責任。“明知或應知”的標準依該司法解釋第九條和上文的分析,此處不再贅述。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在(2004)高民終字第1303號民事判決書中認定:世紀悅博公司對收集到的有關信息進行了選擇、編排、整理;選定被鏈接的網站和下載源,設定下載的步驟、方法,以逐層遞進的方式引導用戶下載;鎖定被鏈接的網站及其錄音制品,限定了下載的地址,從而在自己的網站與被鏈接網站的具體的錄音制品之間建立起了深度鏈接的對應關系。因此,世紀悅博公司應對所鏈接的錄音制品的合法性負有注意義務,但世紀悅博公司放任自己的行為,參與、幫助了被鏈接網站實施侵權行為,具備應知作品侵權的主觀過錯,判決維持世紀悅博公司構成共同侵權的一審判決。
綜上所述,若手機應用平臺轉載的是深度鏈接,且明知或應知APP侵權,則運營商應與第三方開發者承擔共同侵權責任。
參考文獻:
[1]李五平.手機App應用平臺下的著作權保護[J].法制博覽,2014(11)
[2]王博今、孟妍.手機APP著作權保護及侵權救濟[J].楚天法治,2016(11)
[3]王蓮峰.論移動互聯網App標識的屬性及商標侵權[J].上海財經大學學報,2016(1)
[4]許佳航.案例分析:蘋果公司對于Appstore所提供的應用程序侵犯版權的法律責任[J].法制與社會,2017(22)
[5]李穎.移動互聯網APP應用的發展與著作權保護[J].電子知識產權,2014(12)
作者簡介:
馮季英(1972--)女,湖南瀏陽人,碩士,湖南司法警官職業學院司法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