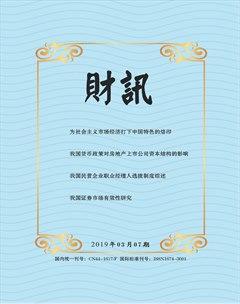中國上市公司股權激勵對公司創新活動影響評述
摘 要:自2005年,我國頒布《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試行)》后,越來越多的上市公司利用股權激勵解決委托代理問題。股權激勵對于公司財務績效的影響日益豐富,但關于股權激勵對公司創新活動的影響,如創新投入、創新產出方面的研究還較少,因此本文希望通過梳理有關股權激勵對公司創新活動影響的文獻,為更多學者在該研究方面提供一定的文獻基礎。
關鍵詞:股權激勵;創新投入;創新產出
一、引言
股權激勵起源于美國,主要是為了解決20世紀50年代出現的委托代理問題。該問題由Jensen(1976)提出,即由于公司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可能導致的公司經營者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問題。我國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也引入了股權激勵以解決委托代理問題。2005年,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證監會)頒布《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試行)》,從此關于我國上市公司實行股權激勵計劃的現象開始涌現;按照中國證監會做出的規定,即“股權激勵是上市公司以本公司股票為標的,對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及其他關鍵員工進行的長期性激勵”。
股權激勵對公司財務績效的研究已十分豐富,萬華林(2018)對兩者關系做出了詳細評述并提出了基于關系型交易理論對股權激勵問題的研究方向。目前股權激勵對公司創新活動的研究還較少,本文主要梳理我國股權激勵對公司創新活動影響的相關文獻,以期對該方面的研究能進一步加以展望。
我國學者關于股權激勵對企業創新活動的影響主要有正相關、非線性相關、負相關和不相關這四方面的內容,而對于創新活動的研究也逐漸從創新投入到創新產出這一階段,激勵對象也從高管擴展到了更為廣泛的核心員工。
二、正向影響關系
劉運國、劉雯(2007)以2001—2004年披露R&D支出的454個上市公司為樣本,得出高管股權報酬有利于高管增加 R&D 投入的研究結論。唐清泉(2009)等構造股權激勵、研發投入與企業可持續發展之間的理論框架,利用2002-2005年披露研發費用的上市公司進行實證研究,發現高新技術企業的研發活動受經營者持股比例的影響更大。孫菁(2016)等人選取滬深兩市上市公司相關數據,采用傾向得分匹配法,以是否實施股權激勵為啞變量,發現企業實施股權激勵能有效促進其研發投入。
姜英兵和于雅萍(2017)進一步將股權激勵對象擴展到核心員工,發現對核心員工進行股權激勵能夠有效增加企業創新產出數量并提高創新產出質量。田軒和孟清揚(2018)選取我國2001—2016年的上市企業數據進行研究,采用傾向得分匹配法和雙重差分方法,發現股權激勵計劃對企業創新投入和產出都有顯著的促進作用。
三、區間影響關系
冉茂盛(2008)等通過建立股權激勵和R&D支出的契約模型,基于委托代理理論求解得出了管理層最優股權激勵比例和最優R&D投資量的參數表達式,發現兩者間存在倒U型關系。湯業國(2012)等運用后股權分置時代,即2007—2010年中國高科技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數據,研究得出中小上市公司股權激勵與技術創新投入之間存在倒U型曲線關系。徐寧(2013)運用相同時間段數據,發現高管股權激勵力度與R&D投入之間存在相同關系。
四、負面影響
趙洪江(2008)等選取2007年上半年深滬證券交易所上市企業披露的R&D進行實證分析,發現董事長持有股份越多,公司創新投入越少。杜劍(2012)等選取2008-2010年創業板上市公司數據,研究結果顯示我國創業板上市公司股權激勵與企業創新投入呈負相關。
五、不相關
魏鋒和劉星(2004)利用1999年—2001三年的財務數據,研究發現國有上市公司高層管理人員持股比例對企業技術創新沒有影響。陳昆玉(2010)利用2006年入選由《關于確定一批企業開展創新型企業試點的通知》確定的37家上市公司,觀察其2001—2008的相關數據,得出管理層股權激勵對創新產出的變化沒有顯著影響。徐長生(2018)等選取A股2337家上市公司2009—2013的數據,利用傾向得分匹配法,發現股權激勵并沒有顯著提升以創新投入為代表的企業創新活動。
六、評述總結與展望
關于股權激勵對中國上市公司創新活動的影響,國內大部分學者認為股權激勵可以促進創新投入和產出,并且部分學者進一步深入研究了包含核心員工的股權激勵對創新產出的影響,如姜英兵、田軒等;同時少數學者認為股權激勵與創新活動的影響呈倒U型,存在最優的股權激勵比例,如冉茂盛等。還有部分學者認為股權激勵對創新活動具有負面影響或兩者不相關,但由于其采取的數據期間較短,導致樣本量較小,對結論的準確性有一定影響。
總體來說,股權激勵對于企業創新活動影響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個特點:一是樣本選擇更加聚焦,從滬深上市且披露了R&D費用支出的企業逐漸聚焦到某幾個細分行業下的企業;二是對于創新投入、創新產出和股權激勵等相關變量的替代指標更加合理,如股權激勵就從高管股權占比發展到了事件研究法;三是在克服樣本選擇偏誤和內生性問題方面,選擇運用傾向得分匹配法等更為合理的方法避免該問題。
隨著未來實施股權激勵時間和公司數量的增加,未來可以研究的樣本容量也會相應增加,相信可以進一步提高研究結果的準確性;在控制了公司治理結構和股權結構的情況下,未來對于股權激勵契約及激勵對象范圍的研究相信會有更多的研究價值,同時也能更好地利用股權激勵計劃提升公司的創新投入和產出能力。
參考文獻
[1]Jensen M C,Meckling W H. Theory of the Firm:Manag
erial Behavior,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1976,3(4):305-360.
[2]萬華林,股權激勵與公司財務研究述評[J]會計研究,2018,0(5):52-58.
[3]劉運國,劉雯.我國上市公司的高管任期與R&;D支出[J]管理世界,2007(01):128-136.
[4]唐清泉,徐欣,曹媛.股權激勵、研發投入與企業可持續發展——來自中國上市公司的證據[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09,31(08):77-84.
[5]孫菁,周紅根,李啟佳.股權激勵與企業研發投入——基于PSM的實證分析[J]南方經濟,2016,0(4):63-79.
[6]姜英兵,于雅萍.誰是更直接的創新者?——核心員工股權激勵與企業創新[J]經濟管理,2017,0(3):109-127.
[7]田軒,孟清揚.股權激勵計劃能促進企業創新嗎[J]南開管理評論;南開管理評論,2018,21(3):176-190.
[8]冉茂盛,劉先福,黃凌云.高新企業股權激勵與R&;D支出的契約模型研究[J]軟科學,2008(11):27-30.
[9]湯業國,徐向藝.中小上市公司股權激勵與技術創新投入的關聯性——基于不同終極產權性質的實證研究[J]財貿研究;財貿研究,2012(2):127-133.
[10]徐寧,高科技公司高管股權激勵對R&D投入的促進效應——一個非線性視角的實證研究[J]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13,34(2):12-19.
[11]趙洪江,陳學華,夏暉.公司自主創新投入與治理結構特征實證研究[J]中國軟科學,2008(7):145-149.
[12]杜劍,周鑫,曾山.創業板上市公司股權激勵機制對R&D的影響分析[J]會計之友,2012(33):94-95.
[13]魏鋒,劉星.國有企業內部治理機制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J]重慶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4,27(3):143-147.
[14]陳昆玉,創新型企業的創新活動、股權結構與經營業績——來自中國A股市場的經驗證據[J]產業經濟研究,2010(4):49-57.
[15]徐長生,孔令文,倪娟.A股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的創新激勵效應研究[J]科研管理,2018,39(9):93-101.
作者簡介:文雅(1993-),女,重慶人,碩士,重慶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400044,研究方向:企業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