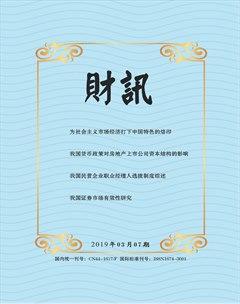管理者過度自信與并購溢價
宋斯奇 蘭天
摘 要:我國企業并購交易規模在近些年得到了大幅提升,然而并購交易市場火熱的背后隱藏著高溢價的隱性地雷,過高的溢價支付影響著資本市場中企業的并購效率與并購績效,但企業高層管理者仍然熱衷支付高額并購溢價。企業高管在并購相關決策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除了必要的經濟利益驅動,高層管理者“非理性”的認知偏差也會深刻影響并購決策的最終走向,過度自信的管理者較易在并購中高估績效低估風險從而產生決策偏差,因此從行為金融學角度研究管理者的并購溢價具有較強的理論與現實意義。本文從2014-2016年的并購交易事件為研究對象,實證檢驗了中國情景下管理者過度自信對并購溢價的影響。研究發現,管理者過度自信的企業,其并購溢價的水平更高。
關鍵詞:管理者過度自信;并購溢價
一、引言
Roll(1986)通過文獻回顧與間接證明方法發現過度自信的管理者會過高估計并購的協同效應,并購活動不會帶來收購方的財富增加反而會造成價值損失,就此提出了"自大假說"。Roll認為在有效市場里,企業的股票市值反映了自身的價值,并購溢價的支付是由于管理層對并購標的實際價值的高估,支付了遠超其實際價值的對價。Malmendier和Tate(2005,2008)以及其后續研究研究了福布斯排行版前500位的CEO投資決策,發現過度自信的管理者髙估了投資項目的回報率,會為投資項目付出更多現金流,所在并購競價中將支付更高水平的溢價;Aida Smaoui(2010)研究了法國1999-2007年期間的并購行為,發現自負的首席執行官傾向于與更高的收購溢價收購,Mohamed、Souissi與Baccar從投資現金流敏感性角度研究管理層投資決策的影響,最終發現CEO的樂觀偏差可以解釋企業投資的政策扭曲,影響了管理層支付的投資現金流量。
國內學者楊超(2014)研究發現管理者過度自信導致過高的并購溢價程度,其中女性與受教育程度較高的管理者都表現得更為過度自信,且過度自信管理者支付的溢價程度耍較之理性管理者要高。李夢瑤(2014)從成長壓力與管理者過度自信角度分析了企業治理對并購溢價的調節作用,結果兩職分離與董事會比例對成長壓力與管理者過度自信起不到調節作用,但管理者的盈利預測與并購溢價呈正相關。國內現有研究大多集中在管理者過度自信對并購決策、并購頻率、并購績效的研究,大多數學者都認為企業管理者的過度自信會高估自身企業和目標企業的價值,過度自倍管理者更傾向發起并購活動(傅強、方文俊,2008),但基于管理層過度自信而進行的并購決策往往會造成主并企業價值減損(宋淑琴、代淑江,2015)。
從企業并購的角度出發,學者們也普遍認同管理者過度自信會影響企業的并購行為。國外學者通過實證研究發現了管理者過度自信與并購溢價正向相關的關系,但國內對于這方面的研究還相對空缺。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統財務理論在“理性經濟人”假設的基礎上,認為信息不對稱理論和委托代理理論是企業溢價并購產生的根源。隨著金融市場上各種異常現象的積累,傳統的理論得到了質疑,此時行為金融理論悄然興起。行為金融理論打破了傳統的“理性”思維,將“有限理性”引入分析框架,認為決策者在投資決策中存在非理性行為。經濟生活中的復雜決策是考慮多種因素作用影響的綜合結果,不僅僅是單純考慮經濟價值最大化。在實際生活中由于決策者是有限理性、甚至會面臨多種沖突的目標以及多變的期望水平,所以大多數人在進行重大決策時會受到心理因素的干猶而使期望偏離理性,因此當管理者面臨并購決策時,其作出的選擇行為模式會表現出明顯的非理性偏差。過度自信是普遍存在的一種有限理性的認知偏差,個體高估自身知識的準確性,低估失敗的風險從而高估成功的可能性。
現有文獻對高管在并購溢價決策中的作用進行了較多研究,Roll(1986)、Hayward與Hambrick(1997)、Malmendier與Tate(2008)的研充都發現高管的行為特征與并購溢價決策水平有密切關系;因為管理者是企業并購決策的主導者,這種絕對控制權往往使得管理層產生控制幻覺,產生認知偏差。根據自我歸因理論,過度自信的管理層往往將決策的成功歸因于自己能力出眾,而忽略各種客觀因素,因此管理層在進行并購決策時,會較多依賴以往的經驗,不能有效而無偏的處理有用信息,僅依據輕松可得的結果評估當前并陶項目的可行性,從而對并購前景過于樂觀,高估并購后的協同效應,忽略項目潛在風險因素,導致對并購標的估值過高,在并購決策中支付過高的溢價。基于此提出假設:企業管理者過度自信程度越髙,支付的并購溢價越高。
三、模型與研究設計
根據前面的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管理者過度自信能夠影響企業的并購決策行為,管理者可能高估目標企業價值,支付更高溢價,因此,本文設計以下模型驗證文章的假設:
PRE=α0+α1OVERCONF+α2CONTROL+ε
在現有文獻的基礎上,本文研究變量的設計融合了前人的研究成果,結合本文硏究假設,選擇的被解釋變量為并購溢價,主要解釋變量為管理者過度自信,控制變量主要從公司財務特征與內部公司治理兩方面設置,包括績效(ROA)、成長性(TOBINQ)、規模(SIZE)、股權集中度(TOP1)、高管薪酬(SALARY)及會計信息質量(DISCACC)等。
本文采用唐宗明、蔣位的辦法度量并購溢價。并購溢價(PRE)=(并購支付價格-標的物賬面價值)/標的物賬面價值,解釋變量主要由兩部分組成,管理者過度自信及內部控制。
本文的解釋變量是管理者過度自信。對于管理者過度自信的衡量,學者們采用的方法都表現出一定的主觀性,主要有以下幾種方法:一是管理層持股變化情況這種方法用CEO持有企業股票或期權的變化程度衡量管理者過度自信,但由于我國實施股權激勵的企業占比較小,采用迄種方法衡量樣本的代表性較弱;二是管理者薪酬集中程度,該指標用管理者相對薪酬作為替代變量,認為薪酬的高低與管理者控制權相關,管理者薪酬越高,越容易過度自信,但這種方法僅用單一薪酬指標衡量管理者對企業的控制程度,不夠健全;三是主流媒體對CEO的評價,這種方法具有較強的主觀性,且在中國較難實行;四是采用CEO個人特征變量,該種方法選擇CEO個人特征變量為管理層過度自信的替代變量,真正從管理者個人特征角度出發,但這一方法比較片面,難有說服力。
綜合上述分析,本文擬采用學界普遍認可的并購中管理者過度自信導致的后果,即高估并購后所能帶來的并購績效、低估并購過程中的風險來評定管理者過度自信,它綜合兩個方面的指標,即并購前后的并購績效波動情況及并購前后的風險系數波動情況。對于并購績效波動情況用凈資產收益率(ROE)的變動來衡量,因為凈資產收益率能夠綜合概括公司利潤的增長速度,是公司運用凈資本獲利能力的集中體現,并且中國證監會將它作為衡量企業績效的基本指標,因此可以選取并購當年ROEt作為并購當年績效的衡量指標,并購后第一年度的ROEt+1作為并購后績效的衡量指標,通過比較兩年ROE,當ROEt>ROEt+1時認為管理者高估并購后所能帶來及并購績效。對于并購風險的波動情況采用息稅前利潤(EBIT)的標準差衡量,風險可以表現為資產產生的回報即EBIT的波動性,EBIT的波動性愈大,則經營風險愈高。運用概率論知識可將EBIT 視為一個隨機變量,當EBIT的離散程度越高,則意味著并購風險越大。EBIT 的離散程度,可用 EBIT 的標準差來衡量,可以用企業并購當年及歷史三年的EBIT 的標準離差率σt(EBIT)及并購后一年年及歷史三年的EBIT 的標準離差率σt+1(EBIT)來衡量并購風險的波動情況,標準離差率為標準差除以其均值,σ(EBIT)越大,則風險越大,當σt(EBIT)<σt+1(EBIT)時認為管理者低估并購過程中的風險。當管理者同時滿足ROEt>ROEt+1及σt(EBIT)<σt+1(EBIT)認為管理者出現過度自信(OVERCONF),取值為1,否則仍未管理者沒有出現過度自信,取值為0。
本文通過收集國泰安并購重組數據庫和企業年報數據庫得到2014-2016年發生并購重組事件全部A股上市企業樣本以及當年的相關財務數據。本文主要使用Stata軟件進行數據處理和統計分析。
四、實證分析
根據前述的樣本選擇標準,本文共搜集整理到2014-2016年數據可用并購案例共1977起,其中屬于管理者過度自信的并購案件共有375起,沒有出現管理者過度自信的并購案例共1602起;全樣本中出現溢價并購的并購案例共534起,占比達到了27.01%。分年度來看,2014年溢價并購案例占2014年并購案例的24.25%,此數值2015年為24.91%,2016年為30.63%,到2017年,溢價并購案例以達到2017年并購案例的36.09%。管理者在經營過程中溢價并購的案例次數總體趨勢較高,且有逐年上升的趨勢,符合中國經濟發展大趨勢。
表1體現了對我國上市公司并購事件全樣本與分樣本的描述性統計。根據表2,從全樣本來看,并購溢價的均值為0.83,從并購溢價樣本來看,溢價平均數達到了4.86,并購溢價率最大值達到了428.51,同時各個公司之間并購溢價率的差距明顯,標準差為29.58,溢價并購企業的溢價呈現較大的離散程度。
表2反映了變量間的Pearson相關系數檢驗結果。其中,管理者過度自信(OVERCONF)與被解釋變量并購溢價(PRE)具有正相關關系,由此可以看出管理者過度自信的企業更容易支付較高溢價,該相關關系與我們的假設預期結果相一致。在控制變量的相關關系中,反映管理層權利的變量(SALARY)、(TOP1)與并購溢價顯著正相關,說明主并企業管理層的權力越大,股權集中度越高越容易在并購中支付高溢價;企業的凈資產收益率與并購溢價顯著正相關,說明企業效益越好,主并企業支付的溢價越高。其他財務特征如公司規模、公司財務杠桿系數與并購溢價呈現正相關關系,可能由于企業的高發展潛力與髙經營能力影響企業對并購后協同效應的估計,導致對目標企業的過髙估值,產生高溢價;公司的成長性與并購溢價呈現負相關、會計信息質量即可操縱性應計利潤與并購溢價呈現正相關,說明公司的成長性、會計信息質量較差時,在并購中容易產生高溢價。
表3是管理者過度自信與并購溢價的實證結果。從模型整體來看,DW值為1.8209,接近與2,說明該模型的殘差項自相關性不強。模型顯著性檢驗的F值為1.98,P值為0.0399,小于5%的顯著性水平,說明該模型可以從整體上解釋因變量的顯著性水平。在共線性檢驗方面,所有自變量與控制變量的VIF都小于2且容差大于0,說明各變量之間不存在顯著共線性問題。
五、研究結論
本文主要研究了管理者過度自信與并購溢價,并力求探索其中的關系。在對現有文獻進行梳理的基礎上,分析了管理者過度自信對并購溢價的影響,通過理論分析,我們提出了假設,并通過實證檢驗了假設的合理性,最終得到了以下結論:
管理者過度自信的公司更可能支付較高并購溢價。企業高管是經營管理決策的主導者,由于信息不對稱,管理者的并購決策一般依賴自己的職業判斷與以往經驗,而不同的個人特質因素的差異使得管理者擁有不同的價值觀與個人認知偏差,所企業管理者的并購決策可能由于個人特征的異質性而存在差異。過度自信的管理者可能由于控制幻覺的存在高估自己的能力,或者因為易獲性偏差、鋪定偏差高估并購項目的收益性、低估項目風險,從而過高評化標的企業價值,造成不合理的溢價支付。
中國金業尚在快速發展的黃金時期,商速膨化的發展速度使企業管理者難以避免地出現自我膨脹與過度自信傾向,在公司并購決策中管理者可能因商佔并購后協同效應而支付較高溢價,產生非理性支付。結合本文實證研究的結果,同時考慮我國的經濟社會現實情況,筆者從公司層面出發提出以下幾點建議,希望能幫助公司管理者提高理性決策水平、減少管理層的過度自信行為帶來的負面效應,進而能夠改進管理水平、提升企業價值。一是,完善公司的內部治理機制,適當限制職業經理人的控制權。二是,建立高層管理者學習與進修機制,不斷提巧高管團隊的專業素養與職業道德水平。
參考文獻
[1]林斌,林東杰,胡為民,謝凡,陽堯.目標導向的內部控制指數研究[J]會計研究,2014,08:16-24+96.
[2]宋淑琴,代淑江.管理者過度自信、并購類型與并購績效[J]宏觀經濟研究,2015,05:139-149.
[3]梁上坤.管理者過度自信、債務約束與成本粘性[J]南開管理評論,2015,1803:122-131.
[4]潘愛玲,劉文楷,王雪.管理者過度自信、債務容量與并購溢價[J]南開管理評論,2018,2103:35-45.
[5]宋光輝,閆大偉.并購溢價協同效應分析[J]特區經濟,2007,04:259-260.
[6]SylilC·Mobley.The Challenges of social Economic Acco unting: The Accounting Review.1970.11
[7]Drik Mattem,Jeremy Moon. Cooperate Social Responsi bility: Journal of Business Etllies.2004.8
[8]Ahlned Belkaou. Social Economic Accounting:The Journalof Accounting.19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