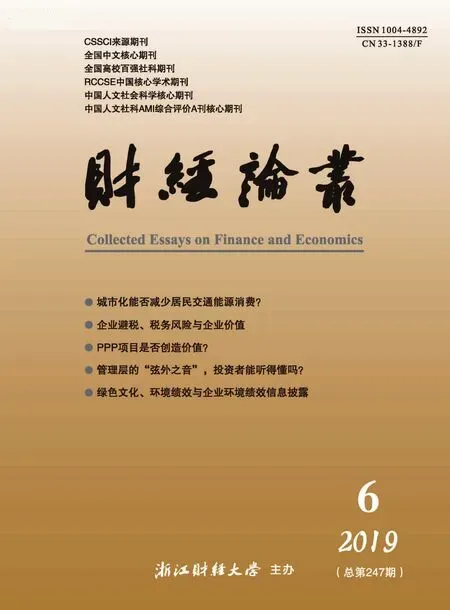環境規制與城鎮居民收入不平等
——基于異質型規制工具的視角
何興邦
(西南石油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四川 成都 610500)
一、引 言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建設美麗中國”。中央和地方政府開始逐步將生態保護納入對各地政府官員的政績考核,加大環境規制力度,但環境規制日趨加強產生的經濟社會影響是決策者必須面對的問題。結合文獻研究現狀來看,環境規制產生的經濟社會影響是十分廣泛的,涉及對技術創新、增長效率、產業結構調整和節能減排等多方面的影響[1][2][3][4]。本研究將環境規制的經濟社會影響拓展到收入分配領域,從理論和實證兩方面考察環境規制對收入分配的影響。
現有研究較少直接考察環境規制對收入分配的影響,但研究環境質量與收入不平等兩者關系的文獻較多。盛鵬飛(2017)基于中國2002~2013年的省級面板數據,發現低收入群體由于健康人力資本投資較少,環境污染更大程度地損害低收入群體的健康,從而擴大收入不平等[5]。Boyce(2007)認為收入不平等改變公眾對環境質量的偏好,進而影響政府的公共環境政策和環境質量[6]。祁毓和盧洪友(2013)基于1980~2010年132個國家面板數據,發現世界范圍內收入不平等是影響國家環境質量的一個顯著因素,而收入不平等對發展中國家環境質量的影響較大,對發達國家的影響則相對較小[7]。占華(2016)采用碳排放量和強度來測度污染,發現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顯著降低中國環境質量[8]。申偉寧等(2017)采用京津冀地區1994~2014年相關數據,發現2005年后收入不平等因素顯著加劇京津冀地區環境質量的惡化[9]。
一般來講,環境規制是規制主體通過各種環境規制工具對企業和消費者行為加以約束,使環境成本內部化的行為[10]。收入分配是各個社會成員占有的社會財富在各成員手中的積累和分配狀況[11]。從兩者的定義來看,很難直接厘清環境規制影響收入分配的內在邏輯。但從中國近幾年經濟社會發展的事實來看,環境規制和收入分配似乎在時空上又存在某種聯系。大量的文獻研究顯示,近年來我國環境規制強度出現穩步增加的態勢[12]。與此同時,根據多數學者測算的結果來看,近幾年我國收入分配形勢的惡化也在同步演進中[13]。那么,兩者之間時空的關聯性是偶然還是存在某種因果聯系?本文試圖探討并回答這一問題。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由于環境規制主要對象為分布在城鎮的企業和消費者,其影響范圍主要限于城鎮居民,因此本研究主要考察環境規制對城鎮居民收入分配的影響。
一般而言,環境規制政策工具主要包括命令控制型和市場激勵型兩類,前者是指政府通過法律、法規、部門規章和制度等政策來確定環境規制的目標和標準,然后通過行政強制性命令的方式對被規制者的行為進行直接管理;后者主要通過收費或補貼等顯性的市場手段影響企業排污決策。這兩類工具對被規制對象的作用機制和強制性都存在顯著差別,因而產生的政策效力也不盡一致。為增強研究的實用價值和政策意義,本研究選擇從異質型環境規制工具政策效力差異的視角來考察環境規制的收入分配效應,為科學制定政策提供一定的借鑒。
二、影響機理分析
(一)環境規制工具對收入分配的共同影響
1.環境規制基于行業成本效應異質性對收入分配產生的影響
常見的排污費、罰款和強迫減(停)產等規制方式直接增加被規制企業的成本,從而減少被規制者的收入所得。但由于不同行業的污染物排放強度存在差異,環境規制部門對不同行業施加的規制強度存在異質性,對不同行業成本的影響也存在差異,因而影響收入分配。一般來說,污染排放強度低、對環境影響較小的現代服務業、新興科技業等綠色清潔產業,環境規制對其生產經營活動的影響較為有限。反之,一些對環境損害較大的污染產業往往受到規制者的重點管制。規制者從標準制定、督查頻次和執法嚴厲程度等對污染產業生產經營者施加更強的外部環境約束。在此情況下,環境規制強度的非對稱性往往造成污染產業的相對收入減少,從而影響收入分配。
2.環境規制基于技術創新對收入分配產生的影響
首先,環境規制對技術創新可能存在顯著的影響。Porter(1991)較早探討環境規制對技術創新的影響,認為環境規制可倒逼企業創新,從而抵消環境規制產生的成本,即著名的“波特假說”[14]。隨后,大量的研究都支持“波特假說”,認為嚴格的環境規制增加企業成本,企業須采取必要的行為削減該成本,進而為企業的創新活動提供有力的激勵。然而,技術創新可能顯著影響收入分配格局。一方面,技術創新帶來的技術進步增加市場對某一特定技能勞動者的需求,同時亦替代一部分非技能勞動者,這種技能偏向的技術進步引起長期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基于新技術、新經營模式的新產業崛起加速引發產業間收入和利潤的再分配,使創新產業攫取更多的經濟利潤,加劇了收入不平等。
3.環境規制基于企業規模非均衡分布對收入分配產生的影響
首先,環境規制可能影響企業規模分布。在環境規制約束下,企業須增加投資污染治理設備以達到排放標準。對資金實力雄厚的大型企業而言,必要資本投入量對企業資金壓力較為有限,還可通過生產規模優勢攤薄成本。但中小企業為符合環境規制標準而新增的必要資本投入量在較大程度上增加企業資金壓力。在此情形下,中小企業的進入決策更加謹慎,進而對行業企業規模分布產生影響。另外,中小企業內部資源較少,從政府和銀行等外部獲得資源能力較弱。當成本上升持續沖擊企業盈利空間時,中小企業可能倒閉或被兼并而退出市場,最終影響企業規模分布。然而,企業規模非均衡分布又可能顯著影響收入分配:一方面,大企業往往具有更強的市場競爭力,可憑借資金優勢、技術優勢和營銷渠道優勢等不斷擠壓中小企業的盈利空間,加劇行業內收入分配不平等;另一方面,大型企業往往具有更強的對上下游行業企業議價權,推動行業間利潤再分配,從而加劇收入分配失衡。
(二)異質型環境規制工具對收入分配的差異影響
命令控制型和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工具在多方面存在明顯的差異,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執行規則存在差異。在中國,常見的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工具主要有“三同時”制度、環境影響評價制度、限期治理制度、總量控制制度等,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工具包括排污費、排污權交易制度和環境保護稅等。兩類環境規制工具在作用對象和作用方式等方面存在明顯差異。二是懲罰力度存在明顯的差異。通常而言,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工具具有更高的強制性,違反規定面臨的處罰力度更大。比如,常見的污染排放標準嚴格約束企業污染排放水平。一旦企業未達到設定標準,可能受到罰款、停產整改甚至勒令退出等帶有懲罰性質的處理,成本遠高于遵守規制下產生的各項支出。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不存在懲罰性質的處罰,企業不必擔心來自規制部門過于嚴厲的處罰。三是企業自主性存在明顯的差異。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工具允許企業基于利潤最大化原則自主通過市場化手段決定產量和污染排放水平。但在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下,企業無法通過市場手段降低污染排放,減少了企業的自主選擇空間。
由于兩類環境規制工具在執行規則、懲罰力度和強制性等方面存在明顯差異,對企業成本、技術創新和企業規模非均衡分布的影響也大不相同。因此,命令控制型和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工具對城鎮居民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影響存在異質性。
三、實證研究結果及分析
(一)變量選擇和數據來源說明
1.被解釋變量
本文的被解釋變量為城鎮居民基尼系數(Gini),以衡量地區城鎮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采用田衛民(2012)的計算方法,可得到多數省份城鎮居民的基尼系數[15]。對僅給出最低收入組和最高收入組的省份,本文采用胡祖光(2004)的方法求得基尼系數[16]。另外,對少數年份未公布收入分組數據的湖南、云南和天津三省市,我們采用平均增加率法補全缺失數據。相關的數據來源于2000~2014年《中國統計年鑒》和各省市統計年鑒。
2.主要解釋變量
本文的主要解釋變量為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強度指數(Command policy)和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強度指數(Market-based policy),以分別反映兩類規制政策強度,均通過構建環境規制強度指標體系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CA)來獲得(見表1所示)。
關于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強度評價體系的構建,本研究選取的基礎指標包括四個:環境處罰案件與地區人口比值,以環境管理部門執法頻次來衡量;環境治理投資占地區GDP比重,以地區環境治理投資金額或規模來測度;環評執行率,以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執行嚴格程度來估算;環保系統人員占人口比重,以機構建設和人員配備規模來表示。相關的數據來源于2000~2014年的《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環境年鑒》。
關于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本研究選取的基礎指標包括三個:排污費占地區GDP比重、車船稅占GDP比重和資源稅占GDP比重。需要說明的是,由于中國在2018年才正式開征環境稅,所以多數學者都采用排污費來測度。另外,本研究繼續加入車船稅占GDP比重和資源稅占GDP比重,主要是考慮車船稅和資源稅兩個稅種具有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的目的,其稅率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政府通過市場化手段進行環境規制的強度。相關的數據來源于2000~2014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環境年鑒》和《中國稅務年鑒》。

表1 環境規制強度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在構建兩類環境規制強度指標評價體系的基礎上,本研究先對各基礎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然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分別獲取兩個指標體系的特征根和貢獻率。在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強度指標中,前三個特征值的累積貢獻率已達93.56%,我們將其作為主成分,并對載荷矩陣進行旋轉后得到相應的特征向量[注]限于篇幅,正文未報告兩類指標主成分因子對基礎指標的載荷情況,作者備索。。在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強度指標中,前兩個特征值的累積貢獻率達到87.79%,我們將其作為主成分,并對載荷矩陣進行旋轉后得到相應的特征向量。另外,在對載荷矩陣進行旋轉前,通過KMO和SMC檢驗來考察主成分分析法的適用性。在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強度指標中,KMO值為0.7459,SMC值均大于0.5。在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強度指標中,KMO值為0.6925,SMC值均大于0.6。因此,KMO和SMC檢驗結果顯示各基礎指標的共性較強,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是符合要求的。
3.控制變量
人均GDP對數(Inrgdp),以控制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對城鎮居民收入分配的影響。人均受教育年限(Education),以控制地區教育程度對城鎮居民收入分配的影響,通過現行學制與各學歷層次人數進行加權平均獲得[注]文盲受教育年限為0,小學為6年,初中為9年,高中為12年,大專及以上為16年。。財政支出占GDP比重(Public expenditure ratio),以控制政府行為對城鎮居民收入分配的影響。國有化率(State-owned ratio),以控制地區所有制結構對城鎮居民收入分配的影響,采用國有企業職工占城鎮總就業人口比重來衡量。城鎮化率(Urbanization),以控制地區城市化發展水平對城鎮居民收入分配的影響,采用地區常住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來衡量。相關的數據來源于2000~2014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工業統計年鑒》和各省市統計年鑒。

表2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分析
(二)回歸模型
為檢驗異質型環境規制工具對城鎮居民收入分配的影響,本研究建立以下的回歸方程:
Giniit=β0+β1Ginii,t-1+β2Commandpolicyit+β3Market-basedpolicyit+φZit+ui+εit
(1)
其中,Giniit為衡量城鎮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數;Ginii,t-1為滯后一期的基尼系數,以反映城鎮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演變的慣性趨勢;Commandpolicyit和Market-basedpolicyit為命令控制型和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強度指數;Zit為控制變量,包括人均GDP對數、人均受教育年限、財政支出占GDP比重、國有化率和城鎮化率;ui和εit為地區固定效應和隨機干擾項。(1)式的回歸方程引入被解釋變量的滯后一期而成為動態面板。在此情況下,一般可采用水平GMM和系統GMM兩種方法。系統GMM不要求擾動項的準確信息分布,以提高估計的效率和穩健程度[17]。系統GMM可采用一步和兩步GMM估計,兩步估計的標準差存在向下偏移,但經有限樣本校正后減少,且兩步GMM估計對異方差和截面相關性具有較強的穩健性。基于此,本文采用兩步系統GMM方法估計模型參數。需要說明的是,本文主要考察環境規制對城鎮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響,而收入不平等同樣可能通過公眾的環境意識對政府的環境規制政策產生影響。如果將環境規制視為外生變量進行回歸,則可能產生內生性問題。本研究分別選取命令控制型和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強度指數的一個更高階的滯后項(即二階滯后項)作為工具變量[注]需要說明的是,盡管回歸模型中僅包括命令控制型和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強度指數的當期變量,但差分方程中包括其一階滯后項,因而更高滯后項為二階滯后項。,然后進行兩步系統GMM估計。
(三)回歸結果
在表3中,Arellano-Bond序列相關檢驗二階序列相關檢驗(AR(2))和Sargan檢驗結果顯示采用系統GMM模型是合理的。表3的第1列僅控制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對城鎮居民收入分配的影響,第2列引入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的影響,第3列繼續控制人均GDP、人均受教育年限、財政支出占GDP比重、國有化率和城鎮化率等變量的影響。結果顯示,無論是否引入其余變量,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都顯著提高城鎮居民基尼系數水平。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強度指數增加1,城鎮居民基尼系數增加0.017。與此同時,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對城鎮居民收入分配的影響程度較小且并不顯著。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強度指數增加1,城鎮居民基尼系數僅增加0.0011。這一回歸結果顯示命令控制型和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對城鎮居民收入分配的影響的確存在明顯差異,前者顯著加劇城鎮居民收入不平等,后者并不是城鎮居民收入分配失衡的顯著影響因素。

表3 環境規制對城鎮居民收入分配的影響:全樣本的回歸結果
注:括號內為標準誤;*、** 和*** 分別代表10%、5%和1%的顯著性水平。下表同此。
考慮到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異質性,環境規制對不同區域城鎮居民收入分配的影響可能存在差異。為檢驗異質型環境規制工具對不同區域城鎮居民收入分配的異質性影響,本文仍基于(1)式的回歸方程并采用系統GMM模型,分別考察不同類型的環境規制工具對東中西部地區城鎮居民基尼系數的影響(回歸結果見表4所示)[注]東部地區包括北京、天津和河北等11個省(市),中部地區包括山西、黑龍江、安徽和江西等7個省(市),西部地區包括四川、重慶、貴州和云南等11個省(市)。。

表4 環境規制對城鎮居民收入分配的影響:分地區的回歸結果
首先,由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工具對不同地區城鎮居民收入分配的影響可發現,影響程度的大小呈現東中西依次遞減的格局。其中,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對東部和中部地區城鎮居民的基尼系數的提升作用顯著。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強度指數增加1,東部地區城鎮居民基尼系數增加0.0251,中部地區城鎮居民基尼系數增加0.018。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對西部地區城鎮居民的基尼系數的提升作用較東中部小且并不顯著。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在不同區域產生的收入分配效應顯示,在不同區域都沒有顯著加劇城鎮居民收入不平等。
四、擴展分析: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對收入分配的門檻效應檢驗
前文,我們發現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對不同地區城鎮居民收入分配的影響程度存在東中西部依次遞減的格局。由于本文測算的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強度指數在多數東中部省份強度靠前,表明高強度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對城鎮居民收入分配的影響程度更大[注]限于篇幅,正文不再詳細公布基于主成分分析法計算的各省份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強度指數,作者備索。。因此,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對城鎮居民收入分配的影響可能存在門檻效應。為檢驗這一門檻效應是否存在,我們借鑒Caner和Hansen(2004)采用的方法[18],以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強度指數(Command policyit)為門檻變量,建立如下的動態面板門檻模型:
Giniit=θ0+θ1Ginii,t-1+θ2CommandpolicyitI(Erit≤γ)+θ3CommandpolicyitI(Erit>γ)+
θ4Market-basedit+ξZit+ui+εit
(2)
其中,I(·)為指標函數,數值取決于門檻變量(Commandpolicyit)和門檻值(γ):當括號內的表達式成立時,I(·)=1;否則,I(·)=0。另外,(2)式的其他變量與前文(1)式一致。由于模型中包含被解釋變量的滯后項,使Caner和Hansen提出的分布理論無法直接應用于動態面板模型。為解決這一問題,Kremer等(2013)采用前向離差變換來消除固定效應。經前向離差變換后的誤差項不存在序列相關,且方差具有單位的形式[19]。不過,由于(2)式含有被解釋變量的滯后項Ginii,t-1,模型可能存在內生性的問題。本研究將內生變量Ginii,t-1作為被解釋變量,然后對其一階滯后項(Ginii,t-2)和其他解釋變量做最小二乘法回歸,再將回歸得到的預測值作為內生解釋變量的工具變量帶入回歸方程中。按照Caner和Hansen采用的方法確定門檻值,并采用GMM方法得到參數的估計值。在估計門檻模型之前,須先檢驗是否存在門檻效應并確定門檻數量,通過拔靴法bootstrap(300次)的門檻效應檢驗(見表5所示)。

表5 動態面板門檻效應的檢驗結果
表5顯示,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接受單一面板門檻模型且估計值為-0.6183。在確定單一門檻值后,采用GMM方法可得到參數的估計值(見表6所示)[注]表6未報告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強度對城鎮居民收入分配的影響,作者備索。。

表6 基于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強度的動態面板單一門檻模型回歸結果
表6顯示,當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強度指數低于門檻值時,其對城鎮居民基尼系數的影響為0.0002且在10%的水平下并不顯著。但跨越門檻值之后,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強度對城鎮居民基尼系數的影響為0.0301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接受這一回歸系數。可見,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對城鎮居民收入分配的影響的確存在門檻效應。較低的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強度對城鎮居民收入分配的影響并不顯著且程度較小,但強度跨越門檻值之后,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顯著加劇城鎮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
五、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將環境規制的經濟社會影響研究拓展到收入分配領域,并側重從異質型規制工具收入分配效應差異性的視角來考察環境規制對城鎮居民收入分配的影響,發現環境規制對城鎮居民收入分配的影響取決于規制工具的選擇。總體上,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顯著加劇城鎮居民收入不平等,而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并未顯著影響城鎮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分區域來看,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對東部地區城鎮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響程度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小。而在不同區域,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都未顯著影響城鎮居民收入不平等。最后,基于動態面板門檻模型的實證結果顯示,適當強度的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沒有顯著影響城鎮居民收入分配,而當強度高到跨越某一門檻值時,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就顯著加劇城鎮居民收入分配不均。
本文研究結論包含豐富的政策啟示,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完善與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相關的配套政策。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的目標明確、強制性高、約束力強,也是環境規制政策工具中的重要一環。但在發揮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工具生態效應的同時,也要考慮其是否過度沖擊產業、擴大收入差距,因而引入一些配套政策是必要的(如提供過渡期的經濟救助、設立配套資金以協助污染企業轉型、加強企業員工的職業再培訓等)。
二是優化政策工具使用。鼓勵決策者運用市場手段進行規制,增加被規制企業在產量、技術路徑和污染治理等方面決策的自主選擇空間,實現環境治理和企業良性發展雙贏的局面,推動地區協調、均衡發展。
三是因地制宜,增加政策彈性。環境規制對不同地區城鎮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響存在較大的異質性。環境規制顯著加劇東部和中部地區城鎮居民收入不平等,表明政府在重點區域的環境規制方式、力度和配套政策制定上需考慮收入分配因素,減少環境規制可能產生的社會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