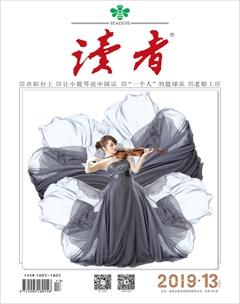讓小提琴說中國話
崔雋

1959 年5 月27 日,上海蘭心大戲院,俞麗拿在《梁祝》小提琴協奏曲首演上擔任獨奏
79歲的俞麗拿刷屏了,這可能是她本人都沒想到的。
2019年3月26日,《真愛·梁祝》在上海舉辦了啟動儀式。這部音樂劇場作品是為紀念《梁山伯與祝英臺》小提琴協奏曲誕生60周年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所作,也是俞麗拿封琴近10年后首次參與的新作。消息一出,各個媒體平臺紛紛轉發。
發布會上,《梁祝》的演奏者俞麗拿和作曲家陳鋼、何占豪再次聚首,他們的合影勾起網友們的回憶。60年前,這群年輕人懷著真摯的初心,用一段唯美纏綿的中國愛情故事,為共和國10歲誕辰獻上祝福。“《梁祝》是共和國成立以來最成功的小提琴協奏曲,在世界名曲中占有一席之地。”“俞麗拿是《梁祝》最權威的演奏者,我每次聽都淚水漣漣。”人們在評論區里分享著屬于自己的《梁祝》回憶。
共和國的弦上蝶舞
1959年5月27日,《梁祝》作為國慶10周年的獻禮曲目首演。《梁祝》全曲超過25分鐘,在凄婉唯美的《化蝶》章節后,尾聲的收音輕如羽毛。隨著這片羽毛輕輕落下,上海蘭心大戲院的觀眾席一片寂靜。這一刻,臺上19歲的俞麗拿惴惴不安。盡管此前經過了無數次排演,她仍不確定這首中西交融的小提琴協奏曲能否被觀眾接受并喜歡。然而幾秒鐘后,潮水般的掌聲向她涌來。她怔忡著謝幕、下臺。掌聲一直沒有停,她和躲在臺口的陳鋼、何占豪再次登臺謝幕。掌聲依然沒有停,于是俞麗拿搭上琴弓,來了一次毫無準備的返場演出。
無論是俞麗拿、陳鋼還是何占豪,幾十年來,他們都在不同場合提起過這一天,提起這段與《梁祝》結緣的金色時光。在那個奮進激昂的年代,這是屬于他們的青春和浪漫。
對俞麗拿來說,這段時光開啟于1951年。那年秋天,上海的報紙上刊登了一則招生啟事,著名音樂家賀綠汀要在上海國立音專(上海音樂學院前身)創辦“少年班”。
此時的俞麗拿11歲,成長在現代音樂氣氛濃厚的上海,從小學習鋼琴。得到消息后,她報名參加了“少年班”考試,最終被錄取。入學半年后,學校為平衡專業人數,將俞麗拿和幾名同學從鋼琴專業分配到小提琴專業。雖然從零開始,但俞麗拿勤奮認真。沒過兩年,俞麗拿已經成為班級里進步很快、技法最嫻熟的學生。
1957年夏天,俞麗拿升入上海音樂學院管弦系學習。經過院長賀綠汀的爭取,此時的上海音樂學院搬入市中心,學生們的演出機會多了起來,劇場、工廠、農村……都有他們活躍的身影。但俞麗拿和同學們的苦惱漸漸出現了——他們發現,無論到哪里演出,小提琴好像都不受歡迎。“聲樂系的同學唱兩首中國歌曲,臺下一片叫好聲,都是‘再來一個!再來一個!我們每次演出完,觀眾的表情都很麻木,掌聲也是稀稀拉拉的。”拉琴的同學不甘心,就去問農村老媽媽:“阿姨,好聽伐?”“好聽呀!”“聽得懂伐?”老媽媽笑著擺手說:“聽不懂呀!”
在這種焦慮下,“小提琴民族學派實驗小組”應運而生。20世紀50年代,中國在文藝領域多受蘇聯影響,學生們都知道蘇聯歷史上有一個強調音樂創作民族性的“強力集團”。為了讓“小提琴說中國話”,學院決定借鑒“強力集團”的經驗,成立“小提琴民族學派實驗小組”。
在那個熱火朝天的年代,年輕人總想著為國家做些什么。俞麗拿毛遂自薦,申請加入實驗小組。“那會兒就是一門心思地想讓老百姓喜歡上小提琴。我加入小組是做了自我犧牲的準備的,不管實驗成不成功,哪怕耽誤了專業學習,都在所不惜!”
實驗小組的探索從改編民歌民曲開始。他們首次將阿炳的《二泉映月》改編成小提琴獨奏曲,又改編了民間曲調《步步高》《花兒與少年》。帶著這些作品,年輕的學生走到外灘,開始了一場即便現在看來也十分新潮的街頭演出。
俞麗拿帶著譜架,還有晾衣夾子——因為怕風把樂譜吹走。十幾個學生一頓張羅,吸引了一圈過路的人。
過了一會兒,學生們紛紛拿起樂器,人群安靜下來。當一首首耳熟能詳的民歌旋律響起的時候,俞麗拿驚喜地發現,“人們的表情不一樣了,你用小提琴講話,他們聽懂了”。這次演出讓小組成員們堅信,他們走的路是正確的。
1958年,上海音樂學院的師生在全國各省深入生活,實驗小組來到浙江。在從溫州到寧波的船上,大家頂著冷風在甲板上討論國慶10周年的獻禮曲目。當時中國缺少宏大的協奏曲和交響樂來表現民族的偉大。因此,在這個節點上,創作一部小提琴協奏曲的想法被小組成員一致通過。
那么,演奏什么曲子呢?當時正值“大躍進”,全國都在喊“大煉鋼鐵、全民皆兵”的口號。實驗小組順應時代潮流,報了《大煉鋼鐵》《女民兵》兩個選題。小組成員何占豪對越劇很熟悉,越劇《梁祝》在全國早有一定的知名度,他們又在給領導的報告上加了一個《梁祝》。

俞麗拿(右三)與上海音樂學院的師生
此后,實驗小組正式著手改編創作《梁祝》,由何占豪、陳鋼作曲,每創作一段旋律,俞麗拿就在一旁試奏一段。“這段如泣如訴的愛情故事,最難品的是味道。它來自越劇,你不熟悉中國戲曲,就不可能拉出那個味道來。我雖然是浙江人,但沒用,因為我學的是西洋那一套。所以我們研究中國戲曲,學越劇唱腔,還學二胡的拉法。這是一個全新的學習過程。”
關于《梁祝》首演謝幕的情形,俞麗拿現在能想起的畫面已經有些模糊了。“返場時,有人說我們演奏了全曲,陳鋼說其實只演了一個段落。琴是我拉的,可我什么都不記得了,大概因為太高興了吧。”這么多年來,每當回憶起那場演出,俞麗拿總會為那一天標注一個定義:“對我們來說,5月27日這天很特殊,它意味著小提琴終于被中國觀眾接受了。”
尊重藝術家的意見
1960年,俞麗拿在上海女子弦樂四重奏中擔任第一小提琴手,并參加了在柏林舉行的第二屆舒曼國際弦樂四重奏比賽,最終取得第4名的好成績。這是中國首次在國際弦樂大賽中獲得名次。就在上臺比賽前,4位中國姑娘把手疊在一起,大聲喊了一句:“為國爭光!”
20世紀60年代,周總理經常陪同到訪中國的外國貴賓來上海。隨著首演的成功,《梁祝》優美的旋律很快通過廣播傳遍大江南北。在接待外賓、安排文藝演出時,周總理也常常點名要聽《梁祝》。當時還是大學生的俞麗拿,因此與周總理有了見面交流的機會。
一次演出后,周總理很有興趣地向俞麗拿詢問有關《梁祝》的創作情況。俞麗拿驚喜地發現,周總理對她的情況很熟悉,知道她們的四重奏在柏林獲了獎。周總理說:“你們的四重奏能在這么大的壓力下獲獎,很不容易。你們辛苦了!”聽到周總理的稱贊,俞麗拿心里一熱。
在和周總理為數不多的交集里,有一件事讓俞麗拿印象最為深刻。有一次,周總理陪外國貴賓來上海,在歡迎宴會上,俞麗拿照例演奏了《梁祝》。演出結束后,周總理走到臺口,對俞麗拿說:“俞麗拿,和你商量個事。”俞麗拿記得,總理的語氣很溫和,但態度很認真,“我覺得《梁祝》太長了一點,你和兩位作曲家說一下,看能不能改短一些,這樣演奏效果可能會更好。”
聽完總理的建議,俞麗拿心里“咯噔”一下。“現在回想起來,那會兒真是年輕冒傻氣,什么叫組織紀律,什么叫政治觀念,我根本不懂。”俞麗拿的心里充滿了擔心,害怕刪減會給《梁祝》的藝術性帶來致命打擊。猶豫再三,她沒有將總理的話轉達給陳鋼和何占豪。
幾個月后,周總理又一次陪外賓來上海,在文藝演出時,他仍然點名要聽《梁祝》。還是那個宴會廳,還是俞麗拿,還是未經改動的《梁祝》。演出結束后,周總理見到俞麗拿,直截了當地問:“俞麗拿,你們沒改嗎?”
“聽完這句話,我很緊張,不知道說什么好,只能對著總理尷尬地笑。誰知道總理接下來的話,讓我記了一輩子,又敬佩又感動。他只說了一句——‘那就尊重藝術家的意見吧!你看,這就是周總理。”俞麗拿說。但這件事過后,她又認真琢磨了周總理的建議。在不同的場合,她會根據具體情況選擇《梁祝》的部分樂章來演奏,比演奏整部作品所用的時間短了很多,演出效果也很好。
幾十年來,《梁祝》的旋律在全世界響起。除了俞麗拿,呂思清、盛中國等音樂家也奉獻了《梁祝》不同版本的演繹。2016年,根據一項國際小提琴賽事的調查,《梁祝》成為在國外演奏次數最多的中國作品。
杏壇春雨潤無聲
從1962年俞麗拿留校任教,至今已經57年。俞麗拿每天6點鐘到學校,晚上10點鐘才離開。如果說年輕時俞麗拿的理想是讓中國人喜歡上小提琴,那么在當老師的幾十年歲月里,她的目標是要讓更多的學生站在世界舞臺上。“中國學生是有競爭力的,不是來‘打醬油的。”俞麗拿說。
改革開放后,俞麗拿有了更多出國演出、訪學、擔任比賽評委的機會。“那會兒,上海和國外生活水平的差距還是蠻大的,可是到了國外,我對那些都不感興趣,我只關心世界各學派最前沿的理論和技術,我要把這些都‘偷回來教給學生。”經過十幾年的努力和付出,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俞麗拿的學生在國際比賽中嶄露頭角,以黃蒙拉、王之炅為代表的優秀青年演奏家逐漸涌現出來。
如今,比起剛當教師時的手忙腳亂,俞麗拿已經相當從容。從容卻不放松,上課永遠排在第一位,這是俞麗拿幾十年的準則。她每天在教室授課長達10多個小時,唯一的休息就是中午拿出飯盒放到微波爐里熱一熱,有時她吃飯的同時也會上課。即使在聲帶手術后講不出話的時期,俞麗拿也不停課。她做了一些卡片,在學生演奏時用舉卡片的方式提醒——“弓速”“分段”“調性”“音準”……甚至還有一張寫著“帥”字。
70歲時,俞麗拿做了告別舞臺的決定。“其實那正是我演奏狀態非常好的時候,但是,一切都得為專心教學讓步。”音樂學院的教學跟普通學校不同,是一對一上課,從附小到大學畢業,一個學生的培養就得花16年。在這16年里,俞麗拿覺得自己就像他們的第二父母。每個學生她都會準備一個筆記本專門記錄,如今這樣的筆記本已塞滿整整一個文件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