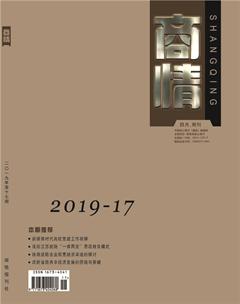單位犯罪處罰人員辨析及其與自然人犯罪的界分
陳奕欣
【摘要】如今我國的單位犯罪比例偏高,但在關于單位犯罪的處罰原則上仍存在許多不甚明確的問題,如在關于犯罪處罰人員中的單位主管人員的認定問題上,司法實踐以及學界存在爭議,在對于自然人犯罪與單位犯罪的辨析上,也存在著界定難,實行難的問題。本文擬通過對現有學說以及相關法規進行分析,對上述兩點問題進行討論。
【關鍵詞】單位犯罪 處罰人員 單位利益
我國刑法規定了兩罰制,單位畢竟是擬制的人,自然人在活動中處于主導地位。除了對單位判處罰金,還可能對單位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判處刑罰,這就存在了如何判斷主管人員以及單位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問題。再者,單位犯罪仍然是由自然人實施,在實踐中不可避免的會存在對于單位犯罪與自然人犯罪的界分不清的問題。本文擬對相關問題進行研究,并提出相應解決辦法。
一、對于單位犯罪處罰人員的界定
單位犯罪的處罰人員,分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對于兩者的具體含義以及在實踐中如何定性,存在著一些爭議,值得我們討論。
對于單位犯罪的主管人員的確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下稱《紀要》)中指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是在單位實施的犯罪中起決定、批準、授意、縱容、指揮等作用的人員,一般是單位的主管負責人,包括法定代理人。”此項司法解釋表明了對于單位的主管人員的定性,應有兩個重要條件:一是其應對單位犯罪有直接的責任。這為學界關于主管人員是否應包括起決策、組織、領導作用的人員的爭論下了一個明確的定義,且對于單位犯罪中領導的玩忽職守導致犯罪的情況也有了一個規定,使得單位犯罪的人員的界限更為明確。二是主管人員一定要有主管權,在單位中具有一定的地位,可以產生一定的影響。
而對于單位犯罪的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定義,學界觀點有重要作用說,行為參與說等等。前一學說的含義是其他直接責任人員額概念并不將所有的參與單位犯罪的人員都納入進去,而只是針對那些積極參與犯罪,在犯罪中具有一定作用的內部一般工作人員。對于沒有起到實質作用的自然人,一般不將其考慮為單位犯罪的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而行為參與說則是將單位犯罪中所有參與犯罪的單位成員都納入到了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隊伍之中。歸類比較,各種學說的重要不同就在于是否將單位犯罪的全部參與人員都規定為單位犯罪的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對此,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認為范圍不宜過大,《紀要》中寫到:“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是在單位犯罪中具體實施犯罪并起較大作用的人員,也可以是單位的職工,包括聘任、雇傭的人員。應當注意的是,在單位犯罪中,對于受單位領導指派,或奉命而參與實施了一定犯罪行為的人員,一般不宜作為直接責任人員追究刑事責任。”但《關于辦理走私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8條規定:“對于受單位領導指派積極參與實施走私犯罪行為的人員,如果其行為在走私犯罪的主要環節起重要作用的,可以認定為單位犯罪的直接責任人員。”對此,有些學者認為不將單位犯罪的所有參與人員都規定為單位犯罪的直接責任人員的理由在于其行為情節輕微,危害不大;有些學者認為這是為了減小犯罪的打擊面;而有些學者認為可以從期待可能性的角度考慮,對于參與犯罪的一些人員來說,一些單位人員很難做出違背單位領導意志的行為,在不具有期待可能性的情況下,他們的主觀惡性相對較小,因此懲罰的必要性不大。
因此我們認為可以將單位犯罪的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理解為積極參與單位犯罪活動并起到重要作用的人,這大大縮小了相關人員的范圍,在實踐中具有極其重要的指導意義。
二、單位犯罪與自然人犯罪的界分
對于單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的界分,我們仍應該進行進一步的討論。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規定:“盜用單位名義實施犯罪,違法所得由實施犯罪的個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關自然人犯罪的規定定罪處罰。”從這一司法解釋我們可以看出,單位犯罪的成立必須具有違法所得歸由單位的特點才可以。《紀要》明確規定:“以單位名義實施犯罪,違法所得歸單位所有的,是單位犯罪。”因此對于單位犯罪來說,為了單位利益而實施行為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為了實現單位利益的目的是單位意志的外在表現。單位成員實現單位共同目標的過程,就是單位自身利益的實現過程。單位成員實現單位共同目標的過程,就是單位成員實現單位整體意志的過程。但是我們對于這個觀點不能作絕對化的理解,在實踐中可能存在為了單位利益而實施的犯罪,最終在結果上并沒有體現為單位利益的獲利,甚至可能損害了單位的利益。因此對于為了單位利益這一要素的分析,理論與實踐有著差距,如果我們只是在理論層次上分析這一問題的話,勢必會造成看待問題的不全面。
但從另一方面來講,若犯罪不是為了個人利益的實現,就應該是為了單位利益,至少大多數是這樣。行為若是為了個人利益,就基本上可以排除為了實現單位利益的可能性。并且在實踐中,相對于單位意志而言,對于單位利益的判定也具有更好的可把握性。
對于為了單位利益而實施行為,最終得到的利益卻被有關人員瓜分的情況的討論,應該分情況討論,當以單位利益為初始目的進行犯罪,犯罪后將所得利益據為己有的應當認定為單位犯罪,再對犯罪人單獨處罰;而對于一開始就是以個人利益為目的,以單位利益作為媒介組織犯罪的,應該作為個人犯罪來處理。犯意不同,處罰方式也應不同,不可以概以一棒子打死,當單位只是作為個人犯罪的媒介之時,其他的自然人的社會危害性明顯不大,應只對犯罪個人進行處罰。
單位作為抽象的主體,其犯罪行為的界定無疑存在著許多難點,不管是在確定犯罪后,對于處罰人員的界分還是在將單位犯罪與自然人犯罪區分開來過程中。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更應該吸取多種觀點的有理之處,將單位犯罪由抽象的條文變為實踐中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