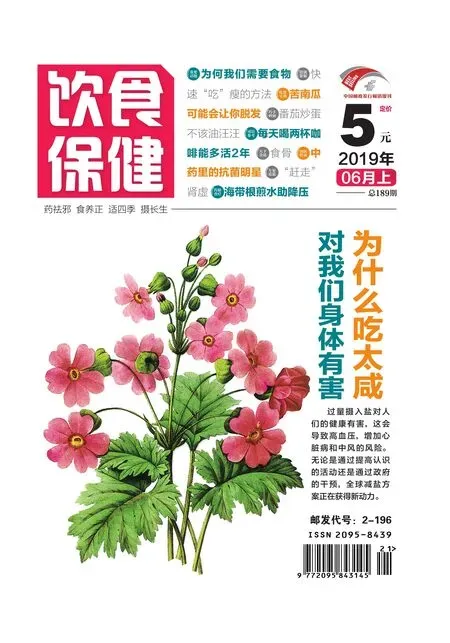紫炙飄香
文 右衽求索

京人嗜食燒烤由來已久,百姓的居家燒烤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較正式,一類較閑散。
記得幼年家中有一套鐵皮烤架和炙子,每至年節,長輩便買來羊腿自行切片,用蔥、姜、醬油、料酒、糖鹽等諸料腌過,隨后在院里置好烤架炙子,取過鐵釬(多是用自行車輻條打磨而成),然后老少分工,有人穿肉,有人燒烤,有人湊熱鬧似的撒孜然辣椒和鹽——當然,這多是我們晚輩干的。有時,家里的長輩會想起拿幾串烤好的肉送給鄰居,可能也得幾個開口石榴回來哄孩子。
另有一類烤食,多是孩童所為,捉上一籠蝗蟲蜻蜓,再去田里偷幾個玉米棒子,拔三五根甘蔗,挖一藤花生白薯,然后隨便找個沒人的地方刨坑,下面燒樹枝,上面設高粱玉米秸編好的箅子,留下花生白薯,將另外幾樣放上去烤熟了,玉米棒子剝殼,蝗蟲蜻蜓揪去頭腹,撕掉六腿四翅,只留胸部肌肉,主食肉食齊備。吃前,再將花生白薯埋入坑中灰燼,封住坑口,只留幾個通氣的小孔,待正餐吃完,掏出坑里熟透的燙手零食,撅了甘蔗,又是一通好吃。這當然是純粹的鄉野吃法,不過回家之前一定要洗凈顏面鼻孔里的塵灰,否則僅“玩火”一罪就足以換來一頓揍。所以聰明的要么毛巾包頭口罩籠嘴,要么烤時遠遠地避開,一聲“開吃”再蹦過去,出手穩準狠,蝗蟲揀大的,玉米挑嫩的,雖然最為招恨,卻也盡得實惠。
華北地區一到立秋日,自來要“貼秋膘”,又言“九月九,吃烤肉。”因夏暑難進油膩肉類,甫至寒季需要食補,若是秋季涮肉烤肉,那乃京中傳統,待暑氣一消散,很多人便攜妻帶子地殺向老字號。
北京的老字號烤肉店有宛、季、王三家,王店現已名形不彰,宛店地處南城,主烤牛肉,季店座落北城,常炙羊肉,兩者都是清真館子,號稱“南宛北季”。要說的話,舊時前門外正陽樓的烤肉還不錯,不過它并非專賣烤肉,所以才能傳承至今。這家店的烤肉雖不如另外幾家的廣為人知,但店里的其他飯菜還是頗有聲譽的。

烤肉用的羊肉尚算易獲,畢竟北京距張家口乃至內蒙都很近,好羊無數,且燕地食羊有舊俗可循。然而牛肉就不太好找了,一者古時至于民國,耕牛難得,凡大一統時代,農耕地區即不允隨意宰殺,違者還將受刑律處罰,二者舊時少有專供食用的肉牛,耕牛肉質不好,醬鹵燉煮或許適食,烤來必定極費牙簽,而且傷胃。
羊肉選后腿、上腦,牛肉擇取上腦、排骨、里脊,盡剔雜骨散筋,箅簾布包肉,用冰塊壓一夜,刀俎伺候成薄片,用蔥末姜汁、醬油料酒、蛋清蝦油、白糖精鹽等腌好。
兒時不理解店家為什么要先用冰塊把肉壓上一夜,只認為把鮮肉切片后,拌好佐料直接烤不好么?后來亂翻生化書,看了自溶酶基本工作原理才大致弄明白,這樣壓一夜確實可以使蛋白質大分子分解為蛋白胨、氨基酸等小分子,經過排酸嫩化,自然會鮮美得多。另一方面,在被冰塊壓著的這一夜里,肉里邊積存的血水會慢慢滲出,同樣是一種提高肉質的手段。
烤肉的最佳燃料是果木和松塔,如用炭類或雜亂樹枝,則等而下之,這也取決于不同的原料。牛羊肉原本多少有些膻氣,其他燃料是壓它不住的,只與松香之味相互沖和,在嗅味二覺上達到了儒家所期許的中庸境界,但又比豬肉多些郊野氣息,算是附會了道家自然。果木常用于烤鴨,其香可與鴨脂相得益彰,拿來烤牛羊肉猶如燒紫檀木供灶王爺,互不搭界。
烤肉原本是個技術活,所謂膾炙,在《周禮》中的地位僅次于處第一位的主食和肉羹。彼時天子諸侯當然不可能抄雙筷子在炙子旁邊圍成一圈等肉熟,我們想像一下——姬家大小和臣子們身坐朝堂喝著甜酒,一邊談國家大事,一邊翻烤肉,其間還有個把不上道兒的猜拳行令,吆五喝六。以這些貴族的烹飪水平,吃出個腹瀉或者食物中毒應該不算難事,說不定還會被人以春秋筆法記下來,“元年,秋,諸侯來朝,侍王狝于鎬京野,王宴臣侯,己為炙,食側,各失儀,夜,紫宮隱,星隕如雨。”那才是多恐怖的事情。
所以還是回歸市井,看看斜陽西落,兄弟幾個架上炙子,聽松塔畢畢剝剝響在下面,將肉片及嫩蔥絲條鋪陳其上,倒一杯二鍋頭,拿幾個芝麻燒餅,取過調味小碗,倒進醬油、醋、料酒、鹵蝦油,再撒把蔥姜香菜的細末,聞著酒香、松香、蔥香和肉香,手上和著諸般調料等待肉烤熟。還有人腳踏條凳,夾過來蘸蘸味料,塞進嘴巴據案大嚼,幾塊肉入肚后,咬口燒餅,吃瓣糖蒜,相互笑罵罰酒,滿腹牢騷皆被酒水漿化了。若門外有貧苦老者經過,便徑自拉進來同食,滿室沸反盈天,也算是對自己終夏忙碌的犒勞,管那隔壁還有人手捧一冊甲戌本《脂硯齋評石頭記》就著秋風夜雨哭哭啼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