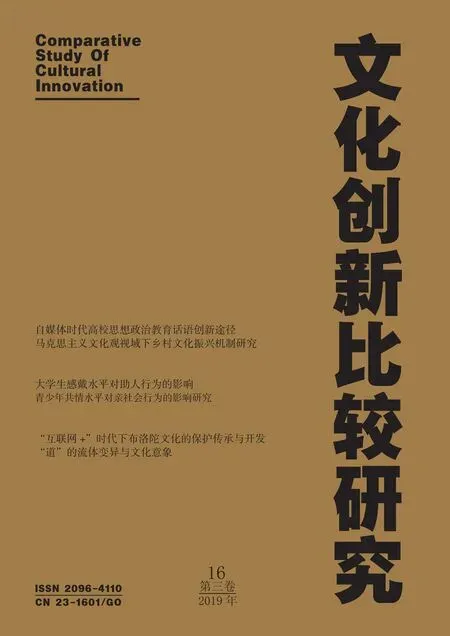國內語言態度的研究方法
——“配對變語實驗”研究綜述
劉楊秋艷
(新疆師范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新疆烏魯木齊 830017)
1 術語的三種翻譯方式
The match-guise technique 是測試語言態度的一種研究方法,最早是20世紀60年代,美國心理學家華萊士·蘭伯特(Wlalcae E·Lambet) 等人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出發所創立的。自20世紀80年代引進中國后,出現了不同版本的漢語術語翻譯,通過搜集文獻總結出以下3 種常見的翻譯版本。
第一種翻譯是出現在1985年祝畹瑾先生所譯著的《社會語言學譯文集》中出現的,在這本書中作者翻譯了蘭伯特的文章《雙語現象的社會心理》,在這篇文章中對于首次出現的The match-guise technique 實驗,祝畹瑾先生把它翻譯為“配對變語”的實驗方法,并說明配對變語的試驗方法比直接表態的調查表方法所得到的結果更能顯示出判斷人對于對立集團的個人反應,這種方法對測量集團的偏見特別有價值。筆者認為這種翻譯方式是把實驗內容作為主要依據的意譯翻譯方式,為了體現出該試驗是通過語言或者方言的轉換誘導出人們的語言態度。
第二種翻譯是與第一種相類似的版本,被譯為“變語配對”實驗方法,這種翻譯方式把變語作為中心語,為了體現變語是該實驗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該翻譯版本出現于1988年沙平刊登于《語文建設》的文章《“變語配對”實驗方法的應用》中。這種翻譯版本的使用頻率和第一種翻譯版本的使用頻率差不多,這兩種翻譯版本是目前大家使用最為廣泛的。
第三種翻譯方式是直譯為主的翻譯方式,The match-guise technique 實驗被翻譯為“改變裝束測試法”,最早出現于桂詩春、寧春巖等編著的《語言學方法論》一書中,該翻譯版本是直接把英語翻譯成漢語,不添加對實驗內容的解析。在該書中把實驗中涉及的法語和英語兩種變語錄音,看作兩類,一類是法語錄音,一類是英語錄音,而這些英語錄音是一種裝束。所以這種翻譯方式并沒有把語言或方言之間的轉換看成是一不同的變語,而是把成為變量的語言看成是對原始語言的一種裝束。
2 數據的收集與分析
該文通過在知網先后輸入配對變語、 變語配對以及改變裝束測試法,通過主題、關鍵詞和摘要3 種方式查找,由于改變裝束測試法通過主題、關鍵詞以及摘要等方式查找不到相關文獻,因此改變裝束測試法擴大為全文搜索。由此一共獲得44 篇文獻,通過逐一閱讀文章摘要,篩選出42 篇有效文獻,并增加5 本相關書籍,共計47 篇。
2.1 時間分布
我們可以從上圖看出20世紀80年代,中國開始出現“配對變語實驗”的身影,前期使用這種測試語言態度的研究方法并不是很多,幾乎隔幾年才出現與之相關的研究成果,但是進入21世紀以后,這種研究方法的使用頻率開始逐漸增多,幾乎每年都有與之相關的文章產出。20世紀80、90年代使用“配對變語”實驗方法的文章占總篇數的15%,21世紀至今所發表的文章占總篇數的85%,由此可見,“配對變語實驗”研究方法正在中國被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們使用與完善。
2.2 關鍵詞
研究重點。關鍵詞是作者最想表達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是文章的核心,所以通過統計關鍵詞的分布領域,我們就能得知該領域的整體研究方向了。在全部47 篇文獻中,共有67 個關鍵詞,共出現198 次,其中18 個關鍵詞的出現頻率較高。
對關鍵詞的分析可以看出以下特點:(1)配對變語和變語配對是使用頻率遠遠大于改變裝束測試法的翻譯版本。(2)語言態度與該實驗方法密不可分,同時還配合有問卷調查、訪問等方式,在關鍵詞中都有體現。(3)配對變語實驗的研究對象大多都集中在學生這一社會階層。(4)大多數文章都是對于方言與普通話之間的語言態度研究,都集中在不同方言區與普通話之間的語言態度和語言使用等,還有一小部分加入了對英語的語言態度,形成了方言—普通話—英語的多變語之間的語言態度研究。最后一種情況是對于華語及外語之間的語言態度和語言使用的研究。(5)結論導向傾向于親和力和對于地位價值的體現。

表1 關鍵詞頻率表
3 內容分析
通過分析查找的論文,我們可以了解到國內使用“配對變語實驗”的研究領域都分布在哪些方面,通過分析內容,在使用“配對變語實驗”為研究方法的文章中,我們可以把它們歸為3 種類型。
3.1 少數民族語言與漢語
在這一類型當中,“配對變語實驗” 用于測試少數民族語言與漢語,由于受試者的主體不同,其反應的結果有兩種。第一種是研究少數民族對于少數民族語言和漢語之間的語言態度、語言使用等。例如延邊的朝鮮族對朝鮮語和漢語之間的語言態度及語言使用情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土家人對土家語和漢語之間的語言態度。第二種是研究漢族(學習少數民族語言專業的學生)對于少數民族語言和漢語之間的語言態度、語言使用等。例如學習維吾爾語專業的漢族學生對于維吾爾語和漢語之間的語言態度和語言使用情況。
3.2 普通話與方言
借助“配對變語實驗”來研究普通話與方言之間的語言態度、語言使用等是目前查閱文獻中的主要部分,我們發現這些文章中研究的語言個數是不同的,把這部分文獻分為兩類: 第一類為研究對象是兩種語言的簡單變語實驗,例如,奇臺方言與普通話、托縣話與普通話、粵語與普通話、朔縣方言與普通話、長沙方言與普通話、贛語與普通話、青島方言與普通話、上海方言與普通話、四川方言與普通話、莆仙話與普通話等等。第二類為研究對象是3 種語言及以上的復雜變語實驗,例如,太原方言—普通話—英語、武漢方言—普通話—英語、惠州方言—粵語—普通話、粵語—普通話—英語、普通話—上海話—山東話、武漢話—普通話—英語、 佛山話—普通話—英語、 官話—上海話—湖州話—普通話等等。我們發現所有復雜變語研究中大多把英語作為第三種參考語言,反映出英語在中國仍是作為最主要的外語,是人們作為交際語的首要外語選擇。
3.3 漢語與外語
在這一部分研究的內容為中英或漢語同其他外語的語言態度、語言使用等等,其中單純研究漢語和英語語言態度,如,沈依青通過“配對變語實驗”誘導出部分年輕中國人對說英、 漢變語的同一說話者所持的帶有傾向性的看法。復雜的有對菲律賓華裔的漢語—英語—菲語的語言態度研究,比如,鄒曉彧和陳君楣、連榕對菲律賓華校學生的語言態度、學習動機、文化認同等的研究。還有中英語碼混用現象情況調查,有的主要按照社會層次來研究,例如,歐小艷針對90 后大學生為研究對象,使用“配對變語實驗”研究英漢語碼混用的態度,趙蕊則是以80 后為研究對象研究英漢語碼混合的語言態度。有的則是按照地域區分來研究語碼混用,例如,叢紅麗通過對上海的兩座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和上海理工大學的大學生作為研究對象,研究校園日常言語交際中漢英混用現象調查研究。其次以二語學習者為研究對象的,如,楊敏敏、毛浩然、鄭伊凡使用“配對變語實驗”研究了二語學習者的心理趨同感知對聽力習得中的效應; 陳國華也對師范院校英語專業的學生的英美英語態度、文化態度等做了研究;何文華則是通過二語學習者使用“配對變語實驗”對二語學習者的英式發音與美式發音偏好進行了調查。最后一類是對外漢語教育中,針對留學生使用“配對變語實驗”,例如,徐晴研究了對外漢語教師的口音對于留學生的不同影響。
4 結語
通過梳理國內“配對變語實驗”研究的使用情況,我們發現“配對變語實驗”在國內的發展只是基于漢語同其他方言、 少數民族語言、 外語等的變語之間的研究,我們的研究由兩個變語之間擴大到三個變語之間,甚至有四個變語之間的“配對變語實驗”,實驗在這些實踐中不斷地被完善,越來越復雜,反映出的結論也從單一的語言態度,變為語言使用、學習動機、文化認同等等不同的領域的實驗工具。
但是我們從基于漢語的方式去配合“配對變語實驗”的方法,永遠只能在不同方言之間使用,使用的領域還是十分局限的,我們需要思考的是這原本就是對于加拿大的法語人群與英語人群設計的實驗,結合中國的實際,我們都局限在了與漢語有關的內容當中,我們是否可以嘗試把“配對變語實驗”應用到周邊國家的語言之中呢?比如與我們相鄰的中亞各國,之前都是獨聯體國家,自解體之后,但俄語一直作為這些國家的通用語流傳在各個時期與階層,我們是否可以嘗試探索中亞國家對于本國語同俄語之間的語言態度呢? 這就是筆者寫這篇研究綜述的目的,希望我們的研究維度更加寬廣、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