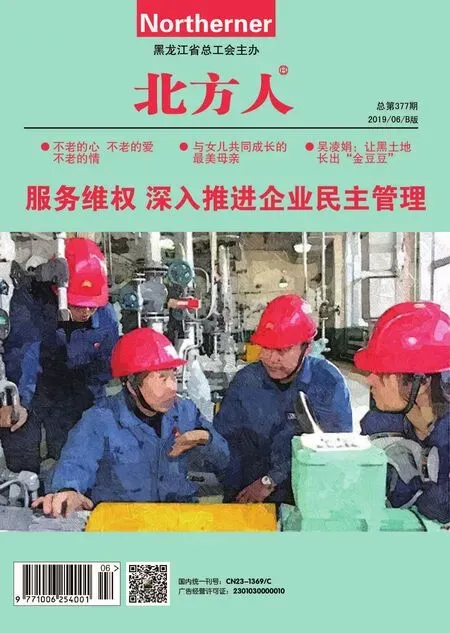春天里的父親
文/熊興國

有些記憶,早已不復存在,而有些記憶卻越來越深刻。
在農家,犁,耙和牛總是不可或缺的,而與之打交道最為密切和頻繁的就是男人,也就是孩子的父親。
我從小就放牛,因此和父親成了“搭檔”,尤其是入春之后,這對“搭檔”就更頻繁地出入在田間地頭。我牽牛在前面,父親就扛著犁在后頭,也順便幫我趕那頭“倔強”的老水牛。
到了地里,父親就拉開架勢,很熟練地給牛套上繩子,掛上牛軛,之后就會發出“溝”“踩邊”“縮”等詞匯。別奇怪,那些都是農家人犁地的時候對牛“命令”的話,無非就是讓牛跟著犁過的溝或者踩在坎子邊走,“縮”自然也就是叫牛倒退的意思。
父親犁了地,我也不清閑,多半都會去地頭割些青草回來,等父親停下來吸煙的時候,我便會將自己割的草去喂牛。那種感覺無比高興,看著牛一口一口的吃著青草,就如同自己獲得了某種“功績”一樣。
那個時候,很多農家犁地和耙田都實行換工,說白了就是今天你幫我家犁地,明天或改天我再給你家耙田。按理說跟著放牛我也是一分子,可到了晚上吃飯的時候,父親卻不同意我跟他一起去客家吃飯。
可能是嘴饞的原因,所以很小的我就想學犁地和耙田,要知道,只要可以單獨掌牛,就可以換工,也就能“名正言順”地到客家去吃飯。可是“好學”的我卻遭到了旁人的嘲笑:“你還沒有犁高,還犁什么地哦。”只有父親很嚴肅:“你要去上學,現在不學,啥時候才學啊!”
后來我上了學,田間地頭的那對“搭檔”不見了,上學路上卻多了一對“搭檔”。從我家到學校有五公里,當時村里在那所學校讀書的就只有我一個人,所以父親就每天早上送我上學,拿一把火把或者打著手電筒。父親總是先把我送到學校,再回來去地里勞作。這種方式一直持續到三年級,有高年級的同學轉到我讀的那所學校,我自然也就有了新的同伴。
其實一直忘了說,那時我家特別困難。難到什么程度,我只能說,每年的二三月份,家里就完全斷了糧。接下來的日子就全靠父親一個人去山里找一些野菜和野果回來糊口。我記得父親挖得最多的就是山藥,大則手腕粗,小的有如鐮刀柄一般。用刀削去皮,洗凈,和水一起下鍋,再加點野菜,就成了一家人的晚飯。當然在削皮下鍋之前,父親定會單獨揀幾節出來,那是專門為我留的。將山藥往火坑里埋起來,一盞茶的工夫再掏出來,剛剛好,或者酥軟,或者已經起了幾塊干巴,用刀或竹片輕輕刮去表面的灰和泥土,再用嘴吹吹,就成了我的“零食”,或是某頓“中午飯”。
父親的點滴仍記憶猶新,只是多年前,父親已永遠沉睡在了春天里。正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孝而親不待,在這個春花燦爛,萬物蓬生的季節里,但愿父親在另一個世界,一切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