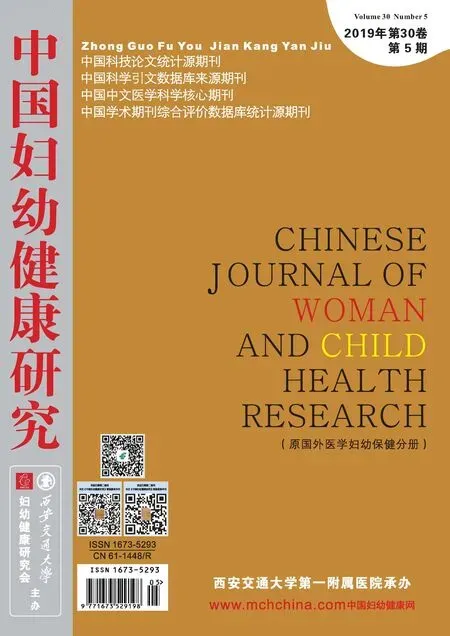嬰兒初發重癥先天性梅毒的死亡相關因素分析
杜偉江,姚愛媛
(永康市婦幼保健院,浙江 永康 321300)
先天性梅毒為梅毒螺旋體經母體胎盤傳染給胎兒,進而導致胎兒多系統感染,是一種危害嚴重的疾病,早期確診并積極干預可改善患兒預后[1-2]。近幾年我國先天性梅毒的發病率呈上升趨勢,臨床對先天性梅毒的預防及母嬰阻斷廣泛關注。尤其是晚發型嬰兒梅毒,起病比較隱匿,而且有多種臨床表現,若不及時控制病情或造成誤診漏診則會嚴重危害嬰兒的健康[3]。為此,本研究對嬰兒初發重癥先天性梅毒的臨床各項特征進行詳細分析,分析其發病影響因素及病死危險因素,為該病的診斷提供有價值的參考,現報道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臨床資料
收集永康市婦幼保健院2012年3月至2017年11月確診為初發先天性梅毒的80例嬰兒作為研究對象,將研究對象按2015年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性傳播疾病診斷和治療指南”[4]病情程度分級標準劃分為重癥組和普通組,其中重癥組35例,男15例,女20例,平均年齡(2.05±1.12)個月;普通組45例,男21例,女24例,平均年齡(3.35±1.42)個月。先天性梅毒診斷標準參照2015年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性傳播疾病診斷和治療指南”[4]:①具有2個以上提示先天性梅毒的癥狀及體征;②血清檢測中快速反應素試驗(rapid plasma regain,RPR)和梅毒螺旋體血凝試驗(treponemal hemagglutination test,TPHA)均陽性;③存在多臟器受損狀況。所有入組患者均自愿簽署知情同意書,本研究通過本院倫理委員會審查并批準。
1.2方法
對所有患兒進行胸部X線或CT檢查、腦脊液檢查、顱腦超聲、眼底和腦干聽覺誘發電位等,以對其重要臟器功能進行評價。記錄患兒的喂養方式、出生體重、發育是否遲緩、患兒來源、發病時間等。尋找重癥組發病影響因素。其中發育遲緩選取Gesell發育診斷量表評價,總分≤69分定義為智能發育障礙。
對患兒采取驅梅治療,有并發癥者相應地采取對癥處理,根據預后情況將重癥組患兒劃分為死亡組和生存組,分析死亡危險因素。
1.3統計學方法

2結果
2.1重癥組患兒器官功能障礙情況
本研究中,重癥組患兒皮膚黏膜損害的發生率最高,為85.71%,其次是胃腸功能損害,為57.14%;骨和關節損害發生率最低,為11.43%,見表1。
2.2重癥組患兒發病的單因素分析
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年齡小(t=4.45,P<0.05)、早產兒(χ2=4.90,P=0.03)、農村來源(χ2=7.32,P<0.05)、發病時間較長(t=13.53,P<0.05)為重癥組患兒發病的相關因素,而與性別、喂養方式、出生體重、發育遲緩等無關,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見表2。
表1重癥組35例患兒器官功能障礙情況[n(%)]
Table1Organdysfunctionof35casesinseveregroup[n(%)]

器官或系統損害例數皮膚黏膜30(85.71)胃腸道20(57.14)肺臟18(51.43)心臟14(40.0)神經系統8(22.86)腎臟6(17.14)血液系統6(17.14)骨和關節4(11.43)



因素重癥組(n=35)普通組(n=45)χ2/tP性別 男15(42.86)21(46.67)0.120.73 女20(57.14)24(53.33)年齡(月)2.05±1.123.35±1.424.450.00早產兒 是20(57.14)36(80.00)4.900.03 否15(42.86)9(20.00)喂養方式 母乳11(31.43)16(35.56)0.150.699 人工24(68.57)29(64.44)出生體重(kg) ≥2.512(34.29)23(51.11)2.270.13 <2.523(65.71)22(48.89)發育遲緩 是32(91.43)35(77.78)2.700.10 否3(8.57)10(22.22)患兒來源 農村30(85.71)26(57.78)7.320.01 城市5(14.29)19(42.22)發病時間(d)12.35±1.126.39±2.4113.530.00
2.3重癥組患兒死亡危險因素分析
對35例重癥組患兒進行死亡危險因素分析,根據預后情況將重癥組患兒劃分為死亡組和生存組,納入死亡組的有6例,病死率為17.14%,生存組則為29例。對患兒死亡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結果顯示,早產兒(χ2=6.62,P<0.05)、出生體重(χ2=9.86,P<0.05)、機械通氣(χ2=15.86,P<0.05)、器官功能障礙(χ2=46.56,P<0.05)為重癥組患兒死亡危險因素,見表3。
2.4影響重癥組患兒死亡的二元Logistic多因素回歸分析
以篩選出的是否早產兒、出生體重、是否機械通氣、是否器官功能障礙作為自變量,以患兒生存結局作為因變量,多因素回歸分析結果顯示,早產兒、出生體重、機械通氣、器官功能障礙均不是影響重癥組患兒死亡的獨立影響因素,見表4。
表3重癥組患兒死亡危險因素分析[n(%)]
Table3Analysisoftheriskfactorsofdeathinseveregroup[n(%)]

因素生存組(n=29)死亡組(n=6)χ2P性別 男14(48.28)2(33.33)0.450.50 女15(51.72)4(66.67)早產兒 是21(72.41)1(16.67)6.620.01 否8(27.59)5(83.33)喂養方式 母乳11(37.93)2(33.33)0.050.83 人工18(62.07)4(66.67)
(轉下表)
(續上表)

因素生存組(n=29)死亡組(n=6)χ2P出生體重(kg) ≥2.526(89.66)2(33.33)9.860.00 <2.53(10.34)4(66.67)發育遲緩 是22(75.86)5(83.33)0.160.69 否7(24.14)1(16.67)患兒來源 農村20(68.97)4(66.67)0.010.91 城市9(31.03)2(33.33)機械通氣 是03(50.00)15.860.00 否29(100.00)3(50.00)器官功能障礙 2個19(65.52)1(16.67) 3個5(17.24)2(33.33)46.560.00 3個以上5(17.24)3(50.00)

表4影響重癥組患兒死亡的二元Logistic多因素回歸分析
3討論
3.1嬰兒重癥先天性梅毒的臨床特征
近年來國內先天性梅毒發病率急劇增長,Zhang等人[5]分析了中國大陸在2005—2012年這一時間段首發、再發及3次復發的梅毒患者臨床資料,發現從2005年到2012年我國梅毒患病率增加了3倍,梅毒螺旋體可以由母體經胎盤傳染胎兒,新生兒及嬰兒患梅毒的幾率也隨之增加。孕婦感染梅毒后倘若沒有采取科學治療,相關數據顯示40%的胎兒會發生不良妊娠結局,如自發性流產、死胎[6]。而且嬰兒梅毒會出現多器官或系統損害,例如皮膚損害,主要以紅色斑丘疹或脫屑為臨床表現,重癥者會發生肝臟損害,以黃疸、肝酶升高、肝脾增大及膽紅素升高多見,其他梅毒相關性損害還包括骨關節畸形、血液系統損害、呼吸系統損害、耳聾、消化系統損害、心臟損害、神經系統損害等[7-8]。本研究結果顯示,嬰兒初發重癥先天性梅毒器官功能障礙中以發生皮膚黏膜損害的發生率最高,為85.71%,其次是胃腸功能損害,為57.14%。骨和關節損害和血液系統損害發生率最低。相關學者表示,新生兒梅毒器官功能障礙主要以肝損害及骨和關節損害為主,發生率均超過60%[9]。雖然先天性梅毒危害嚴重,但孕婦接受規范的青霉素驅梅治療能夠預防98%該疾病的發生[10-12]。
3.2發病相關因素分析及防治措施
本研究對重癥組患兒發病相關因素進行分析,發現嬰兒初發重癥先天性梅毒發病與年齡、是否早產兒、患兒來源及發病時間相關。早產兒免疫力功能較弱,心肺功能不良,所以發生梅毒的風險較高。農村患兒較城市更容易發生梅毒,農村就醫環境差,醫療條件有限,孕婦文化程度低,健康意識淡薄,耽誤了患兒就醫時間,以至于病情難以及時控制。本研究中嬰兒初發重癥先天性梅毒發病與性別、喂養方式、出生體重、發育遲緩等臨床表現無關。但英國學者Simms等人[13]研究顯示,先天性梅毒發病和出生體重相關。而且,學者Cardoso等人[14]表示妊娠婦女所處的社會環境和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影響先天性梅毒的發生率,一些患兒母親年齡較小、吸毒及性生活混亂,性安全意識薄弱,健康保障條件缺乏,以至于先天性梅毒嚴重威脅正常妊娠。本研究對重癥組患兒的死亡危險因素進行分析,發現早產兒、是否機械通氣及合并多器官功能障礙是嬰兒初發重癥先天性梅毒的死亡危險因素,提示在重癥先天性梅毒治療期間需關注多器官功能障礙這一臨床特征。考慮到本研究納入的研究對象有限,有待進一步增加樣本量完善結論。
現如今,先天性梅毒有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轉移的趨勢,一旦先天性梅毒患兒沒有在第一時間內沒有得到診斷及治療,其原本隱匿的癥狀和體征會進一步加重[15]。所以,臨床上需要對患兒進行常規RPR篩查,肝功能、腎功能及心肌酶譜等檢測評價重要臟器功能情況,實現早期診斷,并采取針對性治療。對于可疑神經系統并發癥患兒需采取影像學及腦脊液檢查,及時發現腦炎或神經梅毒,降低漏診率和誤診率[16]。對于懷疑骨和關節損害患兒應該進行關節磁共振或X線檢查,以早期治療。對孕早期婦女需進行梅毒血清學篩查,以免漏診,對于產前確診梅毒病原體攜帶的妊娠婦女需要加強孕產期檢查,加強母嬰保健知識教育,尤其是加強農村婦女生殖健康知識教育,普及產前檢查,開展孕婦梅毒的篩查和新生兒的監測工作,減少嬰兒梅毒的發生,改善妊娠結局。
綜上所述,嬰兒初發重癥先天性梅毒的臨床特征主要是皮膚黏膜損害和胃腸功能損害,嬰兒初發重癥先天性梅毒發病和年齡、早產兒、患兒來源、發病時間有關,早產兒、是否機械通氣、器官功能障礙為重癥患兒死亡危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