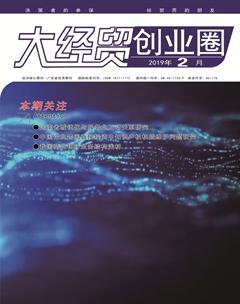透視我國代孕合同的司法需求
吳琳玲
【摘 要】 代孕是一個需要嚴肅對待的社會現象,我國對代孕技術的應用是不支持,卻也未用法律明確代孕等輔助行為的違法性。這種法律“真空”下,代孕已成為一個無法管控的暴利黑色產業。在現代社會科技進步的背景下學界認識到約束代孕行為的必要性,更加關注到解決此類案件實際追求的公平。本文在分析案件判處結果的基礎上,提出幾點涉及代孕的司法需求。
【關鍵詞】 代孕 代孕合同 立法
一、代孕的社會現狀與立法問題
(一)社會現狀
儒家傳統文化根植至今千年不朽,如宗族血親的重大責任為首就是“傳宗接代”“天倫之樂”,從閉塞落后的村莊“買妻”到紙醉金迷的城市“養小三”,求子傳承現象屢見不鮮。隨著科技的發展,人工輔助生殖技術進入了社會市場,也一腳踩上了人倫道德和法律領域的邊界,其中試管嬰兒已被國家所認可,而代孕在法律上仍“諱疾忌醫”。
持支持的觀點在于代孕是生育權和隱私權的延伸,即生育權的內容應當隨著社會發展和生育政策調整而拓展,且認定生育方式的選擇純屬個人隱私權的范疇,國家無法過多干涉。但應當明確基于權利進行立場站定,也會因權利不甚具體的法律內涵而產生爭議。反對派則認為代孕視女性為生育機器,把人類當工具使用是在踐踏人格尊嚴。如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在判決著名的“客體公式”:當一個具體的個人被貶抑為課題、僅是手段或可替代之數值時,人性尊嚴已受傷害。然而,無論是完全代孕還是部分代孕,其本質都是借用(無償代孕)或者租用(有償代孕)女性身體的一部分,這就是將女性的身體工具化,甚至是商業化,貶損了代孕女性人格尊嚴。
(二)立法問題
目前我國代孕的態度還是抵制的。衛生部2001年頒布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第三條規定:“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不得實施任何形式的代孕。”第二十二條規定:“對實施代孕技術的醫療機構,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衛生行政部門給予警告、三萬元以下罰款,并給予有關責任人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責任。”2015年6月份各個省市的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印發了“打擊代孕專項行動方案”,同年12月27日通過了《中國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正案)》卻又刪去了“禁止代孕”的相關條款。對于國家來講,人口問題一直是國家大計,從原先的獨生子女政策到如今的二胎開放鼓勵,可見人口減少失衡嚴重。關于代孕的文件散見于部門規章和政府工作文件中,這些僅有行政規章,不能形成規范的法律規范體系,與其他部門法中的有關規定不能很好的銜接,顯然與其重要地位不相符,難以起到應有的保障作用。
國內立法現狀在代孕方面是缺乏的,存在很多問題:一是立法步伐緩慢,實踐當中涉及案件不少,卻仍未有法律及時調整和規范;二是制定的行政規章效力較低,發揮的作用也是很有限的,況且至今沒有相關的法律或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等出臺,以支撐這些行政規章,它們的效力猶如空中樓閣,無法落于實際;三是僅有行政規章,沒有形成一定的法律規范體系,與其他部門法中的相應規定不能很好的銜接,顯然與其重要地位不相符,難以起到應有的保障作用。雖有正當性,但執行起來很是困難;四是缺少專門的管理機關,同其他機關的行政管理通病一般,哪個行政部門負責管理,如何管理并沒有做出明確的規定,權責也不明確,實際的管理效果必然不佳。
二、代孕案件分析
科學技術的雙重性本就是一把“雙刃劍”,代孕技術亦不例外。現今的技術要為人類發展貢獻力量,需要得到正確的對待,而不是盲目的禁止。關于代孕合同的效力以及代孕行為本身,我國還未用以法律確認或者予以禁止。查閱近年來我國各地法院審理的代孕案件,可得出現今法律主流的立場。選取了四個案件,分別是08年廣西南寧市江南區法院、10年的廣東佛山市順德區法院和湖南常德市鼎城區法院、12年福建廈門市思明法院,除了湖南一案是妊娠型案件外,其余三件是基因型代孕案件(即所需卵子來自于代孕母,所生孩子與代孕母有生物學上的親子關系)。
從上述裁判結果來看,妊娠型案件中的代孕協議有效,而基因型案件都以代孕協議違反公序良俗原則認定無效。總體來看代孕協議的主流觀點是,法院認為基因型代孕協議中,因嬰兒同代孕母有血緣關系,代孕母等同于將自己的親生孩子賣給他人,顯然是具有了販賣人口的色彩,雖然代孕母自身或許不這么認為,但這確實是社會上很難被容忍的。反觀,妊娠型代孕中,認定協議合法的依據在于代孕母出售的是服務,而不是嬰兒。既然實踐中的處理方式已經出現,將“妊娠代孕”(完全代孕)納入法律規制的范疇予以合法化,才是解決問題的最佳途徑。
三、司法應何為?
對代孕合法化最有吸引力的辯護是一種法律經濟學的分析,即基于傳統道德倫理和公序良俗等“常識”的代孕管制是沒有效率的,它無法禁絕代孕行為,與其如此 ,還不如“去管制化 ”,放開代孕并承認代孕協議的可執行性。有社會民意調查顯示,代孕的支持率與被采訪者所處城市的開放性程度、受教育程度成正比, 與受訪者年齡成反比。可以預測,隨著時代的更迭和思想的開放,社會對于代孕的接受度會逐漸提高,也不是竭力抵制。
基于以上這些分析,本文認為因自然生殖困難而求助于代孕的社會現象,合理的做法并不是一味禁止,應是“變堵為疏”。在立法上:一是應將“妊娠代孕”定位為生育的輔助手段,將代孕限制在有限的范圍內;二是明確“妊娠代孕”協議的性質是屬于人身關系方面的委托代理合同,而不是所謂了“人口買賣交易”,代孕行為的客體是代孕母代替他人生育的行為;三是確認代孕協議的效力,但這個協議的效力要經有關部門核準登記后才具有法律效力;四是規范協議的內容,用法律的方式確定下雙方的權利義務。因為這種協議具有人身性,不可強制履行,法律可以規定一定數額的金錢處罰的方式來“迫使”代孕母履行義務。
【參考文獻】
[1] [美]斯蒂文·沙維爾:《法律經濟分析的基礎理論》,趙海怡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2] 周平:“有限開放代孕之法理分析與制度構建”,載《甘肅社會科學》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