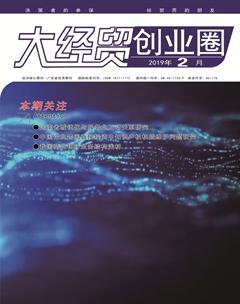對《票據法》五十二條“其”字所指代分析
蒲三林
【摘 要】 對《票據法》第五十二條中“其”字所代指,學界有不同的認識,有學者認為該“其”字代指持票人,亦有學者認為該“其”字代指被保證人。本文通過論證保證人追索權與再追索權的邏輯關系,并采用文理解釋、目的解釋、比較解釋以及體系解釋的解釋方法,對該“其”字進行論證分析后,認為該“其”字應代表被保證人。此外,在承接前述的論證理由的前提下,為符合保障交易便捷的立法目的,繼續提出保證人的再追索權的行使對象不應當包含其他共同保證人,且須從權利行使對象,順序以及權利內涵三個角度區分保證人的再追索權與《票據法》第六十八條所規定的一般再追索權。
【關鍵詞】 票據法五十二條 被保證人追索權 再追索權
一、追索權概述
追索權是票據權利中的第二次權利,是《票據法》為持票人所創設的救濟性權利,其行使的前提為持票人向付款人(或承兌人)行使付款請求權失敗,其行使的對象為持票人及其前手,其行使的內容為請求償還票據上所載金額及其他相關金額。
(一) 追索權的特征
1.連帶性
《票據法》第六十八條1規定匯票的出票人、背書人、承兌人和保證人對持票人承擔連帶責任,即為追索權連帶性的體現。
2.任選性
此為票據法追索權所獨有特征,追索權不限定唯一主體,只要符合條件,持票人可以向一人甚至數人行使追索權。此外,依據《票據法》六十八條第三款規定,追索權不僅可以同時多向追索,而且可以不同時再次多向追索,只要票據債權未足額實現,不論追索進行到何種程度,持票人可以對其他義務人追發行使新一輪的追索權。
3.代位性
《票據法》第六十八條第三款規定體現了追索權的代位特征。持票人向義務人行使追索權滿足后,該追索權不會消滅。只要未至出票人最終清償債務,相同內容的追索權可以在票據法律關系鏈條上的在不同主體之間轉讓變更,依次傳遞,更迭行使。
4.繼承性
保證人再追索權在權利承繼上的限制性,由此得出保證人追索對象的范圍不應優于被承繼者,即被保證人追索權行使對象的范圍不得大于其承繼對象。
二、對《票據法》五十二條2“其”字的理解
《票據法》第五十二條其本質是對保證人追索權的規定,但由于五十二條在法條中使用了“及其前手”帶有模糊語義的四個字,所以使得法律人在適用法律時對“其”字所代指的內容發生了疑問,故而本文通過欲通過結合《票據法》中其他法條對追索權的規定進行論證以澄清五十二條“其”字所指代之意。
(一)從再追索權角度解釋“其”字含義
1.被保證人的再追索權與代位權的關系
保證人是因保證被保證人而存在,故其責任與義務來源應當是同一的。換而言之,一旦當保證人因被追索而履行自己的保證義務之后,則意味著被保證人對已行使追索權的持票人的票據責任也應當同時解除,因為保證人對持票人所履行的保證義務其實質上應當等同于被保證人對持票人的所負有票據責任,被保證人對其后手的票據責任與持票人對其前手的權利,基于權利、義務性質的統一性,同理可證,都應當因為保證人履行義務而消滅。與此同時,保證人則因為自己承擔了保證責任并依據《票據法》五十二條產生并享有了保證人的追索權[1]。
從本質上來講,再追索體現權利的代位行使,即債權的讓與[2]。對于保證人而言,行使保證人的追索權的其本質亦為同樣,即如果持票人追索權行使的對象為被保證人,則保證能可獲得向其前手行使再追索權的資格,而又因為保證人是代替被保證人承擔票據責任,所以保證人所獲得的再追索權的行使對象應當為被保證人行使再追索權的對象,保證人所享有的再追索權與被保證人享有的再追索權應為承繼的同源關系。
此外,在票據法律關系鏈中除出票人是絕對義務人、最終持票人是絕對權利人以外,中間的背書人皆為權利人與義務人的統一體,并且是前手為后手義務人。因此,從票據法中債權人與債務人的身份混同的角度觀之,亦可得知,《票據法》六十八條中規定的保證人所享有的與持票人同一的債權應當是指持票人,即上任追索權人對被保證人的票據債權。
綜上,不論是保證人代位行使持票人的債權還是持票人自行行使該債權,都只能由該債權的義務人來完成。而被保證人是持票人的義務人,被保證人的義務人依據代位的含義同樣可以視為持票人的義務人,但是持票人的義務人與被保證人的義務人并非同范圍的概念,基于代位實現債權的邏輯含義可以得知,《票據法》五十二中的其字應指被保證人。
(二)從法律解釋角度解釋“其”字含義
為論述方便,本文特舉一例,如下所示:
A為出票人B、C、D、E(X、R)、F、G、H為連續背書人,M為最終持票人,Z為承兌人,X、R為E的共同保證人。
1.文理解釋
受限于追索權只能逆向追索前手的規定,可以向持票人X可以行使持票人F對被保證人E以及持票人前手F的A、B、C、D、E的追索權,但被保證人E已經是追索權的行使對象,因此無需在法條中贅述。
2.目的解釋
保證票據的流通性,保障交易的迅速便捷與安全,這是票據追索權的應有目的,但是同樣當發生追索之后,迅速指向出票人消滅債權也應該是票據追索權的目的之一,因此一旦發生承兌不能時,迅速讓索賠方向指向承擔該票據法律關系鏈上絕對義務的出票人也當是設計追索權需要考量的目的之一。因此追索權不能無限擴張,應當限制追索權的行使方向,避免形成首尾相連、周而復始的追索循環圈,提升問題的處理效率。
3.比較解釋
對于追索權的限制,各國皆有法例可尋,如在我國臺灣地區《票據法》第 100 條第 3 項規定:“背書人為清償時,得涂銷自己及其后手之背書”,涂銷被追索人后手,避免自己再陷追索之風險,就是對追索權限制的側面印證。[3]
4.體系解釋
票據保證人的追索權其本質上為再追索權的一種,故應受再追索權的限制,此已無疑義。但是問題在于《票據法》五十二條中“可以行使持票人對被保證人及其前手的追索權”中“其”是指上一任追索權人即持票人還是被保證人,學者間有不同看法,本文認為應指被保證人。依據《票據法》第五十條規定規定可知3,保證人與被保證人為同一責任,既然是同源義務,那么也應當享有同一權利,因為保證人履行了保證責任,因此代替了被保證人在票據法上的地位行使追索權,因此只能像被保證人前手追償。
三、對保證人追索權的建議
(一)保證人再追索權行使對象的限制
《票據法》第五十一條中多個保證人之間的連帶責任是指持票人基于二者之間相互承擔連帶責任而可以任意向R、X之間主張票據權利,還是指當其中一人承擔保證責任后,可以向為承擔保證責任的其他共同擔保人追償。
本文認為保證人的再追索權的行使對象不應當包含其他共同保證人這種解釋最為適宜。從本質上來說,保證人并不背書人一樣為票據的流轉支付過應有對價,因此也就不像其他背書人一樣因取得票據而獲得相應利益,保證人的本質是擔保債的履行,但是倘若持票人憑己之愿只選多個保證人中一人行使追索權,那么其他保證人應當內免除相應范圍內的保證責任,對于履行了保證責任的持票人而言,即使行使《票據法》五十二的權利,也不能其他共同保證人追償自己已經履行的保證債務。這既是保證人對自我風險的負擔,也是為了讓追索盡快指向出票人,徹底消滅債權的應有之義。否則,將會陷入以下循環追償的情況,如上例中,R、X分別向對方追償50%擔保責任,從實質上來看,即便二人相互追償成功,但是自己依然還是承擔著50%的擔保責任,依然還學向被保證人及其前手繼續追償,如此既浪費當事人自己的時間亦浪費了司法資源。
此外,在遵從體系解釋的角度,既然認為《票據法》第五十二條“其”字代指被保證人,那么意義為這保證人的再追索權的對象應當為被保證人及其前手,從文理解釋角度看,該前手的內涵不應當包括被保證人的其他保證人,所以,保證人再追索權的行使對象不應當包含該同一位置的其他保證人。
(二)區分保證人再追索權與一般再追索權
在此基礎上,保證人再追索權與《票據法》第六十八條所規定再追索權權利在行使對象,順序以及權利內涵三個角度皆有不同。當保證人因履行保證責任而成為持票人時,保證人并不能依據《票據法》第六十八條向匯票債務人任意行使追償權,如前所述,其再追索權受到權利承繼等限制。
此外,亦有保證人作為出票人情況,如果持票人向作為保證人的出票人要求其履行保證責任時,對于出票人而言,則不應當賦予其享有《票據法》五十二條所含權能的追索權,因為當出票人承擔足額、充分、完整的保證責任之后,實質上整個票據法律關系的債權都已經得以清償和消滅,雖然保證人責任具有獨立性,但是其也具有從屬性,故再次賦予出票人追索權其本質為循環追償。因此依據保證人在票據法律關系中的不同地位,應當賦予其不同的追索權內涵。
因此,保證人再追索權雖然脫胎于一般再追索權權,但是不同于一般追索權,故而應對此二權利進行區分以正視聽,以便實踐。
【注 釋】
1 《中華人民共和國票據法》第六十八條 匯票的出票人、背書人、承兌人和保證人對持票人承擔連帶責任。
2 持票人可以不按照匯票債務人的先后順序,對其中任何一人、數人或者全體行使追索權。持票人對匯票債務人中的一人或者數人已經進行追索的,對其他匯票債務人仍可以行使追索權。被追索人清償債務后,與持票人享有同一權利。
3 《中華人民共和國票據法》第五十二條 保證人清償匯票債務后,可以行使持票人對被保證人及其前手的追索權。《中華人民共和國票據法》第五十條 被保證的匯票,保證人應當與被保證人對持票人承擔連帶責任。匯票到期后得不到付款的,持票人有權向保證人請求付款,保證人應當足額付款。
【參考文獻】
[1] 于瑩.票據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2):177
[2] 江平.民法學[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11(4):419
[3] 周東威.票據追索權問題研究[D]. 吉林大學, 2016(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