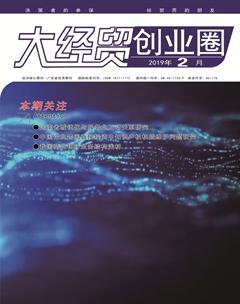《攝大乘論》遍計所執性辨析
董衛昌
【摘 要】 唯識三性是唯識學重要思想,但因為依他起性和圓成實性非凡夫能見,唯遍計執為凡夫所見,因此遍計所執自性是人認識唯識三性的基礎。眾多經論中,但遍計所執具體是什么?又是為何成為凡夫的 認識的,本人以《攝大乘論》為參考對此進行詳細辨析。
【關鍵詞】 唯識三性 遍計所執自性 名義關系
唯識三性說是唯識學中重要思想內容,眾多唯識學經論都對此有所論述,其中《攝大乘論》對此的論述最為詳細,并具有其自身特點。《攝大乘論》對唯識三性的論述強調以依他起為中心,并認為唯識三性關系是非一非異,只是從不同角度理解諸法體相。該論認為依他起相為阿賴耶識種子所生虛妄分別所攝諸識,展開就是十一種識,而遍計所執相則是對依他起相似義顯現,非真實境,圓成實相則是依他起相上遍計所執相永不顯現性。但對于凡夫而言,不能見依他起相,也不能見圓成實相,因此只能見遍計所執相。遍計所執相其具體內容是什么,又是如何成為人的認識呢?本人即以《攝大乘論》為中心詳細辨析遍計所執性。
《攝大乘論》認為依他起諸識的似義顯現即為遍計所執相,但問題是依他起諸識都是唯識無義,都是由阿賴耶識所變現,其本身并無恒常自體,諸識又怎么能顯現為遍計所執呢?《攝大乘論》云:“若遍計所執自性,依依他起,實無所有,似義顯現,云何成遍計所執?何因緣故名遍計所執?無量行相意識遍計顛倒生相故,名遍計所執;自相實無,唯有遍計所執可得,是故說名遍計所執。”①
真諦所譯《攝大乘論》將遍計所執自性譯為分別性。此分別性即意識周邊計度分別,由此意識對諸識進行分別就有了各種好像真實的外境顯現,但此分別不離諸識,所以說顛倒生相。此顛倒生相其自性非真實,唯有周邊計度的分別可得。分別是說區分不同事物的功能,分別性則包含了能分別、所分別,此能、所有主動意味。但遍計所執性強調周遍計度意,顯示了意識分別作用的被動性,這與真諦譯分別性還是有所區別的。從對依他起性的似義顯現角度出發,遍計所執性隱含了被動的意味,對于凡夫而言,無可避免地只能通過意識作用得見諸法遍計所執性。
“遍計所執自性”表達了“能遍計”、“所遍計”的關系,《攝大乘論》說:“當知意識是能遍計,有分別故。所以者何?由此意識用自名言熏習為種子及用一切識名言熏習為種子,是故意識無邊行相分別而轉,普于一切分別計度故名遍計。又依他起自性,名所遍計。又若由此相,令依他起自性,成所遍計,此中是名遍計所執自性。”②
意識的分別作用的被動性是因為其自身也是其阿賴耶識種子所生。意識分別時,其能分別熏習成見識種子,其所分別對象色等熏習成相識種子,因此一切法得以生起。意識的分別作用遍于一切識,就整體而言是對依他起相諸識進行遍計,所以說意識是能遍計,依他起是所遍計。意識分別作用最終讓依他起自性顯現為遍計所執自性。此過程,《攝大乘論》進一步說:“謂緣名為境,于依他起自性中取彼相貌,由見執著,由尋起語,由見聞等四種言說而起言說,于無義中增益為有。由此遍計能遍計度。”③
能遍計的意識以名言即語言為所緣對象,此名即依他起自性所立。意識分別時,就在依他起名上取與之相應之相貌。對此名和相貌的一致性判斷即是見,以此為執著確定此名、此相相對應。對此執著進行尋伺即反復思考探究時,就形成種種能表達的語言。語言言說之內容為見聞覺知,見是眼見色,聞是耳聞聲,鼻、舌、身覺香味、觸,意識知法。這樣意識的遍計已經達成,對于依他起無義諸識確定為有。遍計所執自性就是認為諸法有如是名,即有如是義。
《解深密經》中,直接將遍計所執自性命名為假名安立自性:“云何諸法遍計所執相?謂一切法假名安立自性差別,乃至為令隨起言說。”④
《解深密經》是說遍計所執性就是將一切法借助名言確立其有不同的自性差別,以及根據其所演化的所有語言、概念、理論等。《攝大乘論》說意識通過語言的分別作用,從而將依他起相的虛妄分別確立為有真實境界的對象。
《攝大乘論》又對遍計所執性進行分類,如果分為兩類則為:自性遍計所執和差別遍計所執。自性遍計是對于諸法之間的區別的認識和確認;差別遍計所執則是對同一種法的不同功用差別的認識分別。
進行進一步細化可有四種。《攝大乘論》如是描述:“一自性遍計,二差別遍計,三有覺遍計,四無覺遍計。有覺者謂善名言,無覺者謂不善名言。”⑤“有覺遍計”和“無覺遍計”的差別主要是是否善于利用名言概念去認識事物。有覺遍計就是善于利用名言概念,無覺遍計就是不善于利用名言概念。如人和動物而言,人認識事物就是“有覺遍計”,動物則是“無覺遍計”。進一步說,即便是人,成人對于名言概念的運用強于嬰兒,受過教育的人更善于利用名言概念。此處語言不但是指人類語言文字,也包括其他有情所使用的語言,但是其他有情對于語言的應用比不上人類,相對而言稱之為“無覺遍計”。“無覺遍計”并非不利用語言,只是意識分別作用不夠強大,對諸法的理解停留在感受上,還沒有進入理性分析階段。
四種遍計之有覺遍計和無覺遍計只是對于自性遍計和差別遍計的進一步說明。四種遍計的分類并非是相互獨立的分類,自性遍計和差別遍計都有“有覺遍計”和“無覺遍計”兩種情況。人的知識結構越復雜,名言概念就會越來越多,就更加“有覺遍計”,對于事物的認識越清晰,其遍計所執的程度反而是越深的,當然,對于遍計所執的理解也會逐步加深。從另外一個角度講,如果對遍計所執不能覺察,對于去除遍計所執也是很困難的。
對遍計所執進行更深入的分析,意識的分別作用實質上是通過名義關系完成的。《攝大乘論》說:“如是遍計復有五種。一依名遍計義自性,謂如是名有如是義。二依義遍計名自性,謂如是義有如是名。三依名遍計名自性,謂遍計度未了義名。四依義遍計義自性,謂遍計度未了名義。五依二遍計二自性,謂遍計度此名此義如是體性。”⑥
不管是自性遍計、差別遍計或者有覺遍計和無覺遍計,都可以從五種名義關系來理解。名為能詮即能表達事物的語言,義為所詮,即所表達的對象、事物。
“以名遍計義自性”,就是聞名生義,意識緣名時,就以此名來理解事物,就認為此名能夠完全詮釋所對應義,將名和所指代的事物一一對應起來。這是基于對和義都清晰的狀況下,意識所進行的遍計。這也是一個正常人的基本認識功能,如聽到“杯子”的名,意識分別作用馬上判斷將杯子此名與對應的那個被命名為杯子的事物對應起來。如果將名義關系運用到對五蘊之認識,那么聞色名就認為“色”此名能夠表達色法,受、想、行、識也類似。更推進一步,就認為十八界跟、塵、識名能夠表達其相應義。
“以義遍計名自性”,與“依名遍計義”相反,此為意識以“義”為所緣對象,認為有此義只能用其所對應的名來表示,而不能用其他名表示,其實質是認為名存在獨立真實自性。如認為“色法”的現象必然只能用色名來表示,不能用受、想、行、識名表示。
“以名遍計義自性”和“以義遍計名自性”兩者都是對于已經明了的名和所對應事物的意識分別,它們構成了名和義一一對應的關系。在確定的語境之中,名與義的對應不能替代。如說色名和對應色法,不能用受名來對應色法。針對具體事物而言,如電腦名對應電腦這個現象和事物,不能用杯子來對應電腦這個事物。
“以名遍計名自性”,就是對于一個不知道“義”的名進行遍計,試圖用其他已知義的名言概念來解釋此名。無性注說:“謂如生在椰子洲人,聞說牛聲不了其義,數數分別如是牛聲。”⑦
無性注釋說,椰子洲上的人從來沒有見過牛,聽聞牛這個名字,意識就開始對此名進行分別,如何分別,譬如用羊、老虎等等已知義的種種名去理解。這種理解是隨著對名的內容的豐富而更加明晰,如知牛有角,四條腿,那么就會用鹿名去遍計,得出結論是一種類似鹿的動物。需要注意的是,已知名本身是指向已知義的。所以,名遍計名其根本目的還是探尋名所指向的義。“名遍計名”通俗講,就是用概念來理解概念。如看到英文“tea”就用漢語“茶”來確定其所指代的內容。“以名遍計名自性”意味著名必然有所指代的對象,即概念必然有其內涵。
“以義遍計義自性”,是說意識對不了名的事物進行種種分別,執為種種名。
無性《攝大乘論釋》又用牛來舉例,從來沒有見過牛也從來沒有想過牛這個名,忽然見到牛這個事物,然后對此形象進行種種意識分別。如想,這是不是鹿的變種,是不是馬的變種等等。以義遍計義自性,還是要通過已經知道名的對象進行分別,其實質還是需要將名義關系對應起來。
“以二遍計二自性”,就是對此名及此名所詮之事物進行推度遍計,對此名和義都形成確定認識,對其種種名及種種義的表現都能明白。
以上五種遍計是涵蓋了意識分別所緣對象的所有情況,其實質是通過名言概念來分別所緣對象,并認為名可以表達所指事物,這是人認識事物的特點。但事實上,這是值得反思的。如說“火”名和所指代的“火”這種現象。仔細去分析“火”名和“火”義會發現,“火名”只是一種概念假立,其不能準確表達“火”這種事物本身。這種表達更多的是一種約定俗成,大家都用這個名字去表達一種事物,但此名并不具有所表達事物的特性。并且,如果試圖用其他概念去表達“火”這個事物時,如用“燃燒”、“熱量”等表達時,會發現這些詞語也不能準確表達“火”這種事物。而且,越是詳細分析所表達事物的特性,會發現,這些特性本身也只能用概念表達,但都不能貼近表達事物。《攝大乘論》中用了“稱體相違”說明依他起自性與遍計所執自性是永遠無法等同的,名永遠無法絕對表達事物體性,即概念與現象之間存在永遠無法對等的關系。這說明人意識的分別作用只能理解事物的被人眼、耳、鼻、舌、身、意經過認識之后的印象,但卻不能表達事物本身。這實際上也顯示了意識分別作用的虛妄性和缺陷性。依他起諸識經過意識分別作用后所確認的實在性顯然是值得懷疑的。
這種懷疑即是對名義關系的考察,此考察的過程《攝大乘論》中稱為“四尋思”和“四如實智”。“四尋思”即名尋思、義尋思、自性假立尋思、差別假立尋思。“名尋思”即是對名概念進行分析,能夠推知名只是概念假立。“義尋思”是對文所表達對象進行分析,能夠推知這個事物也只是意識作用假立而已。“自性假立尋思”是推求名和所指代的義的自性,如色、受、想、行、識名和其義自性,結果發現都是意識的分別作用,唯是識沒有獨立自存的自性。“差別假立尋思”是推求名和義種種差別相,如色常和無常,存在與不存在,也只是一種意識分別作用,唯有識沒有獨立存在性。如是,名和義就成了互相依存的意識分別作用,《攝大乘論》說“名事互為客,其性應尋思,于二亦當推,唯量及唯假。”⑧四如實智則是四尋思而獲得的對于“名、義”的自性、差別唯是識的確證的智慧。
總之,《攝大乘論》所講遍計所執性其實質是意識通過名言概念對諸法所認識之結果,由此形成“名義”關系,并認為能詮名與所詮義有一一對應關系。但事實上,意識的這種認識本身存在缺陷性。對此考察會發現名不能準確表達義,名和義都是意識分別作用下的名言假立。
【注 釋】
① 無著著.玄奘譯.攝大乘論本【M】:大正藏31卷,頁139.
② 無著著.玄奘譯.攝大乘論本【M】:大正藏31卷,頁139.
③ 無著著.玄奘譯.攝大乘論本【M】:大正藏31卷,頁139.
④ 玄奘譯.解深密經【M】:大正藏16卷,頁694.
⑤ 無著著.玄奘譯.攝大乘論本【M】:大正藏31卷,頁139.
⑥ 無著著.玄奘譯.攝大乘論本【M】:大正藏31卷,頁139.
⑦ 無性著.玄奘譯.攝大乘論釋【M】:大正藏31卷,頁404.
⑧ 無著著.玄奘譯.攝大乘論本【M】:大正藏31卷,頁143.
【參考文獻】
[1] 無著著.(唐)玄奘譯.攝大乘論本[M].大正藏第31冊.
[2] 無著著.(陳)真諦譯.攝大乘論[M].大正藏第31冊.
[3] 世親著.(陳)真諦譯.攝大乘論釋[M].大正藏第31冊.
[4] 世親著.(唐)玄奘譯.攝大乘論釋[M].大正藏第31冊.
[5] 無性著.(唐)玄奘譯.攝大乘論釋[M].大正藏第31冊.
[6] (唐)玄奘譯.解深密經[M].大正藏第16冊.
[7] 持松法師.攝大乘論義記(電子版,原載《海潮音》).
[8] 釋印順.攝大乘論講記[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11年.
[9] 王恩洋.攝大乘論疏[M].福建莆田廣化寺印制版.
[10] 剛曉.攝大乘論解說[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
[11] 丁小平.攝大乘論本直解[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
[12] 高崎直道等.李世杰譯.唯識思想[M].貴州:貴州大學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