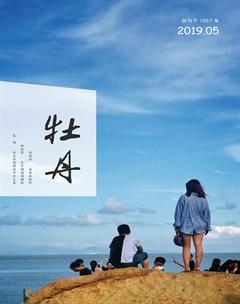《菊與刀》讀書報告
張質雍
《菊與刀》作為西方學者研究日本的經典著作之一,自問世以來便受到學界的關注,數十年來對該書的各種評論層出不窮,可見該書的內容與觀點確有獨到之處。對該書進行合理的分析與解讀,不僅有助于人們了解文化人類學這一學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特點,更重要的是有助于人們深刻地認識近鄰日本和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們。
《菊與刀》是美國著名文化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應美國政府的要求,運用文化人類學的視角和研究方法對日本進行研究后,在其研究報告基礎上整理而成的著作。由于特殊的時代因素,本尼迪克特在進行該項研究時并沒有親自去過日本,只是運用二手的文獻資料以及與當時在美國的日本人進行了接觸。盡管如此,由于其特殊的時代背景、新穎的研究方式以及對日本和日本人獨到的分析和論述,該書在問世以后受到了廣泛的關注,在包括美國和日本在內的很多國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成為文化人類學和研究日本的經典著作之一。本文按照《菊與刀》所論述的內容將其分為五個部分:第一章、第二到第四章、第五到第十章、第十一到第十二章、第十三章。
第一章是全書的開篇,人們可以將其理解為緒論部分。有日本學者將這部分內容概括為方法論,筆者認為這是不全面的,本尼迪克特在本章中確實用相當的篇幅介紹了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方法,但是除此之外,作者還說明了這部著作的時代背景和寫作的背景。筆者認為還有兩點十分關鍵、應該引起注意的地方,首先是作者在這一章中已經部分地揭示了自己對于日本人的研究結果,也就是幾乎所有研究該書的文章都要引用的一段話:“日本人生性極其好斗而又非常溫和;黷武而又愛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禮;頑梗不化而又柔弱善變;馴服而又不愿受人擺布;忠貞而又易于叛變;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歡迎新的生活方式”。其次是作者在這一章中明確表示,她認為世界上不同民族之間差異是必然存在的,但差異并不影響世界各民族的和平共處。也就是說,作者是明確反對日本蓄意對其他國家和民族發動侵略戰爭的,她的這種傾向性為該書后面的內容奠定了一個潛在的基調。
筆者認為,該書的第二部分是第二、三、四章。作者在這三章中主要論述了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原因和目的,以及等級制度和等級觀念在日本社會的重要性。在第二章中,作者對日本為何發動侵略戰爭進行了自己的分析,指出等級觀念在日本的民族意識中十分重要,這與崇尚自由平等的西方(實際上指美國)截然不同。在第三章中,作者提出了日本社會的特征是“各安其分、各得其所”,其內涵是對各個等級或階層的活動做出明確的規定和安排,然后嚴格遵照執行。在第四章中,作者承接上一章,論述了明治維新對日本社會的改造,指出雖然明治維新改變了日本社會的許多東西,但傳統的等級制并沒有從根本上被動搖。最后,作者提出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目的是想把自己的等級觀念向外輸出,想要建立一個以日本為最高等級國家的等級制世界,然而,這種等級制觀念只能存在于日本社會內部,并不被其他國家和民族所接受,所以日本的侵略行為是注定要失敗的。
接下來是第五到第十章,也是全書最為核心的部分,作者在這一部分中詳細剖析了日本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以及這些方式形成的原因。筆者認為可以將這一部分歸納為兩個關鍵詞,即“負恩”和“義理”。作者在第五章中表明東西方民族的思維理念的一個不同之處在于東方人總是有一種對于過去、對于歷史的負債感,而西方人則沒有這種觀念。這一部分中的另一個關鍵詞“義理”是直接按照日文漢字翻譯過來的,按照筆者對書中內容的理解,“義理”應該是“人情債”(對他人的義理)和自尊心(對自己的義理)的混合體,這種“義理”直接影響著日本人的行為,“義理”的任何一個方面受到侵犯都會引起日本人激烈的反應,不過隨著時代的進步,蓄意報復和自殺這樣極端的行為越來越少見,取而代之的是更具積極意義的自我反省和發憤圖強。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第八章中一方面表示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價值觀,要尊重日本人的價值觀,不能犯民族自我中心主義的錯誤,但同時又說日本人的價值觀需要改造,并暗示美國人的價值觀更加優越,這與她在第一章中自我標榜的公正客觀的原則似乎是不相符的。作者在第九章中描寫了日本人對于肉體享樂的追求,尤其是男性在這方面似乎擁有某種特權,他們可以在婚姻之外毫無顧忌地擁有情婦。這種論斷引發了爭議,有學者指出本尼迪克特的論述并不完全符合當時日本社會的實際。當時的日本同西方一樣也是講究對伴侶和婚姻的忠誠的,《菊與刀》中所描述的寬泛道德標準絕不是日本社會中的普遍現象。在第十章,作者正式提出了著名的“罪感文化”與“恥感文化”的定義。作者認為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社會“提倡建立道德標準并且依靠它發展人的良心”,是“罪感文化”的典型代表,而日本是截然不同的“恥感文化”,在這種文化氛圍中,人們由于畏懼他人的恥笑而必須嚴格按照規則行事,這種外在的無形強制力保證了人們的行為的合規性。
接下來進入該書的第四部分,即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作者在這兩章中描述了日本人的成長過程以及在這個過程中所進行的自我修煉。作者認為,日本人的人生軌跡和美國人截然相反,日本人在幼兒期和老年期較為自由,而在中年時期則受到較多束縛。日本的青少年如果因為做錯了事而遭到他人的批評和恥笑,那么他非但得不到家庭的袒護和安慰,反而會受到家人的排斥和指責,與此同時,日本的父母也時常用嘲弄的方式教育和勸導自己的孩子。日本人從小就生活在這種“恥感文化”的氛圍中,從而養成了嚴格循規蹈矩、決不能接受他人恥笑的思維理念和行為方式。不過,日本人的這種性格特征并不妨礙日本在戰后建立像西方那樣的自由平等、對個人束縛較少的社會,因為日本人從小受到的教育要求他們要保持高度的自我克制,這種因素就使日本可以比較平穩地過渡到相對自由的社會。
最后一部分是該書的第十三章,作者在這一章中回到了寫作該書的現實目的:為美軍在戰后統治日本提供政策建議。作者在本章指出,天皇作為全體日本人共同效忠的對象,不應該輕易被推翻,只要天皇愿意和美國合作,美國就應該保留天皇制度,同時盡可能利用日本之前的政府。戰后,日本必須大力發展經濟,提高國民生活水平,減少失業和貧困現象,只有這樣才能防止軍國主義的死灰復燃。作者同時也預言,如果日本能夠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將成為東方貿易中的主角,也會成為世界上有重要影響力的國家。從日本戰后發展的歷史來看,作者的預測是比較準確的,這也說明作者對于日本和日本人的認識和評價是有其可取之處的。
總的來說,《菊與刀》從歷史與現實兩個層面對日本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及其形成和演變的過程進行了分析和解釋,把日本人性格中所展現出的諸多矛盾之處歸因于其獨特的“恥感文化”,這種論斷雖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肯定也是不全面并有失偏頗的。究其原因,最主要還是在于作者的資料來源較為狹窄,僅靠二手的文獻資料和對少量日本僑民和戰俘的采訪,肯定無法探究日本社會的全貌。作者不是專業的歷史學家,對于史料的運用也有不當之處,甚至在某些地方還出現了史實上的謬誤。另外,作者的觀點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其自身價值觀的影響,想要絕對公正客觀也是十分困難的。瑕不掩瑜,盡管《菊與刀》存在著一些不足之處,但其仍不失為一部有價值的學術著作,在從文化的角度剖析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問題上做出了有益的嘗試,直到今天仍然有重要的時代意義。
(天津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