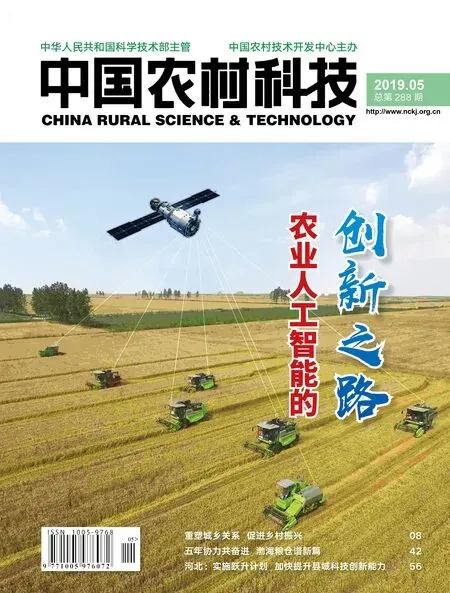“金”菊牽起產業鏈搭起扶貧橋 結出富民果
文/本刊特邀記者 李晨 通訊員 許天穎

4月里,南京農業大學(以下簡稱“南農”)的定點扶貧縣,貴州省麻江縣的宣威鎮卡烏藥谷江村,800多畝菊花悄悄長出新葉。這已經是菊花園落戶麻江的第四年。
據悉,去年的中秋、國慶10天假期,這里吸引八方游客踏“芳”而來,山溝子里的貧困村一下子“火”成大景點,激活農家庭院經濟,拉動傳統農業消費的“提檔升級”。
不僅在貴州大山,近年來,北至天津、南至深圳、東至浙江、西至青海,在全國的版圖上,南農品牌的菊花園競相開放;以菊花為主題的休閑旅游基地將近20個,這背后依托的是2018年國家科學技術發明二等獎團隊—南農菊花遺傳育種團隊的科技力量。
一朵小小的菊花,不囿于傳統的第一產業,與二、三產業深度融合,從貴州“梯田”綻放到青海“雪域”,拉動起產業興旺、鄉村振興的鏈條,完成了一場祖國大地的美麗旅行。
神農傳人采百“菊”
南農湖熟花卉基地,占地150余畝,保存了5000多份菊花資源,其中400多個新品種都是由學校自主培育的,是中國菊花種質資源保存中心,也是目前世界最大的菊花基因庫。
記者注意到,這里的菊花顏色各異、形態萬千,圓球型的綠菊翠色欲滴,大的似乒乓、小的像蜂窩;“風車”菊花突破了傳統菊瓣的細長卷絲,一瓣兒一瓣兒筆挺挺的,像是從花芯處伸出來的小勺子;還有的單朵菊花上就匯聚了好幾種顏色,不僅花瓣、花蕊顏色不同,就連一個花瓣上還漸變出兩種顏色,令人目不暇接。

陳發棣教授進行菊花新品種選種
“菊花的花型、花色是植物界中最豐富的,被稱為自然界育種的奇跡。”南農菊花團隊負責人,長江學者特聘教授陳發棣介紹,他的導師,原金陵大學李鴻漸教授從1944年開始就從事菊花品種搜集、保存等工作,距今已有74年的歷史。
“選育一個新品種大概要花6年左右的時間”,南農菊花課題組教授陳素梅介紹說,新品種主要通過遠緣雜種、雜交等方式培育,每年會配置100多個雜交組合,獲得8-10萬株后代,根據后代呈現出的形態、生長勢、抗性等不同標準,第一年初選出幾百株,第二年進行復選,一般會留下幾十個株系,然后再進行品種比較試驗、區域試驗等過程,最終獲得性狀穩定的優良品種,大概要花去6年左右的時間。
菊花基因庫里藏著“壓箱底”的核心種質資源,陳發棣告訴記者,為了搜集野生種質資源,從1992年開始,他和實驗室的研究生一起,幾乎跑遍了全國各地,有的雖然在植物志上有記載,但是常常“踏破鐵鞋無覓處”,最高爬上過海拔5108米的米拉山口,“撿細針”般地尋找種質。
陳發棣的這股子科研“執拗”勁兒感染了團隊的中青年骨干,王海濱副教授就是其中之一。為了尋找“抗寒”的野生種質,2018年4月到9月,他先后3次來到青藏高原,扛著氧氣瓶、戴著防護工具,讓當地老鄉帶著,在海拔5000多米的西藏米拉山口找到了寶貴資源紫花亞菊。
古有神農嘗百草,今有傳人采百菊。團隊目前已經建立起菊花近緣種質抗蚜、耐寒等重要抗性評價體系,從收集的資源中鑒定出抗蚜種質19份、耐寒種質16份及其他抗性種質43份,首次發現了黃金艾蒿、細裂亞菊分別是菊花抗蚜、耐寒育種的最優種質。
2018年10月,在海拔3000多米的青海高原,從南農菊花團隊引進的園林小菊種植成功,刷新了高寒高海拔地區室外引種園林小菊的記錄。

陳發棣教授(左一)團隊赴菊花生產企業指導菊花栽培技術
這樣的耐寒新品種是如何育成的呢?陳素梅告訴記者,團隊首創了基于控制授粉、胚珠拯救和雜種多色基因組原位雜交鑒定的菊花屬間抗性種質創制技術,建立了以遠緣雜交和分子育種相結合的菊花育種新技術體系,大大提高了菊花抗性育種效率。
目前,團隊已經創制抗蚜、耐寒等遠緣雜種200余份,突破了抗性和花色、花型、株型等性狀的綜合改良,率先育成綠色、乒乓型和風車型等優質高抗新奇特菊花新品種49個,這些抗性新品種的推廣應用,不僅大大降低了生產成本、減少了農藥使用,還能延長花期、拓展菊花的種植區域,推動了我國菊花品種更新和產業升級。
精準扶貧安上科技“引擎”
“大田栽秧行對行,我在田壩栽花秧......”這是三年前,貴州麻江縣高枧村村民易芙蓉編唱的山歌,作為南農的定點扶貧縣,學校的特色學科資源陸續被引進到這里落地開花。
60多歲的易芙蓉,之前未曾參加過任何工作,扛著鋤頭在自家門口就能種植菊花,一個月能拿2000多元的收入,拿到工資的第一月就跑去縣城,花500多元給自己買了生平最貴的幾件新衣裳。
如今的麻江菊花不僅裝點了農戶的門面,為貧困戶摘去了多年的“帽子”,還綻放到了更加廣闊的天地,在麻江縣宣威鎮“藥谷江村”,近千畝、350個品種的菊花被引進栽種,在當地特有的梯田,滿園香艷、錯落有致。
2016年以來,南農菊花團隊將先進的農業技術、科研成果和管理經驗紛紛“嫁接”到麻江,不斷加強菊花品種改良,通過種植一片菊花,發展一個產業,鏈接了一批農戶,富裕了一方百姓。
據了解,自菊花園開園以來,“貴州麻江品菊季”累計吸引游客近70萬人次,帶動旅游綜合收入近1.2億元。2018年僅中秋、國慶10天假期就吸引了近18萬游客。
菊花團隊成員、南京農業大學教授管志勇說:“不僅在貴州麻江,在青海烏蘭、在湖北麻城、在陜西商洛,通過品種和技術帶動產業,菊花猶如動力‘引擎’,為精準扶貧插上了經濟騰飛的翅膀。”
接“二”連“三”產業興
菊花團隊成員、南農教授房偉民告訴記者,菊花觀賞性高、開花晚、花期長,在相對寂寥的秋冬季節是不可多得的觀賞花種。
南農湖熟菊花基地將傳統的菊展與鄉村休閑旅游結合,打造特有的“菊花經濟”模式,從2013年開始,在湖熟,每年有數十萬游客前來賞菊,拉動了周邊旅游、餐飲、零售、農副產品等行業。據地方政府統計,基地2018年參觀人數達55萬人,為老百姓和地方經濟創造收益5200萬元。
南農選育的菊花新品種觀賞性好、抗性強,在長江中下游地區,種苗種植后一般3個多月就能開花,按照房偉民教授的話,就是“當年建設、當年見效”,2017年,在浙江金華,4月份征集的土地,10月份就實現了菊花園對外開放,其中1個周末就迎來了10多萬人次的參觀游覽。
如今,“菊花主題休閑旅游模式”輻射全國,在江蘇淮安和射陽、安徽滁州、浙江金華和南潯、湖南臨湘、陜西鄠邑區、江西南昌、深圳等地,南農與地方政府或企業合作,形成以菊花新品種展示、菊花文化傳播為主,結合農產品展銷的休閑旅游農業模式,打造了一張亮眼的“金”字招牌。
在江蘇淮安白馬湖,占地約200畝的菊花基地又將成為產學研一體化的新模板—當地政府十分看重南農菊花品種資源和研發優勢。白馬湖規劃建設管理辦公室副主任劉書蘇告訴記者,“我們與南農大合作,要把白馬湖菊花園打造成為中國最大、景觀最美、品種最全的菊花產學研一體化研究基地,這與白馬湖的未來發展定位—生態、綠色、觀光、度假的思路是相契合的。”
在躬耕觀賞菊的育種栽培外,團隊還致力于菊花功能性系列產品的開發。鮮食花朵、泡大朵的蘇菊、吃一桌“全菊宴”,這些在陳發棣眼中已經是“過去式”了,“我們正在積極選育可以吃‘葉子’的菊花品種,既能清炒,也能燒湯,還能炸天婦羅!”
從觀賞型菊花,到茶飲型、食用型、藥用型菊花,團隊每年都能在菊花的產業鏈條上翻出新的花樣,陳發棣說,市場經濟環境下,農業價值需要通過二、三產業來提升,只有將一、二、三產業有機融合,才能實現農產品的高附加值,才能讓更多百姓受益。
除了“墻”外飄香,小小的菊花也在校內牽起了學科鏈,“墻”內開花。2015年,由南農科研院牽頭,集結了學校相關特色優勢學科,重點孵化“菊花產業鏈項目”。團隊與工學院合作,開發水肥一體化控制系統,通過機械化實現菊花的輕減栽培;與信息院合作,制作菊花小百科,二維碼一掃,就能識別上千種菊花。
南農“金”菊一頭搭起了扶貧橋,結出了富民果;另一頭則連接了二、三產業,延展了產業鏈。在陳發棣看來,高校的科研工作要為社會服務做好科技背書,在為貧困地區搭好脈、當好醫的同時,要為現有產業安上“引擎”,延伸“鏈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