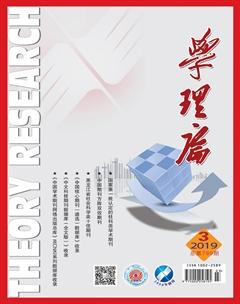農村階層分化及其利益差異
周君銀
摘 要:不同的社會階層有著不同的利益訴求。精準扶貧戰略的推進使得這種階層之間的競爭與博弈關系更加復雜化和多元化。本文從扶貧資源精準配置的視角,分析了現階段農村社會階層分化的現狀及各自的利益訴求,以及這些利益博弈引發的諸如扶貧資源被精英俘獲、瞄準偏離、參與不足、利益表達沉默等扶貧困境,并根據精英階層、中間階層及貧弱階層的特性與需求探尋三者之間的平衡點,以此實現資源分配的最優配置。
關鍵詞:農村社會階層;利益差異;精英;扶貧資源
中圖分類號:F328 ? 文獻標志碼:A ? 文章編號:1002-2589(2019)03-0021-02
在扶貧戰略背景下,扶貧資源成為新的公共資源,而精英階層對資源的俘獲使得扶貧效果欠佳、中間階層的參與俘獲或不作為都助長了扶貧資源分配不均,而貧弱階層自身的利益表達沉默更是加劇了資源配置的不均等。本文結合農村社會扶貧背景下扶貧資源配置問題,從社會資源占有的角度對楊華劃分的七大階層與李祖佩、唐麗霞(2015)[1]等人對貧困村精英階層與貧弱階層的博弈關系進行整合,基于我國農村自身存在的獨特的地緣、血緣與利益、人情相互交錯的差序文化,將現階段農村社會的階層劃分為精英階層、中間階層和貧弱階層。在脫貧攻堅的緊迫背景下,本文試圖分析農村精英階層、中間階層和貧弱階層在經濟條件、發展能力、思想觀念和利益表達等方面的差異性,探尋三大階層主動參與扶貧的利益平衡點,以此約束或引導精英階層奉獻扶貧、引導中間階層主動參與扶貧、激勵貧弱階層自身脫貧。
一、三大階層特征及其利益訴求
(一)精英階層及其利益訴求
精英治理是當前農村社會治理的普遍特征[2]。精英階層的普遍特征在于擁有較多經濟資源和象征性資源。其中,經濟資源包括土地、資金、信息、知識技能等,象征性資源包括權力、地位、關系網絡、社會地位及其他社會資源。其中,土地是影響農村階層占有經濟資源和象征性資源的主要因素。土地占有量越多,其享有的收入水平、村社內部關系質量、超村社網絡關系大小及接近鄉村政治權力程度都呈現正相關的關系[3]。精英階層包括以村干部為代表的體制性精英、以鄉村混混為代表的社會精英、以私營業主為代表的經濟精英和以傳統文化人為代表的知識精英[4]。其中,體制性精英即政治精英,他們是農村社會的管理者,是黨和國家方針政策的基層執行者,是扶貧工作的精準識別、管理的具體組織者和實施者;社會精英主要以鄉村灰色勢力為代表,在扶貧工作中以暴力、強勢等灰色手段奪取資源,在短期內實現財富積累[3];經濟精英依靠其帶頭致富的經濟頭腦,在近年來的鄉村建設中掀起了一股“富人治村”的浪潮,精英階層與政治精英緊密聯系、關系密切,同時又不太關心普通農民的生產生活,因而往往在扶貧資源配置中搶先獲得扶貧項目及其他資源;知識精英的文化素質水平與政治覺悟較高,具有較高的修養并能夠獲得農村其他階層的信任和敬仰,同時由于他們對鄉村政治生活比較關心,有較高的思想追求,因此在農村社會往往擔當正義與民主的角色,具有較高的話語權。在現實生活中,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社會精英往往形成一種利益聯盟,占有較大優勢的農村公共資源,扶貧資源也往往被這個聯盟捕獲,形成扶貧資源配置中的“精英俘獲”困境。
(二)中間階層及其利益訴求
中間階層主要包括中上階層、中農階層和中下階層(高于貧困階層的群體)。中上階層以外出經商農戶為代表,中農階層以農業大戶為代表,中下階層以農民工和半農半工農戶為代表。總體上,中間階層的經濟水平相較于精英階層低而又高于貧弱階層,在土地占有量和收入水平上處于中間水平,他們有自己致富的本領,與村內利益糾紛并不十分明顯,對村內資源的追求欲望也不極端,他們既受惠于農村政策,又是農村事務有力的監督群體,即便是精英階層也在選舉方面依賴于中間階層的支持。相較于貧弱階層來說,中間階層的生活水平較高,空閑時間較多,時間安排較為靈活,對村社事務的興趣也相對貧弱階層要高。中間階層占農村群體的絕大多數,因而是農村社會建設的主力軍,同樣是農村扶貧致富的依靠力量。因而在扶貧開發過程中,若能正面引導和正向激勵,克服其“冷漠性”,發揮其公共理性的約束功能,能夠助推精準扶貧的順利開展。
(三)貧弱階層及其利益訴求
貧弱階層包括貧困群體和弱勢群體。貧弱階層的特殊性表現在:一是在土地占有量上較少,只有1~3畝[5];二是在發展能力上,由于鰥寡孤獨、老弱病殘、好吃懶做、目不識丁等多種因素導致自身脫貧能力欠缺;三是在社會關系上可利用的社會網絡資源較少,村社內部關系網絡狹窄,因而缺乏依靠外力脫貧的機會。因此,貧弱階層正是現階段農村扶貧的主要對象。在貧弱階層中,又存在著利益表達沉默和利益表達激化兩種行為傾向。利益表達沉默群體不能夠及時表達自己的合理訴求,在扶貧開發中參與性不足;利益表達激化群體往往通過上訪、威脅等方式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而這兩種形式都不利于扶貧戰略的有效實施和全面小康社會的實現。
二、扶貧資源配置中的階層利益訴求差異引發的困境
農村社會分化之后,農村的利益關系主要表現為公共利益的分配與貧富差距問題[3]。在扶貧開發過程中,農村各階層的利益關系是連接各階層交流、互動的最重要的關系,但不同的階層利益訴求的差異和獲取能力、主動性上的差異又加劇了這種階層分化、利益分配和貧富差距。總體看來,扶貧資源配置中的階層利益訴求差異引發的總體困境在于扶貧瞄準錯位、扶貧資源產出效果不佳、扶貧工作內卷化、扶貧開發陷入困境。具體來說,精英階層形成的利益聯盟造成一種“精英俘獲”困境,中間階層的利益弱關心導致一種參與冷漠,貧弱階層需求與能力的差異形成一種普遍存在的社會貧困問題。
(一)精英階層在扶貧資源配置中的精英俘獲困境
在村莊貧困治理中,精英俘獲表現在壟斷扶貧項目承包和霸占村集體扶貧資源分配兩個主要方面[4]。此外,在村莊項目實施過程中,農村精英階層往往成為項目實施的主導者,中間階層和貧弱階層成為項目實施的具體操作者,而村莊精英往往通過壓低工程成本的方式實現更多的利益占有,而其他階層往往是高勞動力投入,而獲取低收入。而低質量的工程項目對提升農村發展環境并不能產生良好的積極效應,反而承擔了質量低下的工程項目的消極后果[4]。
其次,精英俘獲導致的工程項目劣化導致了扶貧工作內卷化的產生,即便國家對扶貧資源的投入越來越多,但扶貧取得的邊際收益卻越來越少,扶貧本身正義、公平的價值理念受到挑戰。價值理念的約束功能下降,加上精英階層與貧困階層的交往分化,使得這種利益差異格局固化。
尤為重要的是,精英俘獲的最直接表現在于扶貧瞄準偏離。精英俘獲下的“強者”利用自己的“強權”俘獲扶貧資源,精準扶貧的價值意義不斷偏離。汪三貴和郭子豪以7省市10個縣的抽樣調查證實瞄準偏離的存在,指出民主評議相對于收入瞄準所識別出的貧困群體存在近50%的偏離程度[6]。袁樹卓等基于內蒙古Z縣建檔立卡案例進行研究,表明在政府通過政策合法性重構克服瞄準偏離之前,我國精準扶貧中存在著瞄準偏離問題[7]。精英俘獲的長期存在會激化社會矛盾,公共資源為精英個體所占有,這違背了國家社會的發展理念,脫離了村莊倫理,更是與脫貧攻堅戰的任務要求背道而馳。
(二)中間階層在扶貧開發中的弱參與困境
鄉土農村是一個深受差序文化影響的社會,中間階層在差序格局中處于不遠不近不親不疏的地位。中間階層有自己的發展能力,既不需要依靠精英階層,也不親近貧弱階層。因此在扶貧工作中也沒有表現出過多的主動性。而中間階層的這種“弱參與”并不符合扶貧攻堅和農村社區發展建設的理念。多元主體的積極參與是當今農村社會治理與貧困治理的應有之義。而中間階層的相對冷漠,使得精英階層的俘獲行為因為沒有有效的監督而愈演愈烈,貧弱階層沒有可靠的利益代表者而持續貧困。傳統的根植于鄉土社會中的正義公正的公共理性正在中間階層中不斷弱化。
(三)貧弱階層在獲取資源脫貧致富中的利益表達困境
貧弱階層是扶貧開發的對象,是扶貧資源作用的主要對象。貧弱階層受限于資源匱乏、自身能力不足、主動性不高、信息獲取滯后和外部支持匱乏等主客觀原因,面對精英俘獲的利益沖突往往表現為利益表達沉默,將貧困與命運相聯系。而一方面,由于部分“能人”將“先富帶動后富”的理念曲解為“自己先富”或“親朋好友先富”再帶動“群眾富起來”,忽視并挫傷了普通貧弱群體的利益,他們不滿于農村“先富能人治村”利益剝奪的現狀,往往通過上訪等形式表達自身的不滿。而這種合理的利益表達方式卻與精英階層的利益發生了沖突,導致農村階層在人情上的進一步分化。這些分化的現狀并不利于農村社會的穩定,然而社會穩定協調卻是農村社會發展和扶貧工作順利開展的前提。
三、結論及建議
社會資源的占有量是區分社會階層的主要標準,也是影響話語權與行動能力的重要支撐。傳統的公共資源是農村階層搶占的主要對象,在脫貧攻堅戰略背景下扶貧資源引發了新一輪資源的爭奪。貧困治理問題,必須根除精英俘獲造成的諸如瞄準偏離的現實困境,必須依靠農村社會力量的廣泛參與和有效整合,積極引導貧弱階層實現自身的脫貧,必須將貧困治理與社會治理結合起來。
參考文獻:
[1]唐麗霞,羅江月,李小云,等.精準扶貧機制實施的政策和實踐困境[J].貴州社會科學,2015(5):151-157.
[2]黃博.自治形態與精英治理——對村莊精英治理的二維解讀[J].領導科學,2018(7):8-12.
[3]楊華.當前我國農村社會各階層分析[EB/OL].豆丁網,[2018-10-29]..http://www.docin.com/p-1779347336.html.
[4]陳柏峰.土地流轉對農民階層分化的影響——基于湖北省京山縣調研的分析[J].中國農村觀察,2009(4):57-66.
[5]李祖佩,曹晉.精英俘獲與基層治理:基于我國中部某村的實證考察[J].探索,2012(5):187-193.
[6]汪三貴,郭子豪.論中國的精準扶貧[J].貴州社會科學,2015(5):147-150.
[7]袁樹卓,殷仲義,高宏偉,等.精準扶貧中貧困的瞄準偏離研究——基于內蒙古Z縣建檔立卡案例[J].公共管理學報,2018(4):126-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