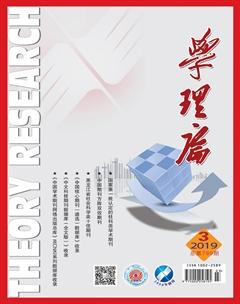萊茵報時期馬克思對現實問題的關注及意義
周斌 曲勝男
摘 要:馬克思在費爾巴哈人本學唯物主義的影響下,對現實問題不斷關注,與各種現實問題緊密聯系在一起,通過對書報檢查令的批判以及在林木盜竊案和摩澤爾記者辯護中對貧困百姓物質利益問題的維護,揭露了封建貴族的專制性,使馬克思不斷對唯心主義理性國家觀產生懷疑,對馬克思早期思想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萊茵報;馬克思;物質利益;書報檢查;林木盜竊
中圖分類號:A81 ? 文獻標志碼:A ? 文章編號:1002-2589(2019)03-0055-02
馬克思雖為青年黑格爾派的成員,卻對脫離社會現實,只想單純依靠理論試圖解決一切的觀點表示反對,認為哲學應走出自我意識范圍,接受社會,才能真正地表現自己。他認為以鮑威爾兩兄弟為主要代表的青年黑格爾分子,以“自由人”為名組成小組,實則是脫離了現實社會活動的存在,認為該小組所寫文章皆不敢涉及社會現實問題。對此,馬克思表示要進行到實際斗爭中去,多關注社會現實。
一、對現實問題關注的緣由
萊茵報時期的馬克思在批判普魯士國家現存的矛盾時,對一直所信奉的黑格爾哲學開始動搖,這一時期對自由和權利的向往正是受到費爾巴哈人本學唯物主義的影響。1842年,馬克思與鮑威爾共同寫作《末日的宣告》。在1842年3月5日,馬克思依然決定與鮑威爾共同撰寫《末日的宣告》第二部,但在3月下旬,馬克思卻表示自己的觀點發生變化。短短的數日之中,馬克思的思想出現了巨大的反差,認為自己的文章應以新的觀點去敘述,這種新的觀點提到“宗教的人類學”“宗教的一般本質”等,這說明費爾巴哈《基督教的本質》一書中的人本學唯物主義觀點已經觸動了馬克思的思想[1]。費爾巴哈在文中表示只有與思辨的唯心主義決裂才能使哲學真正自由和進取,認為自然才是人賴以生存的基礎,是人認識的來源,單純地談論人的認識、理性精神、宗教等是毫無根據可言的,應該與自然相結合,這無不表現了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思想。同時他還指出人是感性實體,是最現實、最真實的存在,是自然的一部分。無論理性、情感還是宗教都是人的本質,充分肯定了人在自然中的重要作用。無論是在對書報檢查令的批判中,馬克思表示自由是人的本質,是屬于人的一切權利,還是在林木盜竊案中維護貧困百姓的權利,以及在摩澤爾沿岸農民貧困的辯護中對官僚本質的揭露,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人本學無不滲透其中。雖然這個時期的馬克思還不能完全跳出黑格爾的唯心主義圈子,但卻批判地吸收了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人本學思想,為馬克思的思想轉變帶來重要影響。
二、馬克思對現實問題的探索
1842年馬克思在擔任《萊茵報》編輯時,不斷與社會現實相聯系,所寫文章也大多與社會現實相關聯,思想觀念也逐漸發生轉變。
(一)馬克思對書報檢查制度的批判
在《評普魯士的書報檢查令》中,馬克思認為新的書報檢查并沒有為實現民主自由而放寬政策。按照新的書報檢查令的規定,對違反書報檢查令要求的行為和后果應歸咎于個別偵查官的不良品行,而非制度本身。該舉措無非是為了所謂的普遍利益能夠得到維護,使專制制度能夠繼續維持下去。“虛偽自由主義的手法通常總是這樣:在被迫讓步時,它就犧牲人這個工具,而保全事物本身,即制度。這樣就會轉移從表面看問題的公眾的注意力。”[2]109換言之,馬克思是在告誡世人,與其被那些偷梁換柱的手法弄得撲朔迷離,不如緊緊地抓住事物的本質——制度。同時,馬克思對新的書報檢查令規定的寫作內容要求也進行了嚴厲批判。他認為自由是人的本體性的存在,是屬于一切人的權利,人就是自由的存在方式和外在載體。自由理應屬于一切領域存在的所有人,但大多數人的自由卻被極少部分的人所限制。發表文章是人們表達其精神內容和思想特點的一種有效途徑,理應由寫作者的意圖去描述,卻要遵守書報檢查令的規定。這實則是對自由和民主的變相壓迫和否決。
(二)關于林木盜竊問題的辯論
1840年馬克思對把撿拾枯樹枝列入林木盜竊范圍一事展開批判。在《關于林木盜竊法辯論》中,馬克思認為撿拾枯樹枝與林木盜竊行為大不相同,二者有本質的區別。林木占有者只是單純地對作為一顆完整樹木的占有,而脫落下來的枯樹枝已成為獨立的部分,不再與樹木有關聯,因此拾撿枯樹枝并不屬于林木盜竊行為。法律理應真實地揭示事物法的本質,而拾撿枯樹枝與林木盜竊本是兩種不同表現,卻單純給它們一個共同的定義,那就是“顛倒黑白、混淆是非”是“在不應該用盜竊這一范疇的場合用了這一范疇”[2]245。如此一來法律便違背了自身的原則,庇護了封建階級的特權,損害了貧困百姓的利益。此外,馬克思認為撿拾枯樹枝是貧困百姓古往今來形成的慣有權利。他認為財產的內在規定性賦予富人權利,是其固有屬性,而其非固有屬性就表示拾撿枯樹枝是窮人的權利。這些規定性是事物自身所決定,從一開始就表現出來,枝繁葉茂的主干與脫落的枝干就是貧富的對比。馬克思認為該權利雖沒有具備法律的形式,但其內容并不與法律形式相違背,是屬于農民最底層的法。
(三)關于摩澤爾記者的辯護
1842年12月,馬克思為記者科布倫茨寫下《摩澤爾記者的辯護》一文來駁回總督的責備。馬克思指出,當地政府否認報告的真實性,認為該狀況是由個人的私利所造成。在當地政府派官員核實了報告的真實性后,官員卻極力扭曲事實。某地發展狀況的好壞,反映了該地區的管理是否得當。如果承認了報告中的貧困現狀,就是承認了當地政府的管理不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他們就會否認報告的真實性,認為貧困是部分葡萄莊園者利欲熏心所致。馬克思表示當地政府這么做的原因就是其自身利益所驅使以及他們對上級管理原則和管理制度的服從。“管理原則和制度到底是好還是不好,這個問題他是無權過問的,對此只有上級才能做出判斷,因為上級對各種事情的官方性質,即對各種事情和整個國家的聯系有比較全面的和比較深刻的認識。”[3]373當地政府作為上級的執行機構無權過問管理工作,只能按照上級的要求去執行。在保證自身利益又能完成任務的同時,他們就會在既定的權限范圍內設法對被管理者進行整改,以便與當前的管理原則相適應。馬克思指出,造成該地區農民貧困的狀況正是現有和統治原則之間相抵觸的結果。
三、對現實問題關注的重要意義
萊茵報時期是馬克思思想發生變化的重要時期。列寧曾表示馬克思在萊茵報時期就開始了從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從革命民主主義向共產主義的轉變[4]83。因此,萊茵報時期馬克思對現實問題的關注在其思想轉變過程中具有重要意義。
(一)促進《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寫作
萊茵報時期對現實問題的關注開啟了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寫作。馬克思說:“1842—1843年間,我作為《萊茵報》的編輯,第一次遇到要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為了解決使我苦惱的疑問,我寫的第一部著作是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性分析……”[5]31萊茵報時期的馬克思認為理性是世界的本質,國家是理性實現自身的表現,具有決定作用,國家應當維護民主和自由,而在批判書報檢查令的過程中發現普魯士國家非但沒有體現出理性的原則,還變相地壓迫民主和自由。在林木盜竊法的辯論中,馬克思發現物質利益在國家和法中的重要性,普魯士貴族為了維護封建主的利益犧牲了法的原則,所有的立場和動機皆是從自身利益出發。在摩澤爾記者的辯護中,馬克思更是意識到在物質利益之下形成的官僚本質,為了自身的發展和利益將責任歸咎于他人去彰顯上級領導的管理得當,這都是現實問題與理性法相抵觸的表現,而馬克思一直所信仰的理性自由主義無法解決他所面臨的現存狀況,繼而陷入理論困境。為了解決該困境,馬克思便開始了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繼而思想發生轉變。
(二)推動馬克思向政治經濟學研究,向唯物主義、共產主義的轉變
萊茵報時期馬克思對現實問題的關注使馬克思首次經歷了經濟利益問題,為其思想發展做了重要準備,尤其是向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轉變。馬克思在對黑格爾法哲學選擇性批判中認識到物質的生活關系的總和,即市民社會對國家和法具有決定作用,而對市民社會更深入的研究和表明均在政治經濟學中體現。在林木盜竊案和摩澤爾記者的辯護中,馬克思對封建階級的反動迫害進行批判,揭露了王室貴族的專制性,為貧困百姓的物質利益發聲,更是意識到這種構建在物質利益下形成的客觀關系對社會具有制約作用。這逐步推動了馬克思從原來的哲學研究領域,放眼到政治經濟學領域,對馬克思思想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在林木盜竊案中,馬克思明白自身現有的哲學理論非但不能對現存狀況做出合理解釋,更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在研究這些問題的過程中,馬克思了解到國家制度、法律、物質利益等與現存經驗的矛盾,使他逐漸擺脫了最初的唯心主義觀點。馬克思認為法律并不是為了少部分人的特殊利益而制定的,更不能讓特殊群體利益去代表多數人的利益,這是不公正的。正是這些現實問題的鞭策,使馬克思沖破了原有的唯心主義。同時,他在摩澤爾記者辯護中對國家制度、管理原則及物質利益三者的關系形成了較為客觀的認識,加深了馬克思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并且對案件都進行了深入的調查和研究,收集了大量的材料和條令。上述所有表現都體現出馬克思以唯物主義的方法來分析和解決現存的各種矛盾,對馬克思由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轉變起了推動作用。
萊茵報時期,馬克思對共產主義的認識尚未深刻,他認為當時的“共產主義”是一種空想社會主義,其并沒有存在的現實可能性,“‘萊茵報甚至在理論上都不承認現有形式的共產主義思想的現實性,因此,就更不會期望在實際上實現它,甚至都不認為這種實現是可能的”[3]173。但在林木盜竊案和記者辯護中,馬克思為維護窮苦人民的利益進行辯護,充分體現出馬克思關心民眾疾苦,向往自由、致力于平等、公正等思想。這些都對馬克思向共產主義的轉變具有奠基作用。通過以上描述可以得知,萊茵報時期馬克思對現實問題的關注和研究,動搖了馬克思對黑格爾理性主義國家觀的堅持,使馬克思的思想發生轉變,在馬克思的思想理論形成中占有重要地位。
參考文獻:
[1]許俊達.試論《萊茵報》時期費爾巴哈對馬克思的影響[J].安徽大學學報,1987(2).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4]列寧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