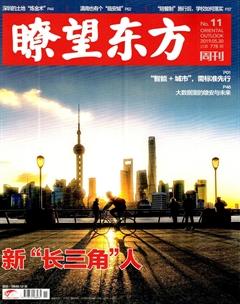長三角的日常:愈發模糊的城市邊界
駱曉昀

“80后”女孩盧芊羽家住江蘇省昆山市玉山鎮,每天從昆山搭乘高鐵前往上海上班(賴鑫琳/攝)
剛剛過去的4月,上海一家國企的財務總監閆麗收到了一張交通違章罰單。
閆麗的公司在上海虹橋機場附近,家在嘉興。每天開車通勤往返于兩地之間,日復一日,已有好幾年。
閆麗告訴《瞭望東方周刊》:“以前從家出發走小路到虹橋機場,路上不堵,也沒幾個紅綠燈。而現在明顯感覺路越修越好,但車流量也越來越大,收到罰單就是因為心急而違規變道超車造成的。”
如今,導航地圖上“前方擁堵”的提示。印證著如閆麗這樣跨城工作的新“長三角”人已不是少數。
財務總監的雙城賬
2017年上半年,浙江省嘉興市、江蘇省南通市發布“官宣”,要“主動對接上海及上海大都市圈建設”。其中,嘉興市提出創建“浙江省全面接軌上海示范區”。南通市提出建設“上海大都市北翼門戶城市”。

2018年8月27日,載有江蘇泰興危重病人的救援直升機飛抵上海龍華直升機場(方喆/攝)
閆麗的家在嘉興。四年前,她參與了公司在上海的項目,在上海蓮花路租房居住了近兩年,那時她每天從暫住地到閔行上班。公司上馬新項目后,閆麗徹底過上了雙城通勤生活。
“我的工作在上海郊區,家在嘉興郊區,但這兩個郊區特別近,所以也沒有考慮換工作或是到上海居住。”閆麗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這名財務總監認真計算過生活成本,“說實話,在上海無論是買房還是租房都有相當的壓力。我有兩個孩子,從孩子的生活環境、教育成本等多個角度考慮。現在的定居點是合理的選擇。我也比較過在上海住的通勤成本,其實與兩地往返的差別并不大。”
以閆麗的資歷和人脈,在嘉興本地找一份工作不算太難,比較尷尬的是收入肯定不如上海。
統計數據顯示,2018年,上海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64183元,而同期嘉興的數據為57437元。
閆麗考慮的還有孩子的教育成本、教育環境以及考試的匹配度。在她看來,盡管上海教育資源豐富,也存在不均衡的問題。選擇好學校的成本并不低;孩子戶口在浙江,意味著將來要在浙江參加高考。如果學習體系與考試體系不匹配。那也是一種冒險。
算清了這筆生活賬,閆麗的雙城生活便成為常態。
打通醫保異地結算
會說上海話、南京話、常州話、無錫話的姚沅出生在南京,現在就職于益基譜管理咨詢(上海)有限公司。除了在美國學習的那一年半,他29年的人生都在長三角兜兜轉轉。
小時候姚沅在長三角串門走親戚,如今公司的客戶也主要集中于長三角地區。對于長三角生活的變化,姚沅說體會最深的就是醫保。
十年前,他的奶奶有一次病得嚴重。“當時她人在上海。醫保所屬地是南京,由于醫保無法異地結算,且家中一時籌不出大筆錢款,只能連夜趕火車回寧,第二天再急忙去醫院看病。而現在,醫保異地結算問題解決了,方便了很多江浙滬一帶居民,尤其是老人。”姚沅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據中國寧波網報道,2018年10月16目。居住在寧波的上海退休市民章阿姨成為上海參保人員在寧波門診異地就醫直接結算第一人。
章阿姨在寧波市第一醫院門診看病花費1368.83元,個人支付了240.23元,上海市醫保基金直接結算1126.60元。
在章阿姨就診的一個月前。提前辦理轉外就醫備案手續的寧波參保市民屠先生.在上海市肺科醫院門診就醫時使用寧波市社保卡直接結算成功。
截至2018年10月,蘇浙皖8個試點地區與上海15家三級醫院和金山區、松江區兩區部分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實現互聯互通。門診費用可按規定直接刷卡結算。
然而。與新“長三角”人的豐富需求相比。社會醫療保險的長三角一體化結算,步子還需要再大一些。
河北人舒揚在上海大學畢業后進入上汽集團,2018年為了更好的職業前景跳槽去了吉利汽車。他在吉利汽車工作的第一站是湖州長興縣。此后調任至寧波杭州灣地區,半年前回到吉利杭州總部,而他現在的醫保繳納地還在長興縣。
“2019年春節前我感冒了。長興的醫保卡在杭州無法直接刷卡結算,只能先自費醫療。”舒揚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舒揚說,感冒看病花費雖然不多,但病后走異地報銷很浪費精力。而且自己參保了卻沒有享受到權益,多少有些感到遺憾。“大型企業員工工作地點變動很常見,醫保結算不通暢很不方便,希望長三角所有地區的醫保都能實現直接刷卡結算。”舒揚說。
“現在,醫保異地結算問題解決了,方便了很多江浙滬一帶居民,尤其是老人。”
到底是哪里人
1843年上海開埠,江蘇、浙江的移民開始在黃浦江邊聚集。現在多數上海居民的祖輩都是江蘇人或浙江人。
2013年,復旦大學發布過一份《長三角人口遷移流動研究報告》。報告透露,從上世紀90年代至2010年,上海迎來了新一輪移民潮,而這一波新上海人中仍以江蘇、浙江移民為主。
根據2010年的統計數據,上海有近900萬的外來人口,其中由長三角內部江蘇和浙江兩省流入的數量分別是150.35萬和45.05萬,占外來人口總量的21.7%。
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任遠是這項課題的帶頭人,他告訴《瞭望東方周刊》,長三角地區從歷史上就是一個統一的整體,且延續至今。未來,長三角地區的二十多個主要城市不應只局限于交通、經濟等領域的合作,更應關注社會領域的合作,除實現經濟一體化外,還要實現人口與社會管理一體化、社會保障的一體化、教育衛生服務的一體化。
身處咨詢行業的姚沅有他自己的見解:長三角區域正在緊鑼密鼓建設的一體化交通網絡構建了“有形”的通暢。而該區域居民天然的文化共性,以及當下城市間主動交流合作的加強則讓長三角在“無形”中也成為一個越來越協調的整體。
姚沅說,記憶中還有小時候坐綠皮火車搖搖晃晃地往來于南京與上海的場景,到了2000年后,往返于長三角之間最便捷的交通工具就是私家車了;而今天,隨著高鐵站的建設和高鐵班次的增加,杭州和南京都進入了上海1小時交通圈。
“蘇南地區和上海的距離越來越近了,各地級市之間的商務和文化交流比以前頻繁了許多。現在我和朋友在工作中一天輾轉長三角三個城市都很平常。可能上午從上海虹橋站出發到南京參加一個客戶項目啟動會,中午到無錫參加一個報告會,下午就回上海和另一個客戶交流。”姚沅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2019年1月8日,上海華夏經濟發展研究院聯合上海社會科學院智庫研究中心共同發布《長三角高質量發展指數報告》。報告顯示,在長三角城市群26個城市高質量發展指數排名中,上海、杭州、蘇州3個城市處于第一梯隊;南京、寧波、無錫、常州、南通5個城市處于第二梯隊;嘉興、湖州等13個城市處于第三梯隊;銅陵、宣城等5個城市處于第四梯隊。
多年以前,長三角不同地級市多處于同一水平線上,可能更多的是競爭關系。而今,長三角眾城市的地位、角色已經不同,這也就決定了這些城市需要在產業鏈上形成有差異、有分工、有互補的網絡。
“城市定位的變化帶來了個人生活和工作區域的多樣性,城市邊界愈發模糊,很多人都說不清楚自己是哪兒人了。”姚沅說。“比如說芯片制造行業。產業鏈必須依托長三角的整體產業資源,這些行業的一部分工作人員可能需要頻繁往來于整個區域的各分支機構。他對于某個城市的歸屬感就會相對弱化。”
被問及身份標簽時,舒揚和姚沅覺得自己“大體上算新上海人”,而閆麗則覺得自己“還是算嘉興人多一點”。身份標簽模糊的背后,正是城市邊界的模糊與融合。
隨著長三角一體化進程的深入,未來,這里的人和這里的生活,都將有更自由更多樣的選擇。姚沅說,“那時候要說清楚自己是哪兒人就更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