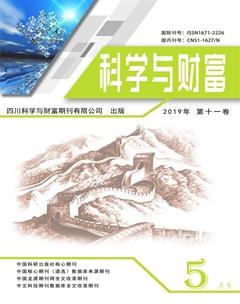流動時代的"炫耀性消費"
摘 要:中國海外留學生對于奢侈品的消費常常被定義為“炫耀性消費”,然而很少有人通過考慮這些留學生遷移前后的社會及文化背景、移居東道國以后的個人情感(如自我認同、歸屬感)的缺失問題,去探索他們奢侈品消費背后的動力機制。因此,本文作者旨在從文化差異、社會適應等方面探索留學生們追求奢侈品背后的“炫耀性消費”的動機。
關鍵詞:中國留學生、炫耀性消費、社會適應、文化差異
一、研究背景
全球化快速且便利的跨國生活使越來越多的人們走出國門去學習,去親身體驗更廣闊的世界。在《中國留學發展報告(2016)》顯示,2015年度中國海外留學生達到126萬人,約占世界國際留學生總數的25%,這一數據也在逐年增長。而中國留學生作為主要的移民群體,在留學國家的消費狀況也日益引起了媒體的關注。事實上,留學移民的消費不僅推動東道國走向國際化,更多的是加強了東道國經濟 。而這些留學移民的消費習慣也是各有不同的,因此了解移民的消費動機有助于了解他們是如何與移居國對話的。
過去30多年,隨著中國人經濟狀況改善,留學生的消費習慣發生了很大變化。關于中國留學生在美國開豪華車,酷愛買國際奢侈品牌的說法已經流行多年。2015年路透社的一則“著名”報道,題為《奢侈品牌瞄準美國穿著考究的中國學生》指出,一些國際名牌和奢侈品賣場紛紛推出專門針對中國留學生的銷售計劃,甚至派專車到大學接留學生購物等,希望通過吸引這些學生帶動他們的朋友和家人消費 。這是因為奢侈品牌商家認為中國留學生購買力巨大,且消費力度很強。例如,很多中國學生在出國留學后愿意將大把現金花在購買奢侈品牌的名車上,例如賓利、蘭博基尼、阿斯頓?馬丁等。
通過分析留學生境外消費時使用的支付卡行為,維薩(Visa)國際組織將留學生消費特點呈現在《2017 中國留學白皮書》中。報告指出2016 年境外交易額主要集中于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法國,而這幾個國家同時也是中國留學生的主要留學目的地。報告同時指出前十大商戶類型總交易額占比近72%,而時尚消費品占比龐大(維薩國際組織, 2017)。類似地,新華社《經濟參考報》與Visa公司聯合發布了《中國跨境消費年度指數報告(2015)》顯示,我國出國留學人員的消費形式中,支出占比最大的兩項分別是:奢侈性的衣著與化妝品 。同時,Bain and Co公司稱,在全球2730億美元的個人奢侈品市場中,中國消費者占31%,成為亞洲奢侈品消費最大的市場。在這些消費者中,中國留學生成為搶購大量奢侈品(如路易?威登、古琦、芬迪、圣羅蘭等)的主流群體。因此,這些媒體將留學生的這種奢侈品消費行為定義為“炫耀性消費”。
然而作者認為這是有失偏頗的。因為包含著文化和情感的消費在中國留學生群體中不僅僅是停留在炫耀性消費和攀比的基礎上去購買奢侈品,留學生這一類移民群體的消費更多是經歷了流動后試圖融入東道國而采取的一種經濟策略,因此作者認為在考慮學生們炫耀性消費的背后,應更多的思考推動中國留學生們奢侈品消費背后的機制,而并非僅僅將消費奢侈品的行為定義為“炫耀性消費”。
二、文獻綜述
(一)奢侈品消費與炫耀性消費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快速增長,消費者在購物時已經不僅僅只是滿足其功能性需求,他們還喜歡通過特定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社會性需求,于是中國奢侈品市場急速膨脹。 2009 年,中國已躋身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市場。大學生群體也由于對新鮮事物的追求被認為更容易進行炫耀性消費。
對于奢侈品的定義而言,學者各有看法。在經濟學中,奢侈品被認為是一種超出人們經濟范圍承受外的商品或服務。人們熱衷于購買奢侈品,是因為帶有獨特、稀缺、珍奇的奢侈品屬性象征著某種財富與地位。因此一定程度上奢侈品消費與其炫耀性消費是等同的。
而炫耀型消費的定義是:富裕的上層階級通過對物品超出實用和生存所必須的浪費性、奢侈性和鋪張性浪費,向他人炫耀和展示自己的金錢財力和社會地位,以及這種地位帶來的榮耀,聲望和名譽。因此有學者指出這類炫耀性消費從純粹經濟學意義上屬于非理性行為。
然而厲以寧認為雖然炫耀性消費與地位與財富展示掛鉤,然而這里面不乏理性的思考在其中。消費者憑借消費產品不僅可以表達自己的社會地位,更多的是表達自己獨特的價值觀、個人品質、性取向、年齡、種族、愛好等。所以我們不能將炫耀性消費直接等同于奢侈性消費。
對于留學生而言,他們雖然熱衷于購買奢侈品,然而從凡勃倫對炫耀性消費的定義看來,將留學生的消費定義為“炫耀性消費”是有失偏頗的。首先,從留學生流動的特點出發,留學生在剛進入移居國時,并不急于用購買奢侈品的方式證實自己在移居國地位,他們首要目標是進行社會適應。
事實上,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消費行為都涉及一場符號斗爭,都是一場為尋求區隔或融入而進行的斗爭。通過這種符號斗爭,消費者可以確立其獨特的地位與認同感。我們不能排除留學生是作為一個較為理性的群體去購買奢侈品,他們或許只是為了進入其東道國的社會圈子,以期獲得良好的社會互動,正如Jaramillo等人所指的那樣。
同時,我們并不能保證這類留學移民群體只是熱忠于奢侈品的消費而忽視了消費品的實用性。凡勃倫也在消費品實用與浪費的辯證法中寫道:如果看到任何商品或勞務的根本目的和主要成分是炫耀性浪費———不管這一點是怎樣顯而易見,就斷定它絕對不存在任何實用性,這種是危險的;另一方面,對于任何基本上屬于實用的產物,如果貿然斷定浪費因素同它的價值毫無直接或間接關系,那也是危險的。因此我們并不能說留學生所購買的奢侈消費品沒有實用性而僅僅只是為了顯示它的價值。
留學生對于移居國的生活而言是一類“陌生人”,而這類陌生人不是“今天來明天走的流浪者”,而是“今天來并且要停留到明天的那種人”。所以這個停留是長期的,在這個長期停留期之中,適應期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Ward及相關研究者發現留學生們移居后的焦慮及缺失歸屬感的狀態在第一年的時候水平是最差的,這是因為第一年對于移居者們來說處于跨文化適應的初期階段,他們不了解如何融入當地的生活。在這種陌生人世界中生活以及需要較長一段時間才能融入這個世界時,除了在他們直接觀察之下所能展示財物的商品(如服飾與化妝品)為依據外,已別無其他方法。正如凡勃倫所說:“一個人要他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那些漠不關心的觀察者,對他的金錢力量留下印象,惟一可行的辦法是不斷地顯示他的支付能力。”
因此,我們不排除留學生群體有炫耀性消費的因素在里面。然而我們同樣要去思考留學生消費奢侈品的目標不僅僅是炫耀性消費,或許甚至不是炫耀性消費,而真正推動他們消費奢侈品的機制是社會適應與文化融入。同時,人是社會之人,也是理性人,不可能單憑個人的表面消費就決定了奢侈品消費為“炫耀性消費”,人的消費與經濟支出必須要考慮到非經濟因素方面。因此,我們要考慮到移民進入“陌生”社會的客觀因素。
(二)移民與消費
移民通常對移居后的文化差異非常敏感,很多剛抵達移居國的移民們一般會參照移居國的消費行為,形成一套消費慣習來作為文化適應的策略。因此這種消費暗喻著消費者對歸屬的期待。正如很多學者通過側重研究移民在移居地的消費,指出國際移民渴望通過消費來實現在移居地的社會文化適應并獲得其對身份的認同以及社會地位特征。 例如,Ger 與Ostergaard討論了移民如何通過移居國的消費建立和展示他們的個性。 Oswald通過對美國中西部海地家庭的民族志研究,論證了民族消費者是如何利用消費這一種“文化交換”在不同族群身份之間流動的。即消費扮演著一種“文化交換”的模式,移民購買其他族群文化中的東西去形成移民在地化的身份認同,他們甚至會為了產生在移居國生活的歸屬感,嚴苛地要求自己去購買移居國消費者的使用產品。
因此消費物品事實上就是消費認同。例如移民美國的海地移民表示他們積極參與美國的消費文化,例如吃快餐,使孩子接受美國大學的教育,享受美國當地電視節目,通過這種消費,消費者不斷接受移居國的文化,適應東道國社會文化的期望。
雖然一些研究表示中國留學生在國外留學時奢侈品后的“炫耀性消費”力巨大。然而作為一部分缺乏歸屬感的群體的留學移民來說,他們剛移居到一個新的國家的時候并不屬于這個社會,這個陌生的世界使他們群體到身份的不確定性與不安全感,再加上他們失去了伴隨他們長大的熟悉的文化根基和地理場域,使得移民群體失去認同感與歸屬感。因此作者認為解釋留學生的消費狀況需要考慮到留學生移居后最容易丟失的一種特質——歸屬感的成分在里面。因為留學生們缺失在地的歸屬感,因此迫切地希望在融入當地人的社會,因此用貨幣去購買奢侈品成為了可視化且便利的實踐。
其次,對于文化來說,中國學生很難融入西方文化。強調集體主義的中國文化認為個人價值要在集體中才能得到更大的體現 。這與強調個人主義的西方文化是完全不同的 。在深受儒家傳統文化影響的中國,消費者與西方消費者觀念有產生很大出入,該地消費者具有較高的依賴性的自我、個人服從群體和社會、等級制合法存在、通過群體判定個人的特征。正如凡勃倫所說亞洲國家例如日本與中國在服裝上有比較穩定的式樣和類型,而這類穩定的服飾事實上隱藏著嚴格、狹隘的地方文化色彩;然而崇尚自由的歐洲發達國家,服飾式樣時新,沒有定式。而在遷移后,留學生脫離了東亞文化圈,進入到較為自由的西方文化圈的時候,很容易被西方奢侈時尚所吸引,迫切地想要改變。在一個充滿異質性元素的社會,他們的認同與歸屬感需要通過重新塑造自己來確立。而塑造認同與歸屬感的來源最便利的策略就是消費。
消費為“局外人”缺失的安全感與想要改變的心態提供了一條便利的途徑。這是因為消費使移民群體可以獲得一種“群體成員感”,也使消費者獲得一種具有了進入某個圈子的門票,從而擺脫了對“落伍”、“不合拍”、“鄉巴佬”等污名化的恐懼。在這些時尚之中,對奢侈品的消費是最容易被觀察到的且最可能獲得好評的。因此對于留學生而言,集時尚為一身的奢侈品的服裝、化妝品等就成為了中國留學生的首選。
同時,從中國學生的生命歷程來說, 基本上每一個中國學生都是按照小學-初中-高中-大學的學習歷程生活,他們中只有少數學生有社會上工作的經歷,也就是說在大學畢業前他們一直處于學習的狀態,他們的生活一直處于家長——老師的這種雙重壓力之下。當他們出國后,他們離開了一個絕對的、長久壓制的生活環境之中,他們需要在別的領域尋找一個暫時的、多變的代替品,而奢侈品中的時尚就構成了個人的巨大征服。
因此如果把留學生的消費定義為炫耀性消費,那么我們會忽視留學生在炫耀性消費中所承擔的更為污名化的風險。例如,在移居地實施 “炫耀性消費” 不僅難以獲得個體社會地位的提升, 還有可能被主流社會斥為 “暴發戶” 并引起公眾反感。而事實上,留學生并不會希望“炫耀性消費”讓他們處于風險地位上。相反,大部分留學生的東西是希望與當地習俗與時尚一致,從而避免受人白眼或引起指摘。
三、結論
因此,結合以上分析,作者認為大部分中國留學生運用經濟手段方式去購買奢侈品的背后的動機并不僅僅是通過“炫耀性消費”去炫耀他們的地位及財富。推動他們購買奢侈品背后的機制或許是他們期望融入當地社會的動機。也許炫耀性消費在留學生中的奢侈品消費中仍然成立,然而我們必須要考慮到留學生們的遷移空間、大部分中國留學生們的生命歷程、以及文化差異的背景去思考這些留學生熱衷于奢侈品消費的原因。炫耀性消費也許僅僅是表象,在炫耀性消費的背后,隱藏的更多的也許是包含文化、社會的動力機制。
參考文獻:
[1]凡勃倫.1984.有閑階級論-關于制度的經濟研究[J].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黎相宜,周敏. 2014.跨國空間下消費的社會價值兌現——基于美國福州移民兩棲消費個案研究[J].社會學研究.
[3]厲以寧.1995. 經濟學的倫理問題[M].北京:三聯書店.
[4]劉飛.2007.從生產主義到消費主義:炫耀性消費研究述評[J].社會.
[5]齊美爾.2001.時尚的哲學[M]. 費勇等譯. 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6]維薩國際組織.2017. 中國留學生海外消費理性嗎[N].中國教育報.
[7]曉彤.2014.中國留學生“燒包”式消費[J]. 中國報道, 41.
[8]王輝耀,苗綠.2016.中國留學發展報告[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39.
[9]Black, J. N. H., and Myles, G. ( 2012).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4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0]Europe.chinadaily.com.cn. (2012). More young Chinese keen on luxury goods|Economy|chinadaily.com.cn. [online] Available at: http://europe.chinadaily.com.cn/business//2012-08/18/content_15686071.htm
[11]Feng, J. (2014). The spending power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online] gbtimes.com. Available at: http://gbtimes.com/business/spending-power-overseas-chinese-students [Accessed 2 Aug. 2017].
[12]Gumpert, K. (2015). Luxury brands are targeting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online] Business Insider. Available at: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r-luxury-brands-shower-attention-on-well-heeled-chinese-students-in-us-2015-12.
[13]Jaramillo, F. and Moizeau, F. (2003).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 Theory, 5(1).
[14]Lazic, A. and Brkic, M. (2015). An analysis of decision-making factor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selecting the summer programme: The case of the Ljubljana summer school. Master. University of Ljubljana.
[15]LSE (2007) The Impact of Recent Immigration on the London Economy [pdf] Lond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Available at: http://www.lse.ac.uk/geographyAndEnvironment/research/london/pdf/thei mpactofrecentimmigrationonthelondoneconomy.pdf
[16]Lichy, J. and Pon, K. (2013). The role of (foreign?) culture on consumer buying behaviour: What changes when living abroad?. Transnational Marketing Journal, 1(1), 5 - 21.
[17]Liuxue.sjtu.edu.cn. (2017). 中國留學生海外消費報告. [online] Available at: http://liuxue.sjtu.edu.cn/mp/new_info.aspx?id=308 [Accessed 2 Aug. 2017].
[18]Lu, C., and Han, W. (2010). Why Dont They Participate? A Self-Study of Chinese Graduate Students Classroom: Involvement in North America.Brock Education Journal, 20(1).
[19]Memushi, A. (2013).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of Luxury Goods: Literature Review of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Eviden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tific and Engineering Research, 4(12).
[20]Ong, A. (1999). Flexible citizenship.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1]Oswald,L.R.(1999). Culture Swapping: Consumption and the Ethnogenesis of Middle-Class Haitian Immigrants.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5(4), 303-318.
[22]Zhang, Z., and Xu, J. (2007). Understanding Chinese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s
adaptation to learning in North America: A cultural perspective. Higher Education Perspectives, 3(1), 45-59.
作者簡介:
陳海粟(1993-),女,貴州省,漢族,碩士,學生,研究方向:移民社會學、教育社會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