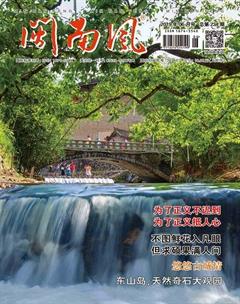不圖鮮花入凡眼 但求碩果滿人間
朱亞圣


時逢新中國成立七十周年之際,2019年4月23日,由中國國際文化傳播中心、中國美術家協會、福建省美術家協會主辦的“水墨聚焦·大國智慧集體之美”畫展開幕式在北京民族文化宮舉行,新華社和人民日報海外版分別做了報道。此次展覽共展出盧一心近年創作的精品力作108幅,題材均以葡萄為主。
4月29日,世界園藝博覽會在北京開幕,而作為中國館里的福建館背景墻作品就是盧一心以“一帶一路”為背景創作的巨幅國畫《大國智慧集體之美》,一亮相就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國際友人的關注和好評。
5月6日,由中國國際文化傳播中心、中國美術家協會、福建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龍巖市政府主辦的“生態龍巖 紅色閩西”全國中國畫作品展在龍巖市美術館開幕,盧一心丈二畫作《大國智慧集體之美》再次成為畫展的亮點。
談到為何創作這幅作品?盧一心現場向相關領導和中國國際文化傳播中心執行主席龍宇翔等介紹畫作創作構思。他說,公元前138年,張騫出使西域,從大宛國帶回葡萄品種,從而打開絲綢之路另一道亮麗風景。如果把中華民族比喻成一棵千年葡萄樹,那么,56個民族就是56串葡萄,每個民族團結起來,就可創造出前所未有的集體之美。同理,如把“一帶一路”也比喻成一棵葡萄樹,那么,沿線各國就是其中一串葡萄,沉甸甸碩果加上一年四季,年復一年所付出的努力,足以說明一切,這就是大國智慧集體之美所呈現出來的時代美感和精神象征,讓我們一起以葡萄的名義弘揚絲路精神。這也正是盧一心在北京民族文化宮畫展的主題,之所以取名《水墨聚焦·大國智慧集體之美》的原因。
自2014年開始,盧一心先后應邀到福建博物院、中國閩臺緣博物館、北京鳥巢文化藝術中心等舉辦個展。2016年應邀參加慰問駐港部隊,作品多次被選為國禮,贈送國際友人。
盧一心現為中國國際文化傳播中心藝術委員會副主席、福建省海峽生態書畫院院長。從20世紀90年代起,盧一心的詩歌就在《詩刊》等報刊發表,并以其自然樸素的句子,謳歌大自然和淳樸鄉情,成就了一個詩人,成為一名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這幾年,他又開始轉戰畫壇,獨樹一幟的國畫作品,引起畫壇的關注。
盧一心認為,藝術創作本該擁有豐富的文學語言和想象空間,這樣的藝術才更有生命力和價值,審美層次感才會更加豐富。也就是說,畫不能只是一張畫,畫的背后應該有更豐富的語言和思想的光芒,否則就顯得太單薄了,審美層次也會不夠豐富。換句話說,畫家不能只滿足于工匠創作,而應該有藝術的感染力和心靈的啟迪與照應。
他有一個逐夢畫家的童年
也許畫家的稱呼對盧一心來說也就是這幾年的事,其實早在他五六歲的時候,在一張三五毛錢的年畫家里也買不起時,父親就自己動手畫。父親多才多藝,當年畫了兩條魚,掛在簡陋的餐桌上方,魚兒活靈活現,至今還鮮活在盧一心的腦海里,正是那張畫,成為他人生最初的藝術啟蒙。因此,與其說這是為了“圓夢”,不如說是觸碰到了“最初的夢想”。
不過父親當年是極力反對盧一心學畫的,在過去不論畫畫還是寫作都被視為不務正業。即使這樣,在他心里父親依舊是他藝術的啟蒙老師,給了他最初對美的夢想和追求。
還有一件事對盧一心來說也是記憶深刻,當時家里窮,買不起紙筆,抵不住學畫熱情的他給在北京的親戚寫信,求親戚帶幾支畫筆能讓他好好學畫畫。親戚用半個月的工資給盧一心買了一大捆一百支的畫筆。不僅如此,親戚還帶回一些塑料花,這在當時可是稀罕物,盧一心小心翼翼保管著,對著塑料花一遍又一遍臨摹。為這件事他被家人責備了好長一段時間。盧一心的另一位美術啟蒙老師叫吳七章,雖然他沒有“正式拜師”,而且吳七章弟子滿天下也是事實,盧一心就是從他那里學到素描基礎的,并且得到很好的啟蒙。
后來他開始寫作,初寫小說,后專攻詩歌。就這樣,盧一心寫了二十幾年的詩歌,至今還對詩歌情有獨鐘。可以說,早年寫詩的經歷對他的畫作不無影響,對詩意的追求有過之而無不及。在那些寫詩的日子里,作畫也不曾缺席,盡管時斷時續。2009年,他出版第一本長篇小說《三平祖師》,書中的插畫都出自他的手。盧一心說他現在大部分的時間在作畫,但他一直堅持上午寫作。
他用一顆詩心在作畫
盧一心首先是個作家。1993年,他參加了魯迅文學院的第十三屆創作研究班,愈發促進了他創作的成長。此后他便寫出了《折疊》《花瓶的舞》《游子心》《土樓系列之四》《作一次靈魂的探險》等詩作,在《人民文學》《詩刊》《啄木鳥》《天津文學》《福建文學》等發表大量作品,先后出版了詩集《玫瑰歌手》、長篇歷史小說《三平祖師》、散文集《不落塵的港灣》《文人的驕傲》《時間的影子》、隨筆集《國家心事》等十部。
如果說,盧一心的詩很擅長通過一種意境或是一個畫面,捕捉到美的意境和感情,讓動人的詩句直抵人的心靈深處,那這種功力恐怕與他對繪畫的熱愛不無關系。其實,探尋盧一心與繪畫的淵源,比寫作來得更早些。“很多人不知道,我繪畫比寫作時間還長。由于小時候家里窮,買不起文房四寶才轉寫作的。”盧一心說,寫作幾十年后突然以畫家身份出現,的確讓許多人感到很奇怪,其實一點都不偶然,因為他從沒有放棄過繪畫。如今他已年逾不惑,終于可以右手著文、左手作畫,朝小時候的愿望邁進了。
汪曾祺曾說:“中國畫本來都是印象派。”盧一心非常認可這句話。他的畫在“似”與“不似”之間,既清晰又朦朧,空靈而真切,充滿想象又富于生活情趣。尤其是他的花鳥,或葡萄或梅蘭或菊竹,畫面清新可愛,布局充滿詩意,加之他隨手點出的幾只小動物,如小雞、小鳥、蜻蜓等,愈發顯示出豐富的感情色彩和文人情懷。對于國畫創作來說,意境很重要,與寫詩一樣,國畫也是一種“功夫在詩外”的藝術。從這一點來看,國畫創作與詩歌創作更為接近,都需要詩意的表達,都需要創作者的才華和悟性。盧一心認為,中國畫意在筆先,寫意是其主要目的,如果沒有意境,那還不如不畫。
作為畫家的盧一心,他的作品特色突出。線條活潑流暢,筆墨淋漓,濃淡濕枯運用得恰到好處。構圖也自成一格,尤其是留白處看似隨意,實則頗有講究,虛中有實,實中生虛,呈現出生活的趣味和泥土的芳香。如他畫的葡萄和梅花,乍看很入仕,細看很“超脫”,可以看出作者的情緒與襟懷。可以說,花鳥畫看似容易,其實出新很難,尤其是現在畫者眾多,想另辟蹊徑十分不易。而盧一心筆下的葡萄和梅花,卻給人帶來了幾分驚喜。同樣的題材,他畫出了“不一樣”的感覺。

從本質上講,盧一心是個詩人,他是用一顆詩心在作畫,這是他的畫不落俗套的原因,也是他逐漸被“圈里人”肯定的原因。
他對畫葡萄一見鐘情
繪畫在盧一心看來,是他用另一種方式來觀察現實生活。
葡萄畫是他的繪畫主攻。畫葡萄最難難在如何把最俗的東西畫到最雅,而且構圖不重復。葡萄在盧一心的理解下有兩個重要的層次,葡萄成熟、甜美、團結,圍繞著一個藤蔓,葡萄一整串一整串的,這跟如今的社會精神是一致的,而葡萄在民間還有多子多孫的意思,喜氣,接地氣。這就是為什么盧一心的作品自然樸素而又充滿感情,他不是憑空作畫,即使普通如葡萄,他也能發現其雅俗共賞、喜聞樂見的內涵。
從寫到畫,這兩種不同的意識形式在盧一心看來,既不是相同的也不是不同的。文學作品和繪畫藝術是兩個審美層面,一個用文字來表達,一個用圖像視覺,而它們殊途同歸,同樣都是讓人在閱讀欣賞它們的過程中產生愉悅和美的享受。只不過,盧一心認為,相比較而言,繪畫這種表達方式更大眾化一點,也越來越受大眾喜歡。
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國際文化傳播中心執行主席龍宇翔說,藝術需要心靈溝通,盧一心就是一個典型的藝術家,他雖然生活在閩南地區,但他始終情系家鄉熱愛家鄉,把自己家鄉的山山水水,用他的彩筆向世界傳播。舉辦的葡萄畫展就展示了他多年的心血。
盧一心集詩人、作家和畫家多重身份,內心涌動著對葡萄原根情結的追問和審美沖動。一邊以作家的深刻,總結出葡萄精神——三種境界和哲學思考;另一邊以畫家的敏感,采用新水墨技法,將國畫的寫意與西洋畫的色彩結合起來,使光影、線條、色彩呈現出更加新奇的視覺效果,創作出一系列獨具特色的葡萄國畫作品,抒寫西域風情,絲路情懷,敦煌情調,表達對新時代、新絲路的暢想。
目前,盧一心的葡萄畫已受到業界的廣泛認可。福建省文聯副主席、書協主席陳奮武評價說:“是個作家,也是個詩人,同時是位畫家,可見他的多才多藝。盧一心的葡萄畫栩栩如生,好像可以摘下來吃一樣,畫得非常好。”原福建省美協主席陳玉峰則說:“他的畫融合了西畫的技法,畫面空間感很好,質感很強,有自己的創新。”福建省文聯副主席、書記處書記、省美協副主席王來文說:“看得出盧一心的葡萄畫受蘇葆楨影響很大,技法和色彩也有自己的追求,找到了自己的藝術語言。”中國美術家協會分黨組書記、駐會副主席徐里欣然為盧一心題寫《一心葡萄書畫集》書名。
他眼里的葡萄閃爍著一種時代精神
把一切苦埋在地下,將所有甜掛上枝頭。
每一個完美的個體都需要集體的擁抱和溫暖。
不圖鮮花入凡眼,但求碩果滿人間。
這就是盧一心對葡萄精神三個層次的理解和哲學思考。
公元前138年,張騫出使西域從大宛國帶回了汗血寶馬和葡萄品種。據《詩經》記載,中國葡萄有3000年歷史,“六月食郁及薁”。“薁”即葡萄。而據《圣經·創世紀》里記載,葡萄在這世界上已有6000萬年歷史。葡萄之神奇由此可知。
盧一心喜歡葡萄,因其色艷、味美,具很高的營養價值,被人奉為“水晶明珠”。也因其果實呈圓形或橢圓形,且成簇成串生長,碩果累累,有團結、合作、共贏、奉獻之時代特點。在民間,它還是吉祥之物,有豐收、甜美、圓滿、多子多孫之寓意,飽含傳統文化韻味。此外,葡萄歷經春夏秋冬,風霜雨雪,年復一年,把一切苦埋在地下,將所有甜掛在枝頭,這種大無畏的奉獻精神就是葡萄精神。
葡萄生命力之強,足可匹敵所有的果樹。無論是河灘、鹽堿地、山石坡地,也無論大江南北乃至全球各地都能生長、結果、成熟,各種氣候均能適應。這是一種品質,充滿向上的正能量。
盧一心為葡萄著文,并以葡萄為繪畫題材,就是要創造出這種美,努力讓這種美成為每個人心中的夢想。在他的筆下,土生土長的葡萄就像一位樸素、甜美的村姑從國風中走出來,靦腆而又羞澀,而張騫引進來的葡萄則像一位洋妞,熱情而又開放,總是給人帶來某種驚喜。